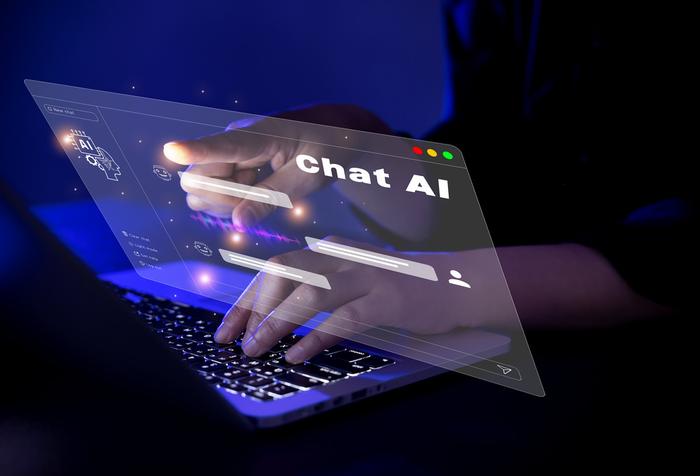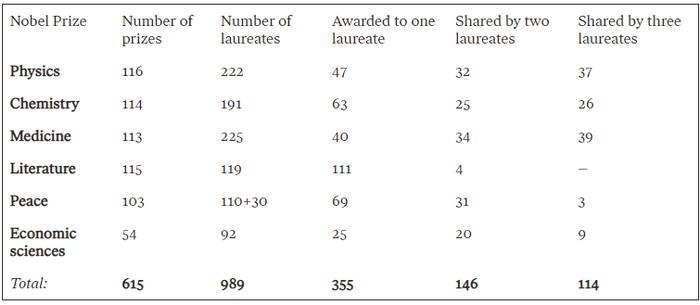《紅樓夢》還有小說作爲“小道”的娛樂精神嗎?
今天,我們在談論文學日漸衰微時,大多在文學的外部尋找原因,也許我們似乎可以從文學內部找找原因——譬如,是否可以考慮從恢復文學的娛樂精神方面入手,擴大受衆面,使文學走出日漸小衆化的怪圈。
娛樂精神,在傳統小說中其實是很發達的。
我們現在一談小說,不少人就顯出一臉“正經”,以文學的文學性、崇高性、嚴肅性來否定文學的娛樂性,更有甚者,只偏執地看到文學的教化功能、“爲人生”的目的,以爲文學除此“目的”之外再也無其他存在的必要。我們似乎忘記了,其實從源頭開始,中國小說就是爲了娛樂。娛樂恰恰是小說最爲重要的品質。
那麼,什麼是中國小說的娛樂精神呢?
我認爲,小說的娛樂精神是指創作者在創作小說時,完全是在自由、愉悅中進行的,秉持非功利的文學審美。小說的娛樂精神,就是指作者在創作小說時,爲了自娛或娛人,讀者閱讀小說,第一尋找的也是快樂。
宋時,理學興起,文人士大夫退出了小說寫作,盛行於民間的“說話”開始走向了前臺。
宋元時期,“說話”盛行,說話藝人們的“話本”經過底層文人的再度創作,成爲宋元話本小說。話本小說來源於“說話”,它的重要特徵是以娛樂爲首要目的。
在源頭上,白話小說就帶有極強的民間娛樂性。
從程毅中先生輯注的《宋元小說家話本》收錄的小說看,幾乎每篇小說都有一個精彩的故事,充滿了娛樂味。如《碾玉觀音》本身就是一個特別有意味的故事,其中璩秀秀做鬼後戲弄郭排軍讓人忍俊不禁,《錯斬崔寧》故事曲折離奇,很有趣味,等等。
同時,話本小說中,還大量使用“徹話”,插科打諢,目的就是爲了娛樂。也有論者認爲,不少話本小說還呈現出喜劇的結構,“如《張古老》《宋四公》《史弘肇》《皁角林大王假形》幾篇,笑聲幾乎隨處可聞,暢情滑稽,又不流於尖酸”。
宋元話本小說由說話人的底本發展而來,首先便要滿足聽衆的娛樂要求——娛樂性和通俗性自是題中應有之意。魯迅談宋之話本,說“其取材多在近時,或採之他種說部,主在娛心,而雜以懲勸”——主要還是一則則生動有趣的短篇故事,使讀者獲得娛樂和審美雙重滿足。“至多有個‘勸’字,勸過了,該講什麼講什麼。”
晚明經歷了中國歷史上一次較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文人尚趣。“晚明文人追求的趣境人生既是一種人生態度的逍遙自適,更是一種洞穿人生的審美本然,這種審美態度表現於文學上就是視文學創作爲自足自樂的個性化行爲,於輕鬆詼諧中追求趣味,展現才情。”甚至有人提出了“文不足供人愛玩,則六經之外俱可燒”。
明代以“三言”爲代表的擬話本小說,不少即由宋元話本發展而來,本身具有娛樂特徵,加之晚明文人重趣,以及“以文爲戲”的推波助瀾。譬如,李卓吾在評點《水滸傳》時就說:“天下文章當以趣爲第一。”金聖嘆直接用“以文爲戲”的觀點來評論《水滸傳》,在第三回他批註道:“忽然增出一座牌樓,補前文之所無。蓋其筆力,真乃以文爲戲耳。”
在尚趣的大氛圍中,馮夢龍對宋元話本小說進行的改寫,使之更加豐富細緻,語言更加貼合人物的個性等,來自民間說話文學的娛樂性和自由勃發的生命力進一步得到張揚。
“三言”中小說的娛樂性大致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其中大量的小說運用了“調包”“冒名頂替”“女扮男裝”等故事模式,使其充滿了戲劇性,情節曲折好看;二是故意製造和設置了許多有趣的對立;三是生動形象、詼諧俚俗的方言口語的運用。
“三言”中許多故事運用了“調包”“冒名頂替”等橋段,這顯然來自民間說話,這些故事模式的使用極大增強了小說的娛樂性,使之十分吸引人。而馮夢龍的改寫創作則使得小說在娛樂性的情節之外具有真切自然的肌理,情節熟悉卻令人百看不厭。這些故事足以媲美莎士比亞具有類似故事模式的喜劇。
比如《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寫因新郎生病,年輕貌美的弟弟代替姐姐出門,他們精明的母親打算在三朝後視情況而定,到底要不要讓女兒真正出嫁。可想不到新郎家卻讓姑伴嫂眠,新婚之夜意外成就了另一對姻緣。在這篇傑出的小說中,“調包頂替”“男扮女裝”的情節架構可能來自民間口頭文學,就像人們總是津津樂道的梁山伯與祝英臺、木蘭從軍的故事一樣。“弟代姊嫁”出人意料,能夠引起聽衆/讀者強烈的新奇、愉悅的感覺,是這篇小說娛樂性最重要的來源。
而馮夢龍的改寫,一方面使得這略顯誇張的情節顯得合情合理,彌合了生活的真實與戲劇性之間的縫隙;同時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劉媽媽之自私自利、孫寡婦之精明、劉公之厚道軟弱,無不躍然紙上。這篇小說娛樂性的另一方面則體現在生動活潑的語言上。代姊而嫁的孫潤和小姑慧娘洞房內的一段對話,委婉、節制、語義雙關、充滿張力。孫潤是知情的一方,又驚又喜且怕,由節制而一步步地挑逗,慧娘因不知情,竟然主動,對讀者來說,既精彩又緊張懸疑。如果說二人的這段對話是文人創作的典範,那麼劉公知情後和劉媽媽埋怨打罵的一段對話則是俚俗的口語、民間生動活潑的方言土語在文學作品中偉大的記錄和表達。而當劉家父女母女三人打成一團、攪成一處時,小說的娛樂精神達到了高潮。結尾是喜劇性的,皆大歡喜:劉媽媽這個不顧他人利害的自私者最終賠了夫人又折兵,受到應有懲罰;而她的女兒慧娘卻是無辜的,最後得以“美玉配明珠,適獲其偶”,同時證明了自己的堅貞。無論戲劇性的情節結構,還是人物的對話語言,都體現出小說的娛樂性。
而這篇充滿娛樂性和喜劇色彩的小說之所以十分動人,其審美價值固然由於上面提到的兩個要素,還因爲它在思想方面充分肯定了人情(相悅爲婚)和人性(“無怪其燃”),肯定了“情在理中”——永恆的天理之下還有複雜的人情。這在理學家們紛紛主張理欲二分、“存天理、滅人慾”,社會風氣乾枯殘酷的明代,尤爲難能可貴。
除了《喬太守亂點鴛鴦譜》,“三言”中還有不少篇目設計了“調包”“女扮男裝”等戲劇性的情節。如《錢秀才錯占鳳凰儔》《汪大尹火燒寶蓮寺》《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而哪怕在“勸善”痕跡最重的《陳多壽生死夫妻》這樣的篇目中,仍有很強的娛樂精神:一是陳多壽從一個天上仙童粉孩兒到滿身癩瘡的癩蛤蟆,再到脫皮換骨,爲強調前後的對比,作者不惜設計了誇張離奇的情節;二是寫多福忠貞,描寫其母柳氏的言語舉止真實而富有喜劇性。
總之,“三言”作爲宋元話本的集大成者,中國白話短篇小說最重要、最傑出的代表,不管是其誌異傳奇的色彩,還是誇張離奇的情節,不管是“調包”“男扮女裝”等橋段的反覆運用,還是人物語言的俚俗生動,都體現出強烈的娛樂精神。
代表中國小說在明清發展成就的,是長篇章回小說。明清的長篇章回小說,朝向更多元化的方向演進,既有英雄傳奇(《水滸傳》)、神佛鬼怪(《西遊記》),又有歷史書寫(《三國演義》)。最重要的,在魯迅所謂的“世情小說”中包含了日常生活的敘寫,從而描寫真實人生,這使小說的審美進入一個新的高度和境界。但是,即使在這類小說中(其高峯當然是《紅樓夢》),依然不乏娛樂精神。
《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這三部小說是從“說話”而來的創作,其中的娛樂精神自不待言。尤其是《水滸傳》,歷代不少學者都將之看成一部“遊戲之作”。《金瓶梅》特地打破了《水滸傳》書寫“英雄”“歷史”的傳統,而把小說帶到“日常生活”的天地中。在這一方天地裏,既有人性和人生的深度、色空的本質,又處處充斥着娛樂精神,不管是西門慶和衆姬妾的生活,還是他和應伯爵等一幫酒肉朋友的交往,無不體現出來。而晚明另一部世情小說《醒世姻緣傳》則可以作爲白話小說中娛樂精神的又一證明。
《金瓶梅》作爲第一部文人獨創的白話長篇小說,影響了《紅樓夢》的創作。《紅樓夢》不但繼承了《金瓶梅》對日常生活的描寫,而且開始關注人物的內心世界。《紅樓夢》第一章告訴我們,這本小說寫的是作者自身的經歷,是一部個人心靈的痛史。也就是說, 它寫的是真實的人生,這和之前中國小說的傳奇志異,書寫英雄、歷史的傳統是迥然不同的——小說開篇反對“滿紙文君子建”,並借賈寶玉之口表明了作者對小說的態度。所以魯迅先生說:“自從《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
那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在《紅樓夢》這樣一部“爲人生”的大書中,是否還有小說作爲“小道”的娛樂精神呢?
首先,就其根本的精神來說,不管是無才補天的石頭,還是石頭在塵世中的幻象賈寶玉,都是反對“仕途經濟的文章”的,也即反對文學的功利和目的,只強調其審美價值。
其次,對立甚至誇張的人物形象設置一直是小說娛樂性的來源。《錢秀才錯占鳳凰儔》中寫醜陋又無才無德的顏俊想騙取美妻,讓有才貌的表弟錢青代他迎娶,其中描寫顏俊和錢青的兩首《西江月》——一個是“出落脣紅齒白,生成眼秀眉清。風流不在著衣新,俊俏行中首領。下筆千言立就,揮毫四坐皆驚。青錢萬選好聲名,一見人人起敬”,一個是“面黑渾如鍋底,眼圓卻似銅鈴。痘疤密擺泡頭釘,黃髮鋒松兩鬢。牙齒真金鍍就,身軀頑鐵敲成。楂開五指鼓錘能,枉了名呼顏俊”,就是以誇張對立的人物形象獲得戲劇效果和娛樂性的例證。
《紅樓夢》是寫實的,描寫更加真實而近自然,並不靠離奇誇張的情節和描寫來吸引讀者、聽衆的注意力。但《紅樓夢》同樣借鑑對立的人物形象設置的方法,以增強小說的趣味性和娛樂性:有一個深情的賈寶玉,就有一個濫情的呆霸王薛蟠;有一個敏探春,就有一個庸俗搞笑的趙姨娘;有一個尊貴威嚴的賈母,就有一個妙語迭出的王熙鳳;有一個一本正經的薛寶釵,就有一個詼諧幽默的林黛玉……
再次,《紅樓夢》的娛樂性固然體現在“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和“繡房裏鑽出個大馬猴”的對比,以及諸如六十三回“壽怡紅羣芳開夜宴”這樣的熱鬧場面之中,但這只是較表面化的一個方面。
更深層的娛樂精神則體現在諸如五十七回“慧紫鵑情詞試莽玉”、六十八回“酸鳳姐大鬧寧國府”、七十四回抄檢大觀園時探春反抗這些戲劇性的情節之中。它們並非重要關目,看似閒筆或風暴中的寧靜一隅,反而體現出小說的娛樂精神。
如到了七十五回,已經過了三十回之前寶黛互證感情、剖白心跡時的緊張激烈,卻以紫鵑的一個玩笑掀起波瀾,再次表現寶玉對黛玉的深摯感情,實際上使小說更具戲劇性。鳳姐大鬧寧國府,並不是她對付尤二姐的重要手段,但鳳姐到寧國府對質的一段描寫充滿喜劇性。
至七十四回“惑奸讒抄檢大觀園”時,已是“悲涼之霧,遍被華林”。探春房裏並非問題所在,但探春做出的精彩反抗,彷彿悲涼之霧下升騰的火焰,風聲鶴唳的小姐和得勢的奴才之間的一場對手戲異常好看。
總的來說,如果說源自“口說驚聽之事”的“說話”而來的話本或章回小說,其娛樂性來自傳奇志異的傳統、誇張而戲劇性的情節結構等,那麼《紅樓夢》這部偉大的傑作寫作者自身經歷,反對俗套的才子佳人的傳奇模式,使其抵達了文學審美更深廣的境界,卻依然在對立的人物設置、精彩的人物對白等方面顯示了小說娛樂性的美學特徵。
較之“三言” 通篇勸善、娛樂相雜的寫法,《紅樓夢》中的娛樂精神沒有那麼直接表現,而是隱藏在喜劇化場景的描寫和人物的設置與對白等元素之中。
要思考晚清民初白話小說中娛樂精神的問題,便不能忽略清中期另一部重要的充滿娛樂精神的白話小說《儒林外史》。
在這本主要寫儒林中人的小說中,第二回到第三十回,寫各種人追求名利地位的喜劇性的故事,其深入靈魂的諷刺同時顯現了小說的娛樂精神,其中“范進中舉”等片段,是小說娛樂性的典型體現。因此魯迅評《儒林外史》:“戚而能諧,婉而多諷。”意即悲慼的故事卻能以詼諧幽默的筆墨寫出——雖然以諷刺之筆顯示靈魂的深,卻又具有娛樂精神。又說它:“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 魯迅特別指出,《儒林外史》除了描寫的逼真外,還富有娛樂的精神。
1894年,《海上花列傳》問世。這部聲稱“模仿《儒林外史》結構”的小說,在其創作思想和內在精神上實際上追步《紅樓夢》。衛霞仙呵退姚季蓴太太的一段有敏探春的風致與口吻;趙二寶和史三公子、“癩頭黿”的故事儘管稱得上是描寫很成功的悲劇, 但其中仍具有隱含的娛樂性——正如它所追步的、描寫真實人生的《紅樓夢》一樣。
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以在報紙上連載的方式面世。它們在兩個方面受到《儒林外史》的影響。一個是結構,一個是諷刺、暴露黑暗。它們也和《儒林外史》一樣,於諷刺中顯示出小說的娛樂特點。
另一方面,晚清受到西方文學的影響。西洋小說的譯介和傳播,影響到文學觀念、創作的改變。
1902年,梁啓超提倡“小說界革命”。他所提倡的“新小說”有很強的政治色彩,旨在揭露社會弊病、暴露黑暗。在新小說的提倡下,小說努力擺脫其作爲“小道”的娛樂性、通俗性,漠視情節、內容空洞、人物符號化,而代之以政治、道德話語。但“新小說”的努力終以失敗告終。
民初的小說全面迴歸了娛樂性。民初的報紙雜誌,刊載其上的翻譯和創作,就小說而言,儘管不乏名著,如翻譯了契訶夫、雨果等人的重要作品,但整體上以娛樂爲導向。研究表明,偵探小說和言情小說佔去了其中的絕大多數。
五四新文學運動之後,不論是1921年“文學研究會”主張“爲人生的文學”,還是創造社提出“爲藝術的文學”,都反對民初的鴛鴦蝴蝶派作家遊戲的文學觀。
至此,小說的娛樂精神逐漸衰微以至消失。
相關圖書
《中國小說的文與脈》
周明全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本書着力探討的是當人類文明已進入“地球村”的今天,作爲中國文學中最爲重要的黃鐘大呂——“中國小說”是否還會獨立存在,或者說,“中國小說”顯現的意義是否曾經有過。作者循着“中國小說”的歷史脈絡,深入文本內部、深入作者的精神世界,用自心在場的心靈觀照,進行了有理有據的分析和闡釋,從而讓文本在解讀中煥發出獨具特色的批評與審美的光彩。
全書共分中國小說、文本細讀、青年書寫三個部分。
點 擊 閱 讀 原 文即 可 購 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