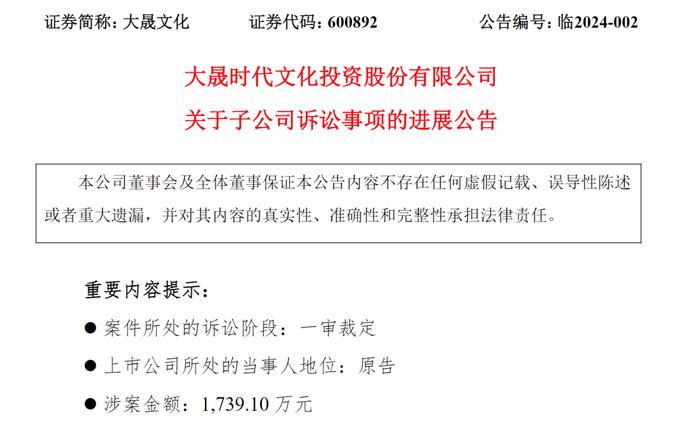《陰符發祕》的養生智慧
《陰符經》,全稱爲《黃帝陰符經》或《軒轅黃帝陰符經》,亦稱《黃帝天機經》,是與《道德經》、《南華經》和《參同契》並列的道教聖典。它被定爲道士必須誦習的經書之一,而納入《玄門功課經》中。其重要性,張伯端《悟真篇》一語中的,他說:“《陰符》寶字逾三百,《道德》靈文止五千,今古上仙無限數,盡於此處達真詮。”
《陰符經》的註釋本甚多,宋代鄭樵《通志·藝文略》中所載書目就有39種之多。《陰符經》現存注本,見於《道藏》的有二十餘種,見於《藏外道書》的有十餘種。下面以蒙文通《道書輯校十種》中的《陰符發祕》爲研究對象,着重探究《陰符經》中的養生思想。
一、《陰符發祕》簡介
清代全真龍門派道士張清夜(1676-1763年),字子還,號自牧道人。初名尊,江南長洲(今江蘇蘇州市)人,享年88歲。乾隆十一年(1746年),“因念遭際之隆,日夕兢惕,乃罄其所覺,以勸方來”,作《玄門戒白》;爲闡釋《陰符經》之祕,於乾隆十九年(1754年)作《陰符發祕》。
沈裕雲在《陰符發祕·序》中,對張清夜的《陰符發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說他的註文更重“身體力行”,他說:“予鄉牧道人去儒服改黃冠,腹笥甚富,寓居成都二十餘年,於三教諸書外,深契是經之妙,所謂三盜五賊之用,殺機之發,奇器之祕,皆以身體力行者自寫其會心之處,而津津道之,較之以郭注《莊》,尤見實際。”
張清夜在《陰符發祕》自序中,極力推崇《陰符經》之博大精深,謂其“乃崆峒授受之文,爲墳典丘索三教百家經書文字之鼻祖,以天地幽明而原始要終,明夫人未生之前、有生之後,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蓋天地與人蔘三才而一理,是以指天道而明人道,言簡而理該,義深而行易。”
張清夜認爲該書所闡明的道理,可以爲萬事萬理之指導,如指導養生、指導爲政、指導用兵等等。他說:“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出世者目爲養生是也,爲治者目爲王政亦是也,師旅者雲兵法亦無不是也。若執何者爲是即非也。惟其所莫能拘莫能定,以之推及於萬事萬理而莫不至,當此其所以爲《陰符》”。並得出結論說,《陰符經》“首以明機察物,繼以知動知時,而防克防漬,其徹始徹終,不過以自然至靜爲工夫,以法天行健爲法則,審能如是而知之、防之、體之、行之,則可超乎有生有形之外,而至乎無聲無臭之鄉,生滅兩忘,與太虛一體,豈止養生、王政、兵法而已哉!”
二、天人理論:天人合一
(一)天人同源
張清夜認爲天地、萬物和人都起源於道,其生化過程是:道生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五行,五行生八卦,八卦生干支,干支生卦爻,卦爻生萬象,萬象生萬物。而太極最終起源於“自然之道”,“自然之道靜者,先天太極之體也”,“虛靜自然爲生天生地之根本”。並認爲虛靜是“自然之道”的本質,它無形無象,無蹤無跡,“自然之道,廓然無象,冥然無跡,既不可以音聲求,又何可以象數計乎?”
自然之道是通過“浸”而產生天地萬物的。就是說自然之道生出的陰陽二氣是逐漸相推相勝的,陰氣消一分,陽氣就長一分,陽氣消一分,陰氣就長一分,如此逐漸進行,“陰陽相推,變化順矣”,天地萬物就逐漸產生出來。張清夜說:“人物何以生?蓋以天地之道浸也,浸者如溼與幹漸沁漸漬,無非形容氣機流動之象,即陰陽相勝之理如此。陰陽相勝者,即如陰之漸漸消一分,則陽亦漸漸息一分,陰之漸漸勝一分,則陽亦漸漸損一分,如是相推相蕩,則變化順而人物得以遂其生矣。”
(二)天人相盜相宜
在註釋“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乃安”,張清夜認爲天人既相互戕賊,又相互協調,養生的方法就是要盜取大地、萬物的造化。
其中,“盜”意即盜竊、戕害;“宜”,平衡,協調;“三才”又稱“三盜”,即指天地、萬物和人。
“天地,萬物之盜”,是說天地通過萬物的盛衰而生殺萬物,即“天地以時之盛衰爲萬物之新故,即……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而“天生天殺”就是說“萬物以天地發生之時而敷榮,以肅殺之候而凋謝”。“萬物,人之盜”是說萬物滿足人的嗜慾來戕賊人的真性。“人,萬物之盜”是說“人利用萬物而能摧殘萬物”。這三種情況都是天地、人和萬物沒有相互協調、相互適應的表現。
如果人能除五聲、五色之類的“五賊”,順應天地運行的規律,不但不會爲天地、萬物所戕賊,反而能盜取天地、萬物的造化,以利於養生。張清夜說:“若人能除五賊,識天符,順時觀化,則不但不爲萬物所盜,且又能盜天地萬物之造化,豈非天地位而萬物育乎!”
(三)天人合發
張清夜認爲《陰符經》的主題就是追求“天人合發”。他認爲,人是一個小天地,他的氣機在天地間周行不止,如果能“得其太極之元”,使“八卦自然內運,甲子自然進退”,“陰陽自然升降”,而不是在自身中反覆,就是“天人合發”的長生之道。他認爲,人的“氣機不能與天地同運並行者,蓋爲不能自作主宰,任爲五賊驅馳,遂與天道相暌、天行不符”,這不是天人合發。只有“天與人合一而不分,所以天地之發殺機而人與之俱發,人之發殺機則天地萬物莫不與之俱發矣”,纔是真正的“天人合發”。人在天人合發之際,就能“奪盡天地衝和之運,奪盡陰陽化生之妙”而長生久視。他說:“萬化定基者,於天人合發之際,奪盡天地衝和之運,奪盡陰陽化生之妙,始克重胚太機,再立根元,而不生之生生毓於此,不化之化化樞於此也。”故而說“此篇經旨,全歸在天人合發一句,爲一卷《陰符》之章旨也。”
三、養生思想
(一)識五賊:養生的前提
《陰符經》說:“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五賊”“即天地陰陽化生之子也,如色聲臭味觸之類也”,又如“耳目鼻舌身之類”。張清夜解釋說:“此五者皆能吸攪情塵,徇私馳逐,顛倒執迷,至死不悟,如太上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是也。若能識得破、看得透,不致認賊作子,便是施行於天也。施行於天者,一如天之無私無言,以五賊爲芻狗之意。審能如是,則六合一軀、萬年一念,身符造化、心統化機矣。”此句的意思是說:色聲臭味觸以及耳目鼻舌身的“五賊”,是戕賊人性命的“五賊”,人如縱情追逐,迷戀它們,就會損性害命,導致死亡。如果能夠認識到這“五賊”的賊性,就能探求到造化的根源,符合造化的運行之理,則可長生久壽。
張清夜認爲由於“五賊”在人心中的不同表現,人心可分爲“天性”和“機心”兩種,天性就是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心;機心則是有愛惡,會對人有危害之心。人心如果能不爲“五賊”所賊害,除去機心,就可以獲得天性。他說:“不被五行所賊的心,便是天性,即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真體也。庸人之情,一遇聲色至前,便生出種種分別愛惡,即此分別愛惡,便是惟危之機心也。人苟息了機心,盡合天性,則心之與性、天之與人豈有二哉!”
(二)辨奇器:施功的條件
張清夜認爲,人之神與氣皆是飛揚之物,很容易隨外界之引誘而飛揚於外,當神已翱翔於“紛華之域”,氣已陷溺於“愛慾之場”時,唯一的方法就是用炁(元氣,先大之氣)將它們擒制歸舍,而且只有此炁才能擒制它們。他說:“炁者,太和氤氳之元氣,天人相應之祕機,獨能含情抱住,凝精毓神之至寶也。……今也神既翱翔於紛華之域矣,氣隨陷溺於愛慾之場矣,所以聖人不得已而示人以相制相成之妙旨。蓋神之與氣,猶男之與女,火之與薪也。今曰擒之制在氣者,猶用女以配男、用薪以傳火也,則天涯蕩子庶幾有鄉關之戀戀,不致於雲蹤雁跡也。但用氣之旨,聖經絕不言身中之氣,而必斤斤乎天人合發之機者,蓋以此軀爲有形有質,皆屬於後天而不可用故也。”
張清夜聲稱,人身有“奇器”,是擒制和鍛鍊精氣神的處所。這種奇器,就是人身小天地之太極,把它稱作玄牝、爐鼎、丹田等都可,無非是聖人藉以盜陰陽、藏造化、下手施功的處所。以此處所爲依據,並通過逆天地造化來修煉人體的精氣神,就可成聖登真。他說:“奇器之名,今古不一:如《道德經》名曰玄牝,而《參同契》命爲爐鼎,《黃庭》謂之丹田,名乃異而用實同也。無非喻聖人之所以盜陰陽、藏造化,必有建立之基、經營之所。蓋奇者對偶之稱;器者受衷之府;故太極者,天地之奇器,而奇器者,乃人身之太極也。此器不與天地並列而能生天地,不與萬法爲侶,而能生萬象,超出萬靈,至尊無對,故曰奇器。從此器而順育陰陽則生人生物,由此器而逆施造化則成聖登真,五行運而八卦生,兩儀旋而甲子布,合溯藏機,神迎鬼避,此統奇器之功能也如此。”
(三)守三要:成聖的津樑
張清夜說:“心生於性,念發必克,精生於氣,情動必潰。”“念”指私念、邪念、雜念;“情”指情慾,即一般所謂的七情六慾。意思是說,修煉者不能存有邪心和情慾,如果存有它們,並讓它們隨意發展,就會使人的天性和生命遭到剋制和戕害,最終引起身心的潰敗。
張清夜認爲,人的邪心和情慾是“五賊”通過作用人的“九竅”(即二眼、二耳、二鼻孔、口、尿道、肛門)而產生的。例如,美色是通過眼的視覺作用後,才引起人們對它的沉溺;淫聲是通過耳的聽覺作用後,才使人們對它的迷戀。如此等等。因此要保持天性的純正,延長人的年命,就必須謹守這些門戶,不給美色、淫聲、邪事等有進入的機會。
在這九竅之中,最主要的是耳、目、口三竅。他說:“九竅中之最靈捷者,耳、目與口,謂之三要,此作聖工夫最喫緊處也”,“三要之動而外逸,爲入邪之首領”,“三要之能動能靜,即吾人作聖作狂之樞關也。”他認爲,此三竅常引誘人之心神向外馳聘,使人執著於情慾,導致人之死亡。
要避免人心爲三要所誘而導致不良的結果,必須採用“伏藏”之法。他說:“無如人心向外馳騁,是須善用伏藏”,“三要靜藏之機全在返源內伏”,“靜而伏藏,實爲辦道之津樑”,張清夜認爲謹守三竅,使心神內藏,則可以盜天地之機,克五行之賊。他說:“絕耳根之利,則兼倍於明,絕視司之利則兼倍於聰,何況三根盡返,而又能宵旦弗逞,其盜機克賊之功,可勝算哉?”
張清夜再進一步指出:三要之中,“目”這一竅最爲關鍵。他說:“耳目口三要之中,何以爲第一要耶?曰目是也。何以知之,曰原夫人生之初,一點元神,凝然中處,不識不知,朝成暮長,日漸知覺,元神變爲神識,則上游兩目,心生愛惡,隨物生死,故曰意雖爲六識之主宰,眼實爲五賊之先鋒,若得此要返元,其餘九關三要不返而自返矣。故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並說“目”作爲三要之中“最神最要者”,是“入聖之真樞”,是三教養生成聖的“津樑”。他說:“予聞佛典之六根六塵以眼爲先,太上有希夷微三者以視爲首,孔子四非之箴勿視爲先,至於帝堯之欽明、成湯之顧諟,《心經》之觀自在,《道德經》之觀有觀無,黃帝之三月內視,《陰符》之機在目,三教聖人之源,莫不以此爲轉機辨道之津樑也。”
(四)食其時:養生的關鍵
在《陰符發祕》裏,張清夜認爲養生的祕訣在於“食其時”(“食”,掌握,採取),即“乘時下功盜奪”天地萬物之造化來養生。他說:“《陰符經》‘陰’字,前人作暗字解,謬矣。昔稱分陰、寸陰,乃時字之義也。按《參同契》有拘蓄禁門、促迫時陰之旨,始知天人合發乃乘時下功盜奪也。何也?中篇雲: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足證此也。”其中,“時”包括“天人合發之時、時動食時之時、日月小大之時”三種。
張清夜指出,“時”就在日常生活中,就在平常之處,並認爲日常生活的所作所爲是“凡聖轉關之津要”。
張清夜強調“食其時”是養生的關鍵,因爲:
“食其時”是克服邪念和情慾的需要。就是說,要克服邪念和情慾必須把握住邪念情慾萌生初動的時機,在它們剛剛萌生初動之時,及時下手克服它們,連根加以剷除。張清夜說:“時者即禍發機動之時,物者即物慾紛然之際,人苟能於禍發機動之時,不惟不令其有必克必潰之勢,且能知之修之而又能返之,此時文之既明也。人又能於物誘紛紜之際,不惟不令其相殘相盜,且能回機內照,翕聚伏藏,此物理之且哲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能在物慾紛然之際,邪念情慾初動之時,立即下手克服它們,並將自己的元神“回機內照,翕聚伏藏”,就能避免身心被克而崩潰的禍患。
“食其時”是獲得聖功的需要,即要“契合日月”。由於“月廓滿則人身之氣血實,肌肉堅,月廓空則肌肉減,衛氣去,形乃獨居”,又由於人體的陰陽消長與日月運行相吻合,“陰火息時陽火消,理分臥立順羲爻,更隨黑白天邊月,六候方終晦朔交。此應人身一月之小周天也。太陽自冬至一陽來,復每月行三十度,三百六十日與太陰十二次交會,此應人身一年之大周天也。”因此,不僅採大藥時要“應時而動”,他說:“天人合發造化之應時而動,在朔望前後各三日共二七日爲大,兩弦前後各三日共十四日爲小。今天機陰符應大而不應小,故大藥之發生必在會望之候也。”而且如想獲得聖功,必須使人身之氣機與天地之氣機“自然牝牡相從”,即達到“天符”,人如果能“用不神之神,運無爲之功,合天人之候,契日月之符,潛修默奪,混俗和光”,則“筋骨乃堅,神形俱妙”。這種“契合日月”的“食其時”也就是“奉天時”,即掌握修煉的“火候”。
“食其時”是人們“作聖作凡”、入“先天”或“後天”的關口。他說:“夫時動者,即天人合發之時也,故時之動介乎先天后天之際、作聖作凡之間。或因其時之動也,則情擾乎中,變先天爲後天,此時動必潰之誡也;或因其時之動也,能運我自然之殺機,可以返後天爲先天,豈非萬化定基之始乎!至於知之者,即是知此時動之機也;修之者,即於機動之際及時下功行一得永得之道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倘能把握住時機,克服邪念物慾,可以返後天爲先天,可以由凡入聖;反之,則由先天入後天,由聖變凡了。張清夜還引《真鉛銘》來作例證,《銘》曰:“一念之非,降而爲漏,一念之見,守而成鉛,升而接離,補而成乾,陰陽歸化,是以還元,至虛至靜,道法自然,入能行之,一飛昇而仙。”張清夜認爲修真成聖,還要“食時動機”,“夫食時動機者,聖人直指人用功之際,機動有時,時至神知,陰陽旋運,地髓天飲,咽歸五內,臟腑安舒,形神俱妙,與道爲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