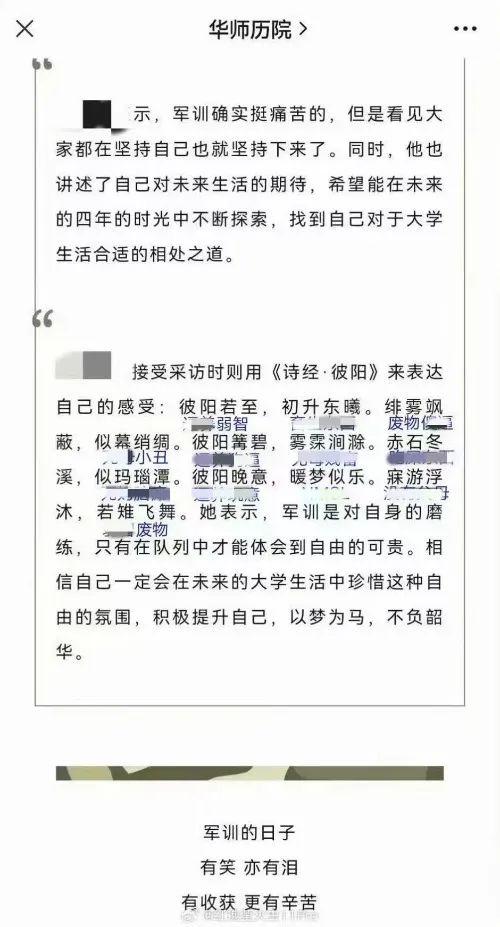潘麟先生講授《大學》連載四十三:《詩經》的價值和意義
編者按:
潘麟先生少年向學,雖早已接觸儒學,但其時因學力不足,見地不深,難以欣賞儒家學問之奧義,待經歷更多生活曲折、人生沉浮之後,再次玩味儒家仁義良知之教,方知華夏智慧,一脈千古,樸實無華而又微妙深遠。先生感念聖賢教化之恩,久欲爲此學貢獻綿薄之力,故發憤著述《〈大學〉廣義》,於此時代鉅變、舉世彷徨之際,以期張揚此聖學於當世及未來,企求薪火相傳,爲民族指示方向,爲人生指示歸途。
《詩經》不僅是儒家六經之一,還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樂歌總集。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爲何孔子如此重視《詩經》?《詩經》到底有着怎樣的價值和意義呢?請看潘麟先生講授《大學》之連載四十三《〈詩經〉的價值和意義》。
主持人:“品味儒家經典,享受中華文化。”大家好,歡迎收看本期的《東學西漸》之《大學》,我是主持人劉倩。本期來到現場的嘉賓依然是當代著名學者潘麟老師,潘老師您好!
潘麟先生:你好。
主持人:《詩》雲:“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請潘老師給我們講解一下吧。
潘麟先生:這是引用《詩經》裏的話。什麼是《詩經》呢?我給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翻譯成現在的語言就是:孔子說,《詩經》有三百多篇,但是這麼多的詩可以用一句話來高度概括它,就是它可以提升和淨化我們的心意,或者叫人格,或者叫身心,這是字面的意思。我們還可以把孔子對《詩經》評論的這句話再進一步地延伸爲它可以貫通先天與後天,形而上與形而下,道心與人心。
“詩”即《詩經》,儒家六經之一。《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孔子晚年對其重新進行編定,祛其浮雜,留其精華,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著名的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所謂的“六經”,指《詩經》《書經》《禮經》《樂經》《易經》和《春秋》。這些文獻,當孔子之時,並沒有稱“經”,直到戰國時期的《莊子》,纔開始稱其爲“經”。《莊子》一書有如下記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所以跡哉,今子之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
我們把這段話簡單地翻譯一下。孔子去拜見老子的時候說:“我研究《詩》《書》《禮》《樂》《周易》《春秋》這六部經典很久了,已熟知其中的道理。因爲內存私慾和虛僞之故,儘管當今七十二個君主都在口口聲聲地談論着所謂的先王之道,紹述着周公、召公等的聖德偉業,以此冒充道統正宗之傳人,但可惜的是,沒有一位君主能夠真心實意地去踐行周公和召公的豐功偉業和偉大的品德。唉——太難了!人心之詭詐太甚,陷溺於物慾太深,仁義之道難昭明於天下呀!”老子說:“你所謂的不幸在我看來是另外一種幸運呀!多虧你沒遇上治世之明君。如被你遇上,用你那一套腐朽的知識影響他,他一定會被你誤導的。其誤導之結果,很可能比你剛纔所說的七十二君更壞、更差勁。你所謂的‘六經’無非是古聖先王的思想之陳跡罷了,之所以說它是陳腐舊跡,是因爲它們都是過時很久的觀念學說了。難道你不明白如下的道理嗎?人的足跡,是人用鞋踩出來的,但你能說足跡就是鞋嗎?腳印雖在,但足履已遠。”以此暗諷孔子只知一味守株待兔,認跡爲履,乃食古不化之人。此是稱呼“六藝”爲“六經”之始。
《詩經》是中國韻文的源頭,也是中國詩歌史的起點,又因爲其中的作品都可以用樂器伴奏演唱,所以《詩經》也被稱爲中國古代第一部樂歌總集。《詩經》分“風”“雅”“頌”三個部分。
“風”是民風、風氣、風俗之義。“風”詩彙集了不同地區的鄉土音樂,多爲民間的歌謠,共計來自十五個地方的國情民風。
“雅”是王畿(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之樂,這個地區周人稱之爲“夏”。“雅”和“夏”在古文中是相通的,“雅”就是“夏”,“夏”就是“雅”。“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作爲典範的音樂。過去把周王朝直接統治的地區,就是“夏”這個地區所產生的各種詩歌和音樂稱爲“正聲”,因爲它就在天子腳下,受到國風影響,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地區,故這個地方的民風、民俗、音樂、詩歌被看作標準和典範。周代人把“正聲”叫作“雅樂”,因爲“雅樂”就是“夏樂”,猶如清代人把崑腔叫作“雅部”,帶有一種尊崇的意味。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和史詩,內容多是歌頌祖先功業的。《毛詩序》中說:“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這句話高度概括了“頌”的含義和用途。“頌”表現手法有賦、比、興,它的基本風格是淳樸自然,直面現實。
我們再說說《樂》,“詩歌”中的“歌”就是“樂”的意思,所以談《詩》是必須要連帶着談《樂》的。《樂》是隸屬周王室司樂的音樂作品,後世不少學者認爲《詩》和《樂》實際上是一體的。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詩》共計)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詩》三百五篇”這個地方少了一個“零”,應該叫“三百零五篇”。《詩》爲樂歌,“詩”記詞,“樂”記譜。《樂》集夏、商兩代音樂之精華,由周公在洛邑整理而成,並由周王室歷代樂官不斷地修訂和充實。現《樂》已經失傳,無法知道其原貌了。
周代重視貴族教育,貴族子弟把《詩》《書》《禮》《易》《樂》《春秋》稱爲“六藝”(“六藝”有兩種,另一種爲《禮》《樂》《射》《御》《書》《數》),是必備的知識。而《詩》《書》《禮》《易》《樂》《春秋》原收藏於周王室,至春秋末年,周王室大亂後,大量典籍散失民間,如此纔有後來“民間教育家”孔子之“刪《詩》《書》,定《禮》《樂》”,重新刪定典籍、整理國故之不朽壯舉,以及教授“六藝”於民間,開“有教無類”之先河。孔子終身以“六藝”教授弟子,自然對其精熟於胸,試看孔子是如何評價“六藝”的:“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主持人:請老師用通俗的話給我們解釋一下吧。
潘麟先生:好的。這些都是距離現在兩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時期的語句了,我們現在使用白話文,所以對這些先秦時期的文言文很陌生,聽起來覺得很拗口。把這段話翻譯成白話文意爲: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是通達《詩》之故;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是通達《書》之故;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是通達《樂》之故;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是通達《易》之故;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是通達《禮》之故;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是通達《春秋》之故。
主持人:老師,剛纔您說孔子一生致力於教授“六經”,特別是《詩經》,您能舉幾個例子嗎?
主持人:感謝潘老師今天的精彩解讀。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感謝您的收看,下期節目再見。
潘麟先生
關聯視頻潘麟先生講授《大學》第四十三集 《詩經》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