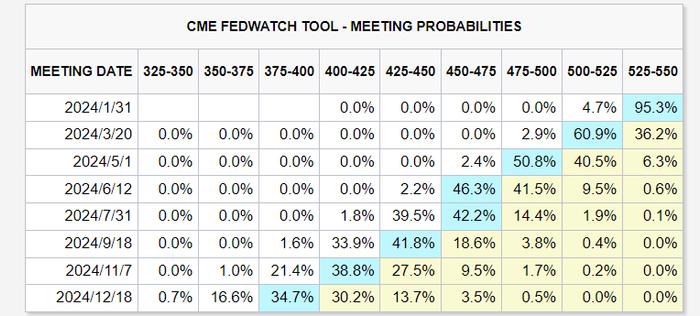深度報道丨中國在美航校學員顏洋自殺事件始末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21期,原文標題《在美航校飛行學員自殺始末》
2019年4月16日凌晨,21歲的飛行學員顏洋在美國航校的公寓內自殺。飛行學員個人悲劇的背後,是高中畢業便與航空公司簽約的“養成生”出國訓練的弱勢局面。
記者/劉暢 實習記者/張佳婧
中國學員在美國航校USAA內學習
重壓下的意外
“最後一次跟我視頻時,他說自己飛得不好,我說該回來就回來。他說行,大不了就轉專業。”在北京打工的李萍沒有盼回遠在美國學習飛行的兒子顏洋。美國德克薩斯州當地時間2019年5月13日上午10點,在150餘名US Aviation Academy(USAA)丹頓校區的中國學員陪伴下,48歲的李萍一襲黑衣,坐在達拉斯殯儀館(Restland Funeral Home)的角落泣不成聲。21歲的顏洋躺在木棺裏,厚厚的劉海仍是生前的模樣,炯炯有神的雙眼再不會睜開。
一個月前,她與兒子隔着手機屏幕見了最後一面。顏洋自2018年4月21日來美國接受飛行訓練,每週都會與李萍視頻。他所在的丹頓校區像一個小村鎮,自今年春節以來,顏洋的同學王鵬見他幾乎整日無所事事,“公寓裏住的基本全是中國學員,有時候白天樓裏只有顏洋一個人,他自己在房間裏喫薯片、看電影”。
顏洋的訓練進度卡住了。他與另外24名航空公司簽約的本科同學,預計在12~14個月內,飛行訓練約230個小時,依次考取私照、儀表、商照三個證。私照又有三個訓練階段,今年春節後,除三名學員已退飛回國,其他同學基本結束儀表飛行階段,只有顏洋仍在私照的第二階段徘徊。從2月5日到4月8日,別人或在學校上理論課,或每隔一兩天便要飛一次,顏洋則只上過4次飛機。“起初他跟我們抱怨,後來我們問他,他就說‘還是老樣子’。”同學們知道,訓練的整體安排以班爲單位,顏洋已遠遠落後其他同學,“原地踏步”於他是巨大的壓力。
“2月4日正常訓練完最後一班,16天后學校爲顏洋安排由主任教員帶飛的Leaderfly。主任教員認爲他表現不好,讓他等待訓練安排。”王鵬向本刊介紹,直到4月1日,他與班長找到私照經理詢問進度,卻因進度滯後,拿到一封停飛警告(reviewboard),並被要求做第二階段的飛行測評。相比其他學員飛8~10個班次之後再考試,因教員經常外出,顏洋這一階段只被安排了3班。“4月8日測評回來,他告訴我們,教員不甚滿意。”
他最後與母親視頻便發生在飛行測評後。但他們並沒爲他過度擔心,既因爲顏洋仍與他們一起看電影、嬉鬧,也因爲他此前也面臨過類似的情況。
顏洋的進度緩慢,從私照第一階段後期就開始了。“他補考經過第一階段飛行考覈後,仍被教員要求同飛,飛行3班後,卻被學校發了一封停飛警告。17天后再被安排飛行,又得一封。”王鵬告訴我,停飛警告累積三次會被建議停飛,送回國內。因此前顏洋已收到過一次,航校於是向航空公司建議停飛。“航空公司則讓航校繼續培訓顏洋,兩方僵持不下,直到顏洋自己‘要求加時自費’,額外花費近3000美元,購買10個小時的飛行時長後,才又進入下一階段。”
“今年三四月份,顏洋每天喫一兩頓飯,他似乎仍準備省喫儉用,再自費買時長。”顏洋的另一位同學李丁說,顏洋也許等不來轉機,此前有先例,若航校再次提出停飛,航空公司就不會再阻止。4月15日晚上,顏洋收到次日早上與私照經理見面的通知,他又一次面臨被送回國的風險。
顏洋的停飛警告中寫明,他英語不過關、降落操作不夠自信、缺乏對飛行的熱情;在顏洋自殺後的航校通報中,聲明顏洋始終未達到培訓水平,早應被送回國。而顏洋的同學們質疑,顏洋既已通過階段考覈,又言“不具備培訓資格”的依據。本刊聯繫航校未得回應。
目前可以的確定的是,4月15日下午,顏洋仍和同學在宿舍看電影,宿舍輪流值日,正好排到顏洋,晚飯後他把廚房收拾乾淨,12點左右上牀睡覺,同臥室的舍友見他睡得很沉,不知他把鬧鐘設到凌晨4點左右。鬧鐘只響了一聲,他就消失在宿舍內共用的廁所裏。4月16日早上6點,一位舍友推不開廁所門,發現顏洋背靠洗手間門,坐在地上,把窗簾的細繩,拴在自己頸部和洗手間的門把手上,自縊而死。
不得已的“留洋”路
北京時間4月17日早上,李萍接到兒子同學報喪的電話,她和丈夫都是江蘇淮安人,分別在北京和無錫打工。他們沒出過國,聽說孩子出事,第一時間買了機票,之後才得知出國需要辦理簽證。半個多月後,在美國領館、航空公司的幫助下,纔來到美國。
顏洋的同學說,帶父母坐飛機本是顏洋最大的心願。而他面臨的壓力也從選擇報考飛行員的一刻便逐漸累積。
顏洋出生在北京,初中回到淮安,高中考到當地重點的淮安中學。那時他已是接近一米八的大個子,在衝擊一本線的班裏名列中上游。顏洋的高中同學王茜向本刊回憶,高三時,學校張貼航空公司招飛的宣傳海報,提到工資高、待遇好,高考分過了二本線就能上。顏洋被翱翔天空的職業榮耀吸引,是他們學校3000名畢業生裏僅有的兩個學生之一。
他選擇成爲飛行員的方式是最快捷的一種。相比大學畢業生與航空公司簽約後,轉爲飛行員,或是個人在指定航空學院自費學習飛行,顏洋這樣的學員被稱爲“養成生”,他們在高考前已通過航空公司的考試,高考達到要求的分數線進入大學後,與航空公司正式簽約,完成理論和飛行訓練後,直接進入航空公司。
顏洋在南京航天航空大學接受前兩年的理論知識。養成生遵循空軍航校的傳統,一進學校便接受軍事化管理,又有針對飛行學員的體能訓練。“我們會爬滾輪、旋梯,讓人頭暈目眩,經常課後還要加練。”王鵬記得,顏洋和大部分同學一樣,萬里挑一地考上養成生,堅持本身成爲克服困難的動力。而飛行專業四年的通識和專業學分,他們兩年修完,在大學的第三年到國外接受飛行訓練。
這是中國航空公司20餘年來,培養民航飛行員的普遍做法。相關資深從業者向本刊透露,“最初中國民航飛行員絕大多數來自中國民航飛行學院。那時每年的飛行學員不到200人,但足夠滿足民航公司的需求。上世紀90年代以來,民航公司發展,國內因爲空域限制,教員和飛機數量也不夠,飛行學院帶頭,在理論培訓後,把部分學員送到國外航校做飛行訓練。如今中國每年培養5000餘名飛行員,有一半兒都要送到國外訓練”。
據相關人士介紹,除空域等客觀條件沒有變化,航空公司的成本也是目前送飛行學員“留洋”的重要原因。“養成生的學費由航空公司墊付。國外的航校更像駕校,而國內的航校在大學內。民航局對飛行教員的要求國內外差距不大,但國內的教員有正式大學編制,國外的教員則多爲兼職,工資差別巨大。國內航校用的訓練飛機標準遠高於國外,對航空公司而言也是一大成本。”
“我們與航空公司籤的是99年的合同,出國的學費先由公司墊付,工作後每月扣除些工資還貸。如果出國期間違約,要支付自己的學費和一定比例的違約金。”李丁告訴我,他們從面試便像走在“獨木橋”上,“如果在國外被停飛,雖然可以回國轉專業,是否賠償也能和航空公司談。但停飛記錄跟隨學員一生,雲執照上會扣5分,5年後才能清零,從此基本與民航飛機無緣。即使轉到航空管制等專業,就業時也會因停飛記錄受影響。若轉到與飛行完全無關的職業,就得重新修學分,延期兩三年畢業幾乎是必然的。”
截至去年,根據中國民航局的審定,美國2000餘所航校中,滿足培訓資格的航校有20餘所。10年內培養2000餘名中國學生的USAA位列其中,但丹頓校區的聲譽在中國學生口中一直不好。“淘汰率不低,教學氛圍還很壓抑。”李丁說,“USAA的面試也是百裏挑一,我們沒有選擇國外航校的權利,雖有三次面試航校的機會,但不確定第一次面試不過後,後面是否仍要面試同一所學校,我們只能全力以赴。”
“沒有紅綠燈的路口”
USAA面向全球招生,不過校園裏有來自中國多個航空公司的200多名學員,幾乎見不到其他國家學生的身影。這座建於2002年的航校,幾乎就是靠中國學生髮展到如今有100餘架飛機、上千萬元的模擬機一應俱全的地步。
書放曾在2009年前到USAA接受飛行訓練,是這裏的第三期學員。他記得自己來培訓時,航校剛從破產的邊緣爬回來,飛機數量不過現在的一半左右,培訓週期也在一年左右。他臨畢業前,二三十人一批的中國學生一年總共能來200人,國際學員相對較少。那時也有刁難人的教員,學員只要爭辯就過不了檢查,大家只當是自己運氣差,後果也不至於無法挽回。他體驗更多的是,當地發達和便捷的民航文化,“相比國內的飛行訓練,美國的訓練更自由,可以降落的機場很多。有時我們想去俄克拉荷馬看場NBA,跟教員說好,直接飛過去,看完球再飛回來,航程就是訓練時長了”。
“不能說中文的規定在那時也有了。”書放說,“‘No Chinese’起初也只是口頭警告,後來發現中國學生英文上不去,便把問題歸結到說中文上,引進扣分制度,抓到說中文就扣分,還要在學生證上打孔,以示‘恥辱’,聲稱打夠多少孔就要停飛,但有的學生證被打得千瘡百孔,也沒見停飛過。”
但明確教育目的的懲罰措施,10年間逐漸變了味兒。當顏洋和同學來到航校時,如果發現學生私下說中文,不僅會罰款,還會拍照到公共區域展覽。“甚至還有體罰,我們有師兄因爲頂撞教員,被罰連續三個星期,每天早上坐5點的校車到學校刷飛機、刷廁所,一直到晚上10點才結束。”王鵬告訴我,這些學生們爲了順利畢業都能忍,最難以忍受的便是顏洋遇到的進度問題,“航校會先給本土學生和其他國際生安排飛行訓練,我身邊有一位國際生,我結束私照訓練時,她剛開始學飛,我基本結束儀表的飛行時,她已拿到商照,甚至考上美國的教員資格了。”
令人詫異的是,同由USAA管理的謝爾曼校區卻有口皆碑,丹頓校區的問題並不普遍。但在書放看來,丹頓校區懲罰學生能夠變本加厲,背後的原因在於,航校完全掌握着中國學員前程的“生殺大權”,“像一個沒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會不會撞車全憑司機自覺”。
相比中國航空公司送來的養成生,美國學員從學飛到進入航空公司,完全依靠累積的飛行時長。“大部分美國學生沒有錢一次性把飛行執照都學完,一般都是邊打工攢錢邊飛。所以他們與航校之間更像商家與顧客的關係,不但三個證不一定在同一所航校學,只要對教員不滿,他們就可以走人,不存在體罰,更沒有強制停飛。”書放如今在美國一家公司從事與航空有關的工作,他告訴本刊,也因爲這樣的制度,美國航校的教員多爲兼職,用於自己攢飛行時長,“甚至有些教員因爲自己要飛行1500個小時才能進航空公司,中國的養成生則只要飛250多個小時,感到不平”。
中國的養成生則不但三個證都要在一個航校學完,也始終有停飛的擔憂。從航空公司的角度看,公費培養的飛行學員是航空公司的“半成品”。相關從業人員介紹,學員淘汰率很正常,他們最在意的是畢業的學員儘快上崗工作,“而航空公司與航校簽訂每個學員的學費,也不似航校招收自費生時在官網上的明碼標價,價格普遍比自費生低。而中國學員佔用教員和飛機的名額,提早送回部分中國學生,能讓航校多招自費生,獲得更多利益”。
養成生的權益難以保障,除南航擁有一所在國外收購的航校,其他航空公司均是把學員全權委託給航校的模式。“我們每一批有一名學生領隊,他每月把學生的飛行情況書面反饋給航空公司。”雖然航校在聲明中稱“中方代理人和代表每年訪問我們學校兩到三次”,但李丁向航空公司反映問題,得到的回覆多是“會和航校溝通”,便沒有下文。
(李萍、王鵬、李丁、王茜爲化名,感謝王湉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