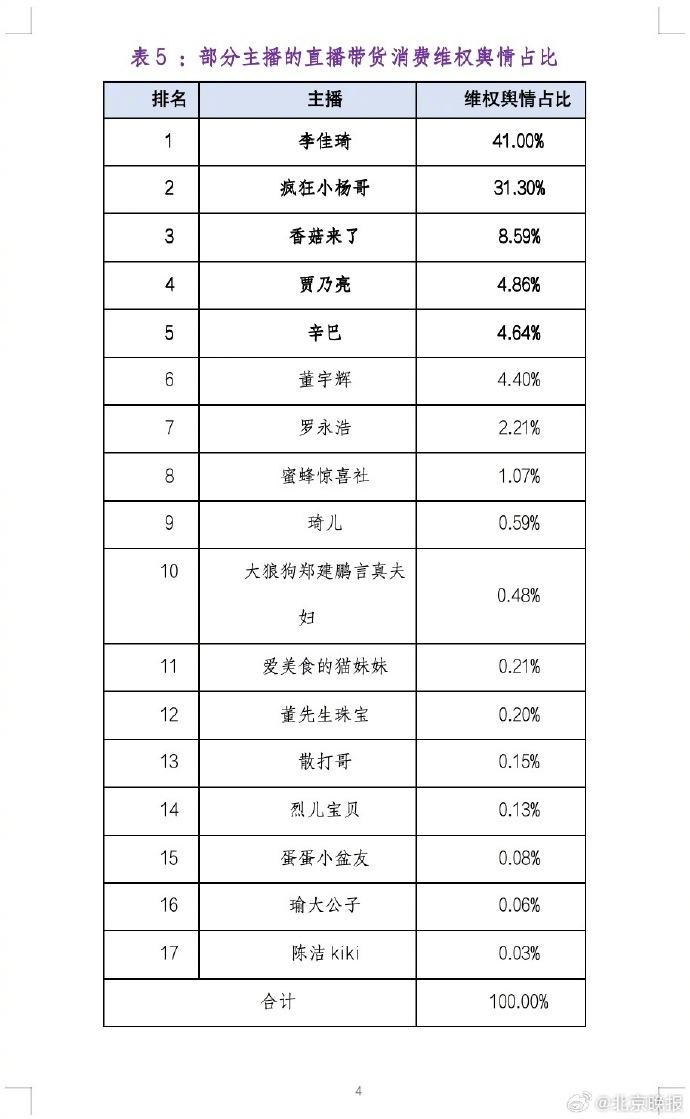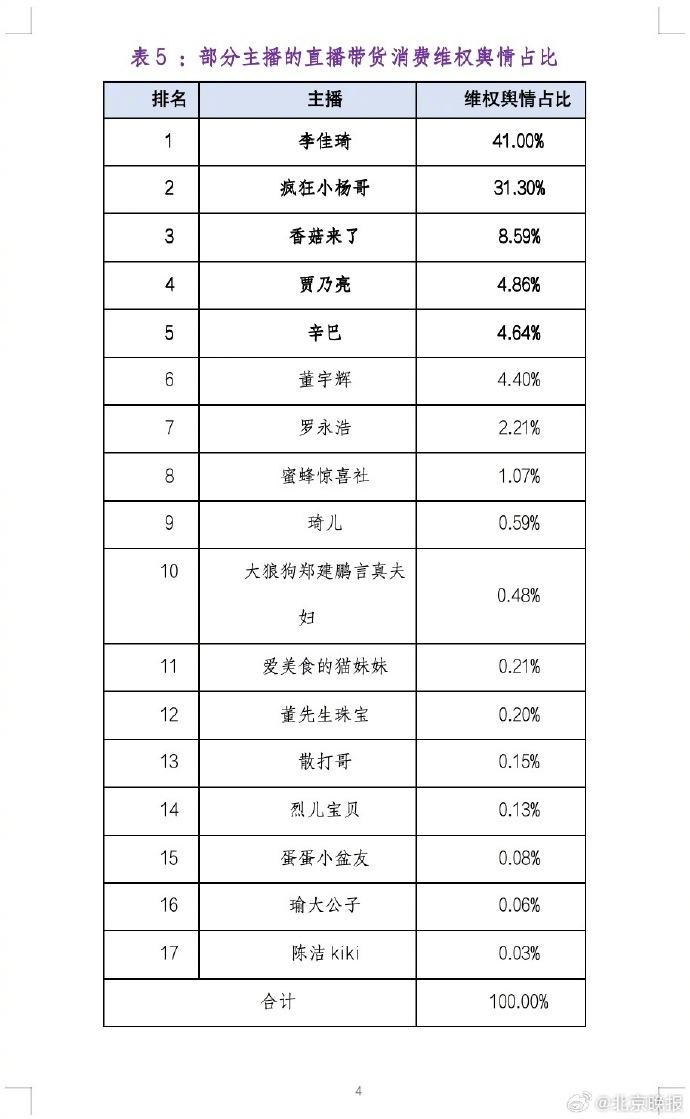男子勸阻廣場舞離世 媒體:別讓無辜者受維權之痛
原標題:“男子勸阻廣場舞離世”,別讓無辜者承受維權之痛 | 新京報快評
從該男子的經歷看,不僅是“善後”維權難,之前的廣場舞擾民維權,又何嘗容易。
 ▲ 圖/新華社(圖文無關)
▲ 圖/新華社(圖文無關)文 | 歐陽晨雨
這又是一起因廣場舞引發的悲劇。
近日,湖南省長沙市一男子因勸阻廣場舞而突發心梗去世,其家屬與事發小區物業簽訂協議,協議中註明物業資助2萬元,最終物業出於人道主義關懷補償了8萬元。對於這一協議,該男子家屬並不認可,稱只是權宜之計,打算回到長沙後起訴物業以及當時跳廣場舞的當事人。
因爲勸阻廣場舞——這件生活中的“不起眼小事”而造成“突發心梗去世”的巨大悲劇,這對當事人家庭來說,的確是無法承受的悲劇。
雖然目前,尚無法釐清廣場舞大媽擾民對男子去世應付何種責任,但是,擾民、爭吵畢竟是誘因之一,涉事的廣場舞大媽通過某種方式來表達一下歉意,既符合人道主義精神,也能給當事人家庭一點心理慰藉。而至今無人道歉,對當事人家庭的確是另一種傷害。
從法律角度看,該男子家屬訴訟維權的訴求理應得到支持。如果有證據表明,該男子突發心梗死亡,與跳廣場舞的當事人發生衝突、物業管理不善存在因果關係,那麼根據《侵權責任法》,對方應承擔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法律責任。
具體而言,應賠償損失包括醫療費、護理費、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等。當然,對於物業方面,之前據協議已給予了“8萬元人道主義資助”,這筆費用將來可從法院判決支付的賠償金額中扣除。
不過,要真正實現維權成功,實際操作起來可能並不簡單。從目前情況看,突發心梗死亡可以做法醫鑑定,但只能證明危害後果,並不能證明與物業方面的管理失職,以及跳廣場舞的當事人過錯有關。
而要證明爭吵與男子突發心梗有關,最有力的證據就是以視頻的形式,證明在爭吵過程中對方有刺激性言語。但問題是監控視頻往往沒有聲音,而涉事對方唯恐避之不及,想要他們自證其罪很難。而即便能找到旁觀者作爲證人,也需要提供其他證據,形成證據鏈,纔有可能被法庭所採納。而舉證的過程,恐怕也並不容易。
其實,從該男子的經歷看,不僅是“善後”維權難,之前的廣場舞擾民維權,又何嘗容易。

因爲“跳廣場舞的隊伍就在家樓下”,從2016年搬來後,他們一家就在“默默忍受廣場舞的音樂”。爲了讓孩子有個學習環境,該男子“跟他們講把聲音調小一點還是可以跳舞的”,卻沒有人聽。物業方面也反映,“有居民跳舞音量過大打擾到其他業主也不是第一次了”,“經常有業主反映噪音情況”。但是,對於沒有執法權的物業,只能出面協調,實際作用很有限。
其實,對於噪音擾民的現象,相關法律不可不謂完備。如《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明確規定,“禁止任何單位、個人在城市市區噪聲敏感建設物集中區域內使用高音廣播喇叭”,“在城市市區街道、廣場、公園等公共場所組織娛樂、集會等活動,使用音響器材可能產生干擾周圍生活環境的過大音量的,必須遵守當地公安機關的規定”。《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違反關於社會生活噪聲污染防治的法律規定,製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處警告”,“警告後不改正的,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
但令人遺憾的是,現實中卻鮮有廣場舞擾民者被制止和處罰的案例,看似嚴厲的法律條款,往往因爲執行成本和維權成本雙高而淪爲了擺設,這也讓不少民衆深受其擾而無法自救。
爲一己私利侵犯公共邊界,是對社會關係的現實危害,如果公權力介入不夠,這一真空就只能由公民自發填補。而公民的這種自力救濟,不僅帶來維權成本過高、矛盾衝突升級等“後遺症”,也無助於廣場舞擾民等問題的真正解決。
要避免此類悲劇再度上演,需要進一步完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在保障民衆跳舞健身權利的同時,有關方面也要加強執法,及時制止不法、不文明行爲,讓違法、違規者承擔行政、民事責任,讓民衆的休息權得到保障。
□歐陽晨雨(學者)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