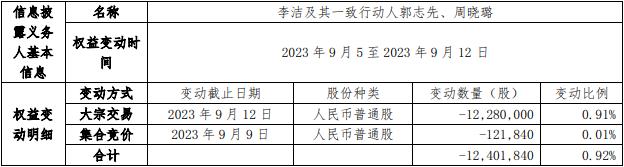疫區擺渡人:再也沒進過孩子房間 他求抱抱我卻不能
(原標題:疫區擺渡人:再也沒進過孩子房間,“他求抱抱,我卻不能”)
經濟觀察報 “今天拉到的醫生是武昌婦幼保健院的,他是我的常客。”2月2日,農曆正月初九,武漢“封城”的第11天,經濟觀察報記者聯繫到了志願者司機李潔。
電話那頭傳來她的聲音,如果不是自我介紹,記者完全聽不出李潔已經50歲了。“有人說我聲音像30多歲的,比較有活力,可能跟心態有關。”
李潔是第一次做網約車司機,講起與武漢的淵源,她說,自己從宜昌來到武漢讀書,畢業後留在這座城市裏,如今經營酒店生意,並在武漢安了家,“我在武漢將近30年了”。
她告訴記者,本來今年春節不打算回老家過的,丈夫就帶着20多歲的女兒提前回宜昌看外婆去了,卻不曾想趕上了疫情,“結果他們回不來了。”
雖然李潔隻身一人在武漢過年,這反倒讓她覺得“沒有後顧之憂”。大年三十那天,她見一個朋友微信羣中丟進來一個二維碼,經詢問是在徵集志願者,“他們說是幫助抗擊疫情的。”對於志願者這三個字的理解,李潔只知道是公益活動,並且自打疫情爆發後,她每天看着新聞裏報道着那些在一線的醫生們,“我們每個人都是社會上的人,抗疫也是我們該做的”她想力所能及地爲醫生們做點事——加入公益志願車隊,駐守社區,接送醫護人員。
50歲的志願者司機李潔成爲了“醫護專車”首批司機中的一位。
當疫情來臨,面對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醫護工作人員首當其衝,奔赴一線。當整個中國,甚至全球都在共助抗疫之時,除了在最前方的白衣天使,有不少人像李潔一樣,主動加入到志願者司機的行列中來,行走在疫區,以保障醫護人員的出行。
“封城”前後
1月23日,武漢“封城”。其實,早在消息還沒公開之前,成冬就感受到了這個訊號。這要從他頻頻接到“大單”開始。
今年37歲的成冬,老家在黃石,如今舉家待在武漢,經營着一家賣飾品、箱包的門店。平時除了去店裏,他還註冊了滴滴跑網約車。
據成冬講述,在武漢跑網約車能接到二三十公里的都是大訂單了,“一百多公里,一個月有一兩單就不錯了。”
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有天早上,我打開滴滴,發現都是幾百公里的訂單。”成冬記不清那天具體的日期,但他告訴記者,那天打電話給他的人“特別特別多”,“他們要離開武漢,去往長沙、黃岡方向的特別多。”
成冬說,當時的網約車還在運營,加之很多武漢人聽說要封城,都慌了,於是“反常”現象發生。他心裏清楚,這些人是想逃離這座城。
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採訪時,成冬說到了他當時的第一反應——買喫的。
“買了很多大米、水果,買了一筐桔子。”家人看成冬買這麼多東西都很喫驚,畢竟他們準備喫了年夜飯就去北京。沒想到,囤的東西成爲了全家人“封城”之後的生活儲備。
在採訪中,成冬告訴記者,他所在的一個車友羣裏,在武漢沒有“封城”之前,就開始招募志願者了,他看到便報了名。“本來招募的都是公司所屬的,但那時候很多外來務工人員的車都開回老家過年去了,招不滿,才允許我這樣以個人形式加入進來。”
“封城”之後,武漢的市內公交、地鐵、輪渡雖全部暫停運營,但整個城市的運轉仍然需要一些基本保障,特別是醫療物資的運輸、醫護人員的出行保障等。
經濟觀察報記者瞭解到,除了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緊急徵集了6000輛出租車解決市民出行不便問題外,包括滴滴出行、曹操出行這樣的網約車平臺,相繼在武漢召集網約車司機組建起了“應急社區保障隊”。
據悉,網約車平臺還紛紛組建醫療保障車隊,免費接送醫護人員。一組數據顯示,截至2月1日,滴滴武漢“醫療保障車隊”已配備200多名司機,覆蓋武漢7家醫院5019名醫務人員;而高德打車在聯合武漢當地出行合作伙伴風韻出行組織公益志願者車隊後,還在2月1日緊急上線了“醫護專車”服務,24小時免費呼叫,專屬且全方位安全護送一線的醫護人員,而李潔、成冬則是這個“醫護專車”車隊裏的首批司機。
“擺渡人”
記者看到,在這些志願者司機中,除了像李潔、成冬這樣的企業老闆,還有不少像代敏這樣的普通職員,在看到志願者車隊的消息後,不懼疫情,第一時間報名加入其中。
在武昌造船廠上班的代敏,今年39歲,平常就是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工作,“平時開車到單位也就15-20分鐘,下班後就在高德上跑一下專車。”
如今和爸爸兩人住在一起的代敏,在12月底時就聽說了疫情,“那時候覺得離自己有點遠,原以爲這個事情不是真的,直到政府發通報,單位也放假了。”
在家裏待了幾天的代敏,每天看着新聞裏報道着疫情愈發嚴重,“我在家就待不住了,想出去做點什麼,想出一點力。”
因爲家中有70歲的老父親在,加之新冠肺炎病毒的易感人羣是老人,當記者問及代敏加入志願者車隊護送醫護人員,是否有風險擔憂時,他坦言,“我屋裏人肯定是擔心的,但知道能夠爲抗擊新冠出點力也蠻支持,就是囑咐我一定要做好防護,不能馬虎。”
代敏說得輕鬆,其實他在報名之初瞞着父親,直到出發前,他跟父親講到了自己的防護措施做得很好,“口罩、手套我都有,我還有摩托車頭盔,衣服我就穿連體的雨衣,雖然有點熱,但我都準備了。”即使要送一些有狀況的人,代敏也不擔心,“消毒片,我都準備好了。”
據代敏介紹,他最多一天曾送了8位醫護人員,“他們上下班的時間都很集中,有時候順路的話,7、8點上班的,我能送上2個。”
志願做司機,本不求回報的代敏,經常會被感動到。
主動加入志願者車隊的代敏,最多的一天裏接送了8位醫護人員。
他曾在駐守的社區裏多次送一位醫護人員,“6點半從家出來,7點到那裏,他給我帶了一個牛奶,兩個麪包。他知道現在外面沒有早點賣,我們可能沒喫,還希望我不要嫌棄。”
除了喫的,還總有醫護人員送給他口罩、酒精。代敏知道,疫情之下,醫療物資尤爲緊張,這些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極大,“看得出來,他們每天忙不停的節奏。”代敏總能從後視鏡裏看到有的醫護人員上車後,不太愛講話,很累的樣子,那一刻,“我就想讓他們早一點回家。”
李潔從全職來做志願司機開始,起初沒有防護服,只是戴兩層口罩。每天接送七八個醫護人員,她也知道從醫院裏邊出來,不是很安全,“我不糾結”,李潔認爲,只要自我保護好,多洗手,每天對自身和車內都消毒就好。“我每天都要把車開到橋上,車窗全打開,通風。”
談及接送醫護人員的點滴,李潔告訴記者,他們聊的基本是一個話題——注意自己,保重身體。
“有的醫生家離醫院很遠,現在疫情比較嚴重,都是在醫院裏住着,不回家,偶爾回家拿點東西,又怕耽擱時間。有的醫生告訴我,她們的愛人、孩子都回老家過年了,而她們選擇留下來,在武漢戰鬥。”接過很多女醫護人員的李潔,覺得自己與她們是一個狀態——留在武漢戰鬥,不同的是,她始終瞞着家人和朋友,她深知自己在做的志願司機這件事,會遭到家人的阻攔。
如今,李潔每天都會和女兒視頻,“她總交代我,不要出門了,外面很危險。”即便如此,只要聽到高德打車上的信息提示,李潔便穿戴好口罩、護目鏡、防護服,做好車內消毒,積極響應出發接送醫護人員。
爲武漢加油
自打疫情爆發,行駛在“九省通衢”的武漢城內,成冬覺得有點陌生。
這個平時可以用熱鬧來形容的城市,相對較堵,“以前上下班高峯期,從武昌到漢口可能走2個小時,現在最多20分鐘。”
近來,成冬都是在義務接送武漢第三人民醫院、湖北省婦幼保健院的一些醫護人員上下班,每天都準時準點。早上6點,武漢的天還沒透亮,成冬便出了家門,他要先對車內進行全方位的酒精消毒,然後按時到達社區,7點送醫護人員上班。
“現在路上基本沒車”,對於目前的出車情況,成冬甚至說到,“我永遠不會遲到,說多長時間就多長時間。”
這是成冬志願者服務工作中的一次自拍,近來的他每天都是早上7點準時接送醫護人員去上班。
這些天的接送,成冬與醫護人員之間已經建立起了非常信任的關係。有醫生會跟他講到自己的壓力,甚至因同科室的同事感染而心情低落;也有醫護人員感激成冬的接送,不僅會送口罩、藥品等防護品給他,還會指導他一些專業的防護知識。
在成冬的行車記錄視頻中,記者看到,不少醫護人員下車時會暖心地對他說,“開車注意安全”,而他會像親人朋友一般招呼說,“什麼時候下班了,給我發微信,我來接您。”
疫情之下,遠離風險本就是人的本能,但在武漢城內,不止李潔、代敏、成冬,還有數以千計的志願司機們,逆行其中,奔走在危險的社區與醫院之間。
成冬的孩子纔出生不久,老婆和丈母孃對於他義務接送醫護人員的決定並不太支持,“畢竟醫護人員也是高危人羣”,但他因2003年曾在非典期間進行過志願防護,基於比較專業和謹慎的安全防護經驗,主動響應,從不懈怠。
他爲此準備了專業的手術用手套,每次回家都會把外套、褲子,甚至帽子、圍巾換掉或放在通風的地方,“最近高德打車還協調了一批全身用的防護服,更加安全了。”
嘴上雖這樣說着,但在採訪過程中,記者得知,以前每天都會抱着孩子玩的成冬,自打參加志願車隊起,就再也沒有到過寶寶的房間,更不會接觸寶寶,“我不會抱他,即便他要抱抱,我也不能。”
一組數據顯示,如今參與的志願者近5000人,而成冬只是其中再普通不過的一位。但他告訴記者,他們志願者都有一個信念,“明天會更好。”
“加油”兩個字,是成冬近來對醫護人員說得最多的兩個字,他發現這些在一線流汗付出的醫生們,會因爲這樣簡單的鼓勵而感動好多天,他認爲這是傳遞正能量的好方法。儘管他們不曾摘下口罩,看清對方的模樣,但成冬知道,上下車的那一刻,一個點頭、一個相視的眼神、一聲囑咐,都是彼此間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