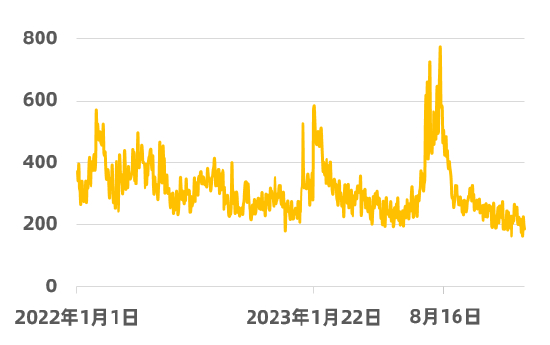玩遊戲的老人們

歡迎關注“創事記”微信訂閱號:sinachuangshiji
文/池騁
很少有人把玩遊戲的老年人當作真正意義上的玩家。他們在遊戲裏的生活、他們對遊戲投入的感情、他們在遊戲中收穫的意義,長久以來都是被忽視的。就像在家庭中的角色一樣,老人們不太爲自己出聲——但他們是重要的存在。
本文爲“編舟計劃”系列文章第7篇。編舟計劃,記錄遊戲與時代,只收集與遊戲相關最優秀的文章。
老年人在遊戲玩家中是一個幾乎隱形的羣體。
每個人的身邊都有幾個玩遊戲的老人。可能是那個癡迷於在線象棋、抱着手機不撒手的爺爺,也可能是那個爲了領取體力、每天凌晨都會分享遊戲截圖到朋友圈的外婆。但很少有人把這些老年人當作真正意義上的玩家。
有些人也許會關心老年人的遊戲時間是不是太長,也有些人可能會關心他們每天是不是睡得太晚,但很少有人問過他們對遊戲投入了怎樣的感情,在遊戲中得到了什麼,又如何看待遊戲的意義。
長久以來,針對老年羣體的玩家畫像是缺失的。在屏幕的另一端實力突圍的可能是一位打到了“榮耀皇冠”的退休阿姨;在《我的世界》裏被小男孩表白的可能是一個年過60的“小姐姐”。一些在我們看來已然是老古董的遊戲,對他們來說依然新鮮有趣:在《黑道聖徒2》裏打了2500小時的大爺究竟在想些什麼?面對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這些玩遊戲的老人們是不是比其他老人走得更前?
通常情況下,老人們都是沉默的。又或者,沒有多少人關注他們想說什麼。
1
退休之後,邢大爺明顯感覺到自己關注新事物的心力大不如前了。
邢大爺在鐵路上工作了40年,剛退下來的那兩年,他天天出門找人打麻將,偶爾去別的城市旅個遊。他隱約知道外面的世界發展越來越快,但他不關心這些。
“他們老跟我說,把網絡這個東西弄弄好,什麼都方便。購物方便,看東西方便,知道的東西也多。”邢大爺說,“我說,我幹了那麼多年鐵路什麼不知道?”
外甥周林一個勁地慫恿他,學學這個,玩玩那個,還直接把自己Steam帳號分享給他,先篩出他的電腦配置跑得動的,再從中挑選出他可能會喜歡的遊戲,讓他挨個嘗試一遍。
結果,邢大爺被《黑道聖徒2》擊中了。從2017年12月份至今,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他在《黑道聖徒2》裏花了2500多個小時——也就是說,平均每天花上將近4個小時。“有時候玩一天,有時候玩着玩着就玩到半夜,有時候上去了就下不來。”邢大爺告訴我。

在邢大爺心目中,《黑道聖徒2》排第一,“其他都只能排後邊”
他被這個遊戲深深地迷住了。“這裏頭設計的人物好像都有思想,我做什麼動作,他回一個動作,我感覺老麼奇怪了,弄得挺神祕似的。”他覺得這個遊戲中可鑽研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僅僅通關還不夠,他對裏面的小遊戲也非常好奇,老想着“把這東西徹底玩完,看看裏頭的內情到底是怎麼回事”。
像着了魔一樣,一天到晚,邢大爺心裏頭就老琢磨這個遊戲。“心頭老掛着這個事,出門辦事也只想着趕快回家玩。”
邢大爺對《黑道聖徒2》的執着令外甥周林感到迷惑又無奈。他試圖給邢大爺推薦其他的遊戲,但邢大爺就是不肯換。
周林給了我一張清單,上面記錄了邢大爺嘗試的每一款遊戲,以及邢大爺不喜歡它們的原因。“《Portal 2》,不感興趣;《足球經理2018》,不想當官;《ICEY》,難操作,字太小;《這就是警察》,節奏太慢;《熱血無賴》,難操作,只看景,能回憶旅遊;Xbox 360體感遊戲,不想活動……”

周林給我的“舅姥爺玩過的遊戲”清單
清單上有20幾款遊戲,但在邢大爺眼中,這些都不如《黑道聖徒2》“來勁兒”。就算是“黑道聖徒”系列,他也獨獨鍾情於2。周林給他裝上了更新的3和4代,嘗試以失敗告終,“他說3和4劇情太扯淡”,周林對我說。
提起自己對於《黑道聖徒2》的着迷,邢大爺頗爲自得。“周林昨天還來我這兒,又說讓我換個遊戲玩,我說不換,肯定不換,有生之年不可能換了,別的遊戲都換了也不能把它換了。”
邢大爺也知道《黑道聖徒2》是個老遊戲,“我聽他們說,這個遊戲是09年的,早已經過時了。”但這並不能改變邢大爺對這款遊戲的執着,“我也不知道它的設計者後面給留的什麼懸念,我就對這個挺感興趣。”
“怎麼?你們對這個事不感興趣嗎?”邢大爺問我。
2
劉阿姨玩的遊戲同樣也非常古老:《祖瑪》《空當接龍》《植物大戰殭屍》……這些遊戲她輪換着玩,每天要玩上六七個小時。
劉阿姨起初不怎麼玩遊戲,但當女兒去了北京工作之後,只剩下丈夫、婆婆和她3個老人在家,她感覺家裏一下子變得冷清起來。“我可不得搞得熱鬧些嗎?”爲了哄老太太開心,劉阿姨玩起了一些小遊戲,有時候老太太在一旁看着,有時候也和她一塊玩。
“原來我跟她奶奶下跳棋、打撲克,後來她奶奶眼睛不好了,只能看得見球了,所以我就陪她打《祖瑪》,老人家高興。”
“高興”二字始終貫穿着劉阿姨對於遊戲的感受。一開始,她玩遊戲是爲了讓上一代高興;老太太幾年前去世後,她自己一個人玩,越玩越喜歡,心裏頭也高興。每天把家裏的事情做完,其他時間都在電腦前打遊戲。
對劉阿姨來說,玩遊戲也是在學習新鮮事物——雖然她玩的那些遊戲已經不再新鮮了,但她依然覺得有意思。她最喜歡的遊戲之一是《植物大戰殭屍》,“說實在的,我給製作遊戲的人叫好,你知道吧,這個人他弄的小殭屍也太好玩了,不跟你吵架,不給你發脾氣,你喜歡玩哪個就玩哪個,錘殭屍錘得我可高興了。”

《植物大戰殭屍》在許多年前曾經流行,至今還能給劉阿姨帶來無窮快樂
她時不時會讓閨女給她下載新遊戲,自己一個一個琢磨着玩。“比方說《憤怒的小鳥》《水晶連連看》什麼的,反正我要學的好多,不會的我都學。”現在手頭上的幾個遊戲,劉阿姨天天都打,除了覺得遊戲好玩以外,“我也怕我忘掉怎麼打”。
劉阿姨住石家莊,離北京不遠,但跟女兒還是不常見面。“見她一面不容易,見了她以後我光想學點東西。”劉阿姨總盼着女兒多回來幾趟,“我要跟她在一起,我老早學會好多東西了。我不知道她腦袋瓜裏到底有多少東西,反正我見了她就得趕緊學。”
以前劉阿姨還有更豐富的娛樂活動,比如中老年迪斯科,她跳了整整17年。但後來搬了家,從橋西搬到橋東,舞友們都留在了另一頭。還有一回,她在戶外玩得太過頭,又是跳舞,又是打羽毛球,又是打籃球,“這麼一搞,後來腿就出了毛病”。
有了遊戲以後,劉阿姨就算在家待着也總有事可做。“這個小遊戲不是一般地好玩哦!”劉阿姨拔高語調對我說,“你知道嗎,我坐在這兒就想先打它們一會兒。”

劉阿姨對《空當接龍》也頗有心得:“這遊戲看着簡單,要是心靜不下來,半天也解不開一個。”
劉阿姨不覺得遊戲分什麼老年人還是年輕人,或者分什麼新和舊,“各人有各人的脾性,誰跟誰喜歡的也不一樣,管不着別人。”劉阿姨說,“我們成天不就是爲了身邊的人活着、也爲自己活着嗎?大家玩着,高興就行。”
3
朱阿姨後來才明白,《我的世界》這個遊戲,“玩家們的年紀都蠻小的”。這些小朋友們有自己的規矩:在這個低齡玩家佔絕對多數的遊戲圈裏,像她這種年齡的老人家是不太受歡迎的。
之所以會被人識破,是因爲她一開始的遊戲ID叫作“愛妞寶的婆婆”——她有一個叫作妞妞的外孫女。玩了一段時間,她加入了幾個遊戲QQ羣。羣裏的小孩子們看到這個名字,問她“你是嬤嬤嗎”,她沒什麼心眼,回答“是呀是呀”,立馬就被踢了出去。
爲了能夠和小朋友們一起玩,朱阿姨趕緊把她在遊戲中的名字改成了“寶莉小馬”,因爲她喜歡看那個動畫片。她還向外孫女妞妞請教,妞妞給她支招:“婆婆,以後再有人問你年齡,你就不要說話。”
朱阿姨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玩《我的世界》,這個遊戲是兒子給她推薦的。“那個時候我沒有事做,心裏面蠻寂寞的,覺得很空。”朱阿姨說,“兒子就給我下載了這個‘MC’,說老媽你可以在裏頭種種田、養養貓什麼的。”

朱阿姨喜歡遊戲裏的各種厲害的建築,保存了許多
自從有了這個遊戲,朱阿姨幾乎每天都玩——在我給她打電話的時候,她正在遊戲裏生氣:房間裏的牀昨天好像被人睡過了,她被莫名其妙地傳送到了主城。爲了接受我的採訪,朱阿姨表示可以暫時掛機一下。雖然在掛機的狀態,朱阿姨還是放心不下,時不時地回去看一眼。
“姑娘你等一下哦,有怪來了。”朱阿姨說,“我正掛機呢,他們把我送到曠野上了……等等怪要來把我打死掉了,我上去跟他們說一下哦。”
這樣反覆了幾次,朱阿姨一會兒查看一下自己的狀態,一會兒給遊戲中的其他玩家留言,委託他們解決自己“牀被人睡過了,回不去了”的問題。在電話那頭,我聽到朱阿姨耐心地給搗亂的小朋友發語音:“你怎麼睡我的牀呢?我都寫到牌子上了,‘寶莉的牀,謝謝,別睡我的牀’,你還睡!雖然你昨天給了我兩個村民,我非常感激你,但是你把我趕出來了,我怎麼辦,對吧?”

在《我的世界》中,“你家進熊孩子了”被稱爲“就算是大神聽到也崩潰的話”——朱阿姨時不時也會碰上這個麻煩
朱阿姨的聲音很年輕,只聽聲音的話,說是二三十歲也不會惹人懷疑。換了新名字後,朱阿姨算是在遊戲中站穩了腳跟。她在遊戲裏的好友列表越來越長,加的QQ羣也越來越多。
小朋友們只當她是年紀稍大的“姐姐”,一到下午,朱阿姨的QQ就熱鬧了起來,很多小朋友來敲她:“姐姐你不玩遊戲嗎?玩不玩呀,玩不玩?”朱阿姨總是禁不住這樣的呼喚。“看他們那麼熱情,我就上游戲跟他們一塊玩了。”
“姐姐”甚至遇到過要跟她“交朋友”的男孩。
“有時候碰到那些不太懂事的男孩子,說姐姐我們交朋友吧,我說我們不是已經是遊戲好友了嗎?他說我們交另外一種朋友。”朱阿姨笑着說,“我說不行,我多大呀,你都沒見過我,怎麼交朋友?他說,交朋友不就可以見面了嗎?”
朱阿姨心一軟,差點就要跟他講出實情。“我想跟他說,我還有自己‘灰暗’的一面呢!”但想了想,她還是作罷了,“一說他們把我踢出去的話,我就沒得玩啦!”
遊戲裏的朋友們對朱阿姨而言特別重要。剛開始玩《我的世界》時,朱阿姨特別害怕怪物,“看到怪我就跑呀,我也沒有好的武器,都是自己砍樹,做一些木頭的工具之類的,又沒有盔甲什麼的,很慘的。”一個人開創造模式玩,朱阿姨也覺得有點無聊,“在天上飛來飛去的,看到怪我又不敢下來”。
跟朋友們玩在一塊後,朱阿姨在遊戲中體會到了幸福感。“他們幫了我很多。有時候看到我,他們知道我怕怪,衝到我前面就把怪打死了。”朱阿姨說,“我最近玩‘空島’嘛,掌握不好自己的步數,不小心就掉下去摔死了,摔死了然後又重生,後來他們那些小男孩也會幫我把路開得寬寬的,然後跟我講,小姐姐你不要往邊上走。”
“他們真的蠻關心我的,有一種暖心……那種暖心的感覺。”朱阿姨說,“玩了‘MC’之後,我沒那麼寂寞了。”
4
就像被踢出羣的朱阿姨一樣,遊戲的世界對待老年人可能並不友好。老年玩家在遊戲中常常會遭遇不同程度的年齡歧視。
尤其是在玩線上多人聯機的遊戲時,老人們往往會很快地意識到,自己的真實年齡在遊戲的世界裏是個敏感詞——而這種歧視幾乎就是衝着年齡來的,往往與實際的遊戲水平無關。
在《和平精英》中最好戰績打到過“榮耀皇冠”級別的李阿姨也生怕別人知道自己的年齡。“有時候他們聽我說話的口氣,會覺得我有點年紀。” 遇到這種可能會“暴露年齡”的情況時,她一般就含混過去,“我就告訴他們,是啊,我是你姐,不是你妹呀……我是真的不敢告訴他們年齡,我怕他們知道了以後,就不和我玩了。”

李阿姨以前從未課金,她告訴我,過了這個賽季,她也打算開始買些新皮膚了
剛開始玩的時候,李阿姨老是不敢跟別人打,打四人排位時她總揣着擔心,“變成人家的累贅不太好”,所以等兒子有空的時候,就讓他帶自己一把。兒子也有一羣朋友一起玩,就把她拖到那個羣裏去玩了幾天。
“他們一幫年輕人都特驚奇,問我:‘阿姨你也會打嗎!’”李阿姨說,“我看不到他們的臉,但聽他們的口氣就知道他們很驚訝——好像在說:怎麼這麼大歲數的人還在玩這個遊戲!”
李阿姨連忙對他們說:“我很菜的,我跟你們混,跟在你們後面就行了。”
沒玩幾次,李阿姨就發現,這幫年輕人工作都忙,人總是湊不齊,不能經常陪她玩。打了幾天,李阿姨覺得在他們那裏學不到東西了,提高不了打遊戲的水平,就去找直播看,跟着主播們學。
“剛開始真的很菜,有人過來,我聽到聲音連東南西北都搞不靈清的。”在主播們的“指導”下,李阿姨的遊戲水平迅猛提升。“直播裏面它會教你很多東西!你去看這些主播們打——雖然他們都是很剛的,但也會教很多很多東西,戰術、戰略都得到了提升。”

從跟在別人後面的“菜鳥玩家”到如今能夠獨當一面的“榮耀皇冠”選手,李阿姨的水平在短時間內突飛猛進
在普遍傾向於休閒遊戲的中老年女性玩家中,李阿姨對《和平精英》的愛好顯得有些特別。李阿姨對打槍的喜好要追溯到幾十年前——上世紀90年代初,20多歲的李阿姨在中國電信做話務員,參加過通訊兵的預備役。“我那個時候喜歡上打槍了。我們有打實彈的實戰演習,我都打得挺好的,所以看到玩槍的遊戲我就很感興趣。”
如今,她在遊戲裏有了一些固定的戰友。他們的年紀有大有小,但就像李阿姨沒有告訴他們自己的實際年齡一樣,李阿姨也不太清楚他們的具體情況,只能猜個大概。李阿姨很滿意目前的狀態,“太遙遠的東西也沒必要搞清楚,玩玩可以,他們要加微信我都不加的”。跟線上的朋友們相處的時候,她始終維持着一定的模糊地帶。
李阿姨早已不跟兒子和他的朋友們一塊玩了。“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嘛。” 她被同鄉的朋友拉到一個叫作“Welcometo 浙戰”的兵團裏,裏頭都是浙江人,除了日常穩定的搭檔以外,李阿姨有時也會和兵團裏的人一起玩。
“我老公經常說我一打遊戲就嘰裏呱啦,因爲我戴着耳機自己說話聲音有多響也不知道,就跟着裏頭的人一直嘻嘻哈哈,他老說我吵的。”李阿姨笑着說。
5
一方面,老人們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越來越多地接觸遊戲了;另一方面,那些原本就玩遊戲的人也變老了。
90年代,雨哥就已經買了紅白機,玩上了當時流行的《魂鬥羅》和《超級瑪麗》,“這個可能是最早的遊戲機了,不知道你們這代玩過沒有”。後來他又置辦了電腦,“有了電腦就開始玩‘生化’,玩‘極品飛車’……對了,‘CS’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玩的。”雨哥說,“電腦就是玩遊戲最好,最考驗電腦硬件的不都是遊戲麼?”

雨哥在幾十年前就是主機玩家加PC玩家
雨哥以前是工程師,2000年出頭那會兒,經常跑到各個地方修高速公路。有一回住到了山裏,他就跟手下幹活的小夥子們弄了幾臺電腦,連上網線一起打CS。“那時候沒有無線網,我們就連個局域網,沒事幹就玩呀,住山溝裏頭,離城裏50多公里,也只能玩這個。”雨哥說,“一打發現我級別比他們還高,這些小夥子晚上沒事兒就拉着我玩,好傢伙,完了非請我喫燒烤。”
後來他買了PS3,“那會兒我跑外地工作的時候,來回坐火車坐飛機我都一直帶着那玩意兒。”到了單位,他就把遊戲機接上電視玩。
作爲一名老強者,雨哥一直都走在時代的前沿,遊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從長城386時代就已經接觸了電腦,在單位裏學制圖、學辦公軟件、學五筆輸入法,他都比人更快;至今用的電腦也是用兒子“淘汰下來的破玩意兒”,自己買零件拆裝,熟練得很,“全都自個兒弄”。
他在《穿越火線》裏打了足足11年,去年練到了滿級——五星大元帥。因爲打得好,他去年被招進了一支戰隊。跟遊戲裏“那些名字花裏胡哨”的戰隊不同,雨哥的這一支戰隊名字樸素得多,叫作“老年夕陽紅”。瞧這名字,“我估摸着裏頭的人可能歲數都不小”,雨哥說。

雨哥受邀加入了戰隊,但在遊戲裏他還是更喜歡單打獨鬥的“獨狼”路線
加入歸加入,雨哥在戰隊裏掛了個名兒,但幾乎從不參加戰隊的活動。“他們還要訓練什麼的,我可沒時間。”他喜歡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尤其是滿級以後,雖然還能接着往上升,“上面還有個紫金大元首呢”,但已經打到這份上,他也不太着急了,每天上游戲就感到很威風。
“我這打人家那簡直——我跟你說,那不一樣的!我以前就是受虐,現在虐別人,那能一樣嗎?”雨哥說。
退休之後,雨哥基本上都在專攻《穿越火線》,每天會玩上五六小時,但每隔一兩個小時他就會休息一會兒。“每一把大概半個小時,打三四把我就不打了。”雨哥說,“打到那會兒其實腦袋是懵的,脖子也硬了,老是朝着一個方向,一轉頭那個骨頭就咯咯響。而且按着鼠標的時候小指頭一直是伸直的,打的時間長了手指頭彎都彎不過來,還得用手掰它一下子……不得勁兒嘛。”
在休息的時候,雨哥也閒不下來。“我還得磨戒指、畫素描、彈吉他呢,玩相機我也挺內行的。”雨哥說,“我還有好多其他事兒,以前還爬山徒步,北京的山我都爬遍了。”
對雨哥來說,遊戲只是他退休生活的娛樂項目之一。“遊戲嘛,你適當控制它的節奏,就是個健康愛好。”因爲有着這樣的生活態度,雨哥認爲自己至今也還算是走在時代的前沿。什麼淘寶網購、移動支付,雨哥都是最早的那一批用戶,“這些東西能有多難哪?你老覺得這些東西挺難不去接觸,這個也難那個也難,最後啥也幹不了了。”
“社會在進步,你不能當一個啥都不知道的人。”雨哥說,“咱得跟上時代是吧,不能讓時代給咱落了。”
他不擔心自己有一天會玩不了遊戲,回答得十分爽快:“人生這個路,大傢伙都差不了多少,玩不了就玩不了了,也沒什麼遺憾了。這麼個歲數,沒有什麼放不下的東西。”
至少在當下,雨哥說,“你得興奮起來”。
6
對於老年人玩遊戲,一直有一個流行的觀點,就是遊戲對老年人有用。相關的討論在《Pokémon Go》風靡中老年人羣時曾經達到一個頂峯,癡迷於抓小精靈的老人們爲了遊戲走出家門,既鍛鍊了身體,又找到了與當下的社會接軌的方式。
如今,與老年人相關的遊戲研究越來越多,大部分都聚焦於遊戲的功能屬性上。有的遊戲能夠提高老年人的反應速度和認知能力;有的遊戲能夠促進海馬體灰質的產生,對緩解老年癡呆症有作用。因此,遊戲常常被當作一種治療的手段。

在國外,遊戲作爲一種促進老年人健康的方式更加流行
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研究的成果的確爲遊戲洗脫了一些“原罪”,但也形成了一種慣性:彷彿談到老年人和遊戲,“功能”和“效用”就是唯一的打開方式。
當然,只要保持在一定的遊玩程度,遊戲對於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是有幫助的。當我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老人們往往會立刻告訴我,遊戲對他們頗有益處。
“最起碼……最起碼手沒那麼笨,腦袋也沒那麼笨吧。”雨哥對我說,“這個手指啊,你來回操作,上躥下跳、開槍瞄準,都需要一定靈活度。”
“人的時間是有限的,你在家裏玩了遊戲,其他的一些事兒就玩不了了。”雨哥笑着說,“像抽菸、喝酒、賭博,可不就避免了嗎?”
對於這些老年人們來說,遊戲的效用使得遊戲成爲退休生活的娛樂選項之一,但他們會一天一天地玩進去,還是因爲遊戲本身給他們帶來的樂趣。
“開心!玩了遊戲就非常開心。”朱阿姨告訴我,在自己玩遊戲之前,她討厭兒子玩遊戲,只是從原則上理解“遊戲是孩子的天性”,只要不影響功課,她就不干涉。在自己玩遊戲之後,她才明白了遊戲的魅力。
朱阿姨讓我加她的遊戲QQ號,進她的空間看看。她的狀態和相冊裏除了外孫女的照片以外,幾乎都是《我的世界》有關的圖片,有的是玩家在遊戲裏建造的怪建築,也有她自己的遊戲截圖。
“我看到這些照片的時候,心裏面就會激動。”朱阿姨說。

朱阿姨相冊裏存的遊戲畫面
在大部分的時間裏,老人們對自己的遊戲時間還是有所剋制的,他們也總會找到各種各樣的方式來調劑。有時候是在做飯,“蒸上包子之後,過幾分鐘我就得放下游戲去看一眼”,劉阿姨說。有時候是其他的娛樂活動。“我打太極拳、游泳,還在家裏養了一大堆花。”李阿姨告訴我,“下午我一般吹葫蘆絲,葫蘆絲練好了我纔去玩遊戲——我覺得《和平精英》和練葫蘆絲也差不多的,都講究聽力和反應。”
有時候玩得過頭,邢大爺偶爾也會感覺到身體健康狀態不太理想。眼睛、頸椎、腰,在電腦前坐得久了總會出點毛病,但邢大爺對這些不太在意。“幹鐵路的時候也是東跑西闖的,這麼多年都習慣了,不在乎這些。”邢大爺說,“遊戲打久了,有點問題也不要緊,治不就完了。”
7
老年人是一個非常龐大、非常多樣化的羣體。當我們將目光放在這些老人身上,試圖瞭解他們在玩什麼、想什麼,並且爲他們發出一點聲音的同時,我們也意識到這些老人的背後是一個更廣闊、更多元、更難以觸及的社會圖景。事實上,能夠被我們看到的這些老人幾乎是老人中狀況最良好的一批:他們多半曾經從事着一份體面的工作,退休後也有着充實的活動安排,與子女關係良好,經濟上較爲寬裕,生理和精神狀態都還算健康。
這顯然不是巧合。從某種程度上,不是他們選中了遊戲,而是遊戲作爲一種具有科技屬性的現代產品,只有“符合一定條件”的老年人才能好好享受到遊戲的樂趣——不僅玩,而且是健康地玩。

參與電競的老年人之所以能成爲話題,正是因爲他們是罕見的老強者——但並不是每個老人都這麼強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資料顯示,我國目前60歲及以上人口將近2.5億,其中超過4000萬是失能失智老人,這意味着他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和基本的認知能力——這一部分的老人只會比其他老人更加沉默。如果他們也玩遊戲,那麼遊戲在他們生活中的地位會不會更加重要?
另一個經常被忽視的羣體是獨居老人。他們或許身體和頭腦都還健康,但他們的情感需求卻得不到滿足。
“如果從情感寄託的角度上講,這樣的老人有沒有權利主動選擇不跟外界溝通,而是沉迷於一些能夠給他提供補償作用的遊戲?當他們失去了過去在工作中那些良性互動、有來有往的社交關係,有沒有可能在遊戲中尋找作爲社會角色的另一種存在感?”老齡社會30人論壇祕書長唐穎認爲,對於老年人玩遊戲的現象的探討應該有更多的維度,對於老年人羣體也應該有更多人文角度的關懷。

當老年人成爲遊戲愛好者,他們玩起來也是認真的
唐穎認爲,當我們討論老年人玩遊戲時,更合理的劃分不是按照年齡,而是按照生存狀態。隨着醫療水平的提升和人均壽命的延長,人並不會一過60歲就變成失去生活能力的傻瓜。許多老人在退休之後仍然處在活力充沛的健康老齡期,正要開啓自己的“第三人生”。
“對生存狀態好的老人來說,他們玩遊戲的需求,我認爲跟其他所有玩遊戲的人的需求是一樣的。”唐穎說。但事實上,許多老人玩遊戲的需求在現實生活中不被身邊人理解,而他們在遊戲裏也要隱瞞自己的年齡,以獲得其他年輕玩家的接納。像朱阿姨一樣成功地和小朋友玩成一片的老年人自然很“酷”,但爲什麼只有夠“酷”、懂得如何融入年輕人的老人們纔有資格享受到遊戲的樂趣呢?
“老年人在遊戲中遭遇的年齡歧視其實反映了社會的公共問題。”唐穎告訴我,“我們如何去對待年長的人?我們如何理解年長的人的一些社會行爲給我們造成的影響?”
隨着社會逐步走向老齡化,這樣的問題將會變得越來越重要。根據全國老齡委2015年發佈的《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總報告》,我國的老齡人口將會不斷增加,到2053年達到峯值4.87億人,在本世紀的後半葉將一直維持在3.8億到4億之間,占人口的三分之一——那正是我們這一代人老去的時間。
唐穎告訴我,她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我們今天的年輕人也會變成未來的老人”。此刻正在有着話語權的這一代人,也會走向蒼老,走向退休,走到時代的聚光燈之外,變成又一個沉默的邊緣羣體。
“所謂的前輩們,也只是活在自己的時代裏。在合適的時間點,他們也擁有過自己的話語權。爲什麼隨着年齡的增長,他們就要被自然而然地淘汰掉,被漠視、被歧視,甚至被敵視呢?”唐穎告訴我,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兩個方面的,一個是年長的羣體要儘可能地跟上時代的變化,另一個是年輕人要對老年人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因爲所有人都會變老。
就像採訪中這些老年人一樣,曾經他們可能是時代的“弄潮兒”,玩的都是最新的遊戲機,趕在所有人前頭;如今他們可能連學習那些不再時髦的遊戲都感到費勁,不敢在其他玩家面前暴露自己的年紀,或者更願意守在一個10多年的老遊戲裏一天一天地玩下去。
8
1996、1997年那會兒,邢大爺40多歲,給兒子買了任天堂的遊戲機,自己倒玩上癮了。“那時候不合眼地玩,玩迷了。什麼‘俄羅斯方塊’、‘超級瑪麗’系列,買了很多遊戲卡,插卡玩的。”家裏買不起兩部遊戲機,邢大爺跟兒子搶着玩。
他喜歡玩兒,不止玩遊戲,也玩其他東西——但由於條件的限制,這成了他在年輕時沒能完成的夢。“年輕的時候,我好這個好那個,吹拉彈唱、琴棋書畫哪個不好?也好玩遊戲。但那會兒我淨忙着上山下鄉,要麼家裏窮沒條件,要麼根本就沒這些東西。”邢大爺說,“說實在的,全耽誤了,沒趕上好時代。”
到了退休的歲數,條件是有了,但邢大爺感到自己對於新鮮事物的渴望也差不多消失了。一開始,他對於現在的科技產品根本提不起興致,嘴上說着“我幹了這麼多年鐵路什麼事情不知道”,事實上他心裏清楚,“自己已經沒那個勁頭了”。
“對這些事情不熟悉了,不感興趣了,腦子不好動了,人不好鑽研了。”邢大爺對我說,“昨天我還在說,電子產品淘汰太快了,根本就跟不上,要是沒有年輕人帶着,你進不去。”

唯一讓邢大爺感覺“進入意境”的只有《黑道聖徒2》
在外甥的鼓動下,他開始用手機,玩電腦,但他喜歡打的遊戲也就那一個。“對這個遊戲,我肯定就千方百計動腦子,我鑽進去玩,但對其他東西我就不想動腦了,覺得自己不是年輕人那塊料了。”
在邢大爺還年輕的那幾年,他工作忙,沒時間想別的。每天上班路上,他都會經過大連友好廣場那一塊。“那一片全是遊戲廳,那時候大家都在遊戲廳裏打遊戲,你知道吧,什麼賽車,什麼殭屍,那畫面確實好看。”
遊戲廳裏的“殭屍”給他留下的印象很深。退休之後他終於有了時間,想起當年路過遊戲廳的畫面,他就跟外甥說:“有什麼打殭屍的遊戲也給我安上幾個。”
邢大爺已經叫不上來那些遊戲的名字了。“也挺好玩的,就……四五個人打殭屍,有點兒恐怖的意思。”邢大爺說,但是打了一段時間後,他慢慢也不感興趣了。
“那個年代過去了。”他說。
好在他遇到了《黑道聖徒2》。“這一打正好,我就不撒手了。”邢大爺很是滿意。在我寫完這篇文章,向外甥周林要一張邢大爺的Steam截圖時,我發現邢大爺的遊戲時長已經超過2600小時。
他是真喜歡。

邢大爺在Steam上由衷大讚《黑道聖徒2》
“你說,他到底在遊戲裏做什麼呢?”我問周林。
“我也不知道……他的話,最感興趣的可能也就幾件事兒。”周林說,“一個是開飛機在天上飛,一個是開大卡車堵高速公路,再有就是蹲在地鐵上。”
“蹲在地鐵上幹嘛?”
“在地鐵上……”他想了想,“看看城市吧。”
(本文由頭條遊戲頻道“編舟計劃”獨家支持,頭條首發。編舟計劃, 用文字將遊戲與時代編織相結。每週一篇,敬請期待。未經授權,內容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