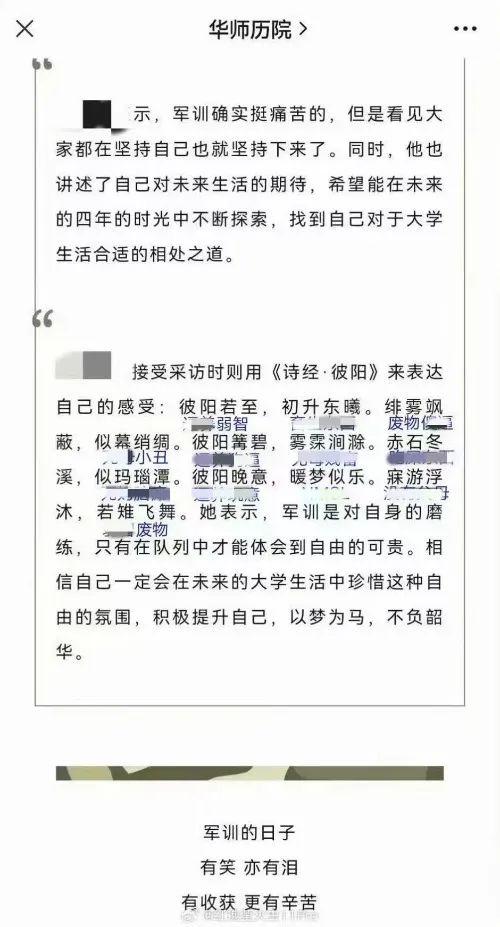鄭振鐸的《詩經》學研究
鄭振鐸(1898—1958),是現代著名的學者和作家,他在文學、藝術、歷史考古和版本目錄學等領域都作出了顯著的貢獻。在古史辨學派掀起的辯論熱潮中,鄭振鐸也投身參加了辯論,雖然他寫的文章不多,但是觀點大膽潑辣,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反響。
《詩經》在鄭振鐸的學術領域中是值得重視的一個部分。鄭振鐸對於幾種主要的《詩經》學派都曾經接觸過,他在《讀毛詩序》中回憶道:
我以前初讀《詩經》時,用的是朱熹的集傳。後來又讀《毛詩正義》,又看《〈詩經〉傳說彙纂》。最近纔看關於三家詩的著作。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諸家異說的紛紜,與傳疏的曲解巧說。當讀毛鄭的傳箋的《詩經》時,覺得他們的曲說附會,愈讀愈茫然,不知詩意之何在。再把朱熹的《詩集傳》翻出來看,解說雖異,而其曲說附會,讀之不懂,解之不通的地方也同傳箋差不多。
正因爲各家的解說都不能令他滿意,所以鄭振鐸纔在時代大潮的激盪下,開始着手進行研究,他選擇的突破口就是《毛詩序》。有學者認爲,“對《詩經》的研究貫穿在鄭振鐸一生的文學研究中,從1927年的《讀毛詩序》到1953年的《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詩歌傳統》,他的研究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即對《詩經》地位的肯定,對其進行分類以及獨特的研究方法”。這個說法大致不錯,不過他的《毛詩序》並非發表在1927年,而是發表於1923年《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號上,其後被收入《古史辨》第三冊中。在鄭振鐸的後期,也發表過一些有關《詩經》的言論,不過大多是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去研究,與他早期的觀點截然不同。
《讀毛詩序》是鄭振鐸在《詩經》領域最主要的代表作品,也是他收錄在《古史辨》叢書中唯一的一篇《詩經》方面的文章,這篇文章在當時影響很大,引發了學界關於《毛詩序》的爭論,錢玄同曾經表示:“得讀鄭振鐸先生底《讀毛詩序》,極佩。”(《論詩說及羣經辨僞說》)
在《讀毛詩序》一文中,鄭振鐸對於過去的《詩》學發展歷史有一個簡明的勾勒,從他對於《詩》學史的勾勒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大致的《詩》學觀。
漢興,說詩者即有齊魯韓三家。其後又有毛氏之學。北海相鄭玄爲毛氏作箋,毛詩遂專行於世。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後亦亡逸,僅有《外傳》傳於世。然《毛傳》雖專行,而王肅說《毛詩》又與鄭玄不同。其後,孫毓作《毛詩異同評》,評毛鄭王之異同,多非鄭黨王之論。陳統又作《難孫氏毛詩評》,以駁孫氏之說。到了唐代,韓愈對於《毛詩序》又生疑義。及宋而《毛詩》遂被許多人攻擊得體無完膚。歐陽修作《毛詩本義》,蘇轍作《詩解集傳》,程大昌作《詩論》,王柏作《詩疑》,毛詩才漸漸的失了權威。雖有周孚、呂祖謙諸人的竭力擁護,而總敵不過攻擊者的聲勢。元明以來,朱熹的勢力極大,《詩集傳》用爲取士的標準。一切說詩的人便都棄了《毛傳》,服從朱熹。到了清代,反動又起。閻若璩作《毛朱詩說》,毛奇齡作《白鷺洲主客談詩》,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陳奐作《毛詩集疏》,多非難朱熹之說,要把《詩經》從朱熹的《集傳》底下回復到毛鄭的傳箋之舊。段玉裁寫定《毛詩故訓傳》,孫燾作《毛詩說》,且進一步而排斥鄭玄之說,要把《詩經》從鄭玄的《毛詩箋》底下回復到毛公的《毛詩故訓傳》之舊。魏源作《詩古微》,陳喬樅作《三家詩遺說考》,龔澄作《詩本誼》,皮錫瑞作《詩經通論》,王先謙作《詩三家義集疏》,又更進一步而不滿於毛詩,要把《詩經》從毛公的《故訓傳》底下回復到齊魯韓三家詩之舊。此外又有姚際恆作《詩經通論》,崔述作《讀風偶識》,方玉潤作《詩經原始》,脫去三家及毛公鄭玄之舊說,頗表同情於朱熹,一以己意說詩。
從這段提綱挈領式的勾勒中,可以看出鄭振鐸對於《詩經》學史的認識相當清楚而且成熟,對於歷代《詩》學的評點都能夠從事實出發,力求客觀公允。事實上,現代《詩經》學史的認識也基本如此,鄭振鐸對《詩》學史的描述是比較準確的。正如我們分析其他古史辨學者的《詩經》學所看到的,他們在對傳統經學的批判的時候,自然而然地對於《詩經》學史上具有疑古思想的學者給予了過分熱情的評價。但是這種情況在鄭振鐸的身上並沒有發生,從他的描述來看,筆觸相當有分寸。
鄭振鐸雖然對於姚際恆等人深表佩服,但是他也看到了他們的缺陷:“雖然姚際恆、崔述、方玉潤的幾部書能夠自抒見解,不爲傳襲的傳疏學說所範圍,然而究竟還有所蔽。《詩經》的本來面目,在他們那裏也不能找得到。”
如同其餘的古史辨學者一樣,鄭振鐸研究《詩經》的前提是把《詩經》當作文學書籍來看,他認爲:“《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總集。我們要研究漢代以前的詩歌,非研究《詩經》不可。雖然在《詩經》以外,逸詩還有不少,然而有的是後人僞作的,如白帝子皇娥之歌;有的是斷章零句,並非完全的,如《論語》、《左傳》所引的詩句,其他完整而有意義的詩篇,至少不過二三十首。而在詩經裏,我們卻有三百零五首的完整的古代詩歌可以找到。在這三百零五首裏,有的是頌神歌,有的是民謠,有的是很好的抒情詩,差不多首首都是有研究的價值的。”
雖然《詩經》是文學作品,但他的價值顯然超越了文學本身,鄭振鐸對於《詩經》研究價值格外重視,他認爲:“凡是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古代的社會,乃至古代的思想,對於《詩經》都應視它爲一部很好的資料,而與研究中國詩歌史的人尤爲重要。所以我們可以說,我們要想研究中國漢以前的古代的詩歌,除了《詩經》以外,不能更找到別的更好更完備的了。”
對於《毛詩序》的批判是鄭振鐸《詩》學主要內容之一,他認爲:“《詩經》也同別的中國的重要書籍一樣,久已爲重重疊疊的註疏的瓦礫把它的真相掩蓋住了。……我們要研究《詩經》,便非先把這一切壓蓋在《詩經》上面的重重疊疊的註疏的瓦礫爬掃開來而另起爐竈不可。這種傳襲的詩經註疏如不爬掃乾淨,詩經的真相便永不能顯露。”這種觀點與顧頡剛的“蔓草之說”有異曲同工之妙。鄭振鐸認爲:“在這種重重疊疊,壓蓋在詩經上面的註疏的瓦礫裏,《毛詩序》算是一堆最沉重,最難掃除,而又必須最先掃除的瓦礫。”他反覆強調:“我們現在動手爬除壓蓋在《詩經》上面的註疏瓦礫時,應該最先下手的便是《毛詩序》。”他認爲:“《詩序》的釋詩是沒有一首可通的。他的美刺又是自相矛盾的。但他的影響卻極大。所以我們爲了要把《詩經》從層層疊疊的註疏的瓦礫堆裏取出來,作一番新的研究,第一必要的,便是去推倒《毛詩序》。”
鄭振鐸對於《詩序》的批判相當激烈,如同宋代王柏刪《詩》一樣,他認爲索性將《詩序》從《詩經》中刪掉最好,他提出“《詩序》之亂《詩》,其禍且甚於僞書。我希望在最近的時候,能夠也有人出來做這種工作,把《詩序》詳細的攻駁一下,把他從《詩經》裏永遠逐出”,他表示自己願意做“這種掃除運動裏小小清道夫的先鋒”。
對於《毛詩序》的弊病,鄭振鐸認爲“《毛詩序》最大的壞處,就在於他的附會詩意,穿鑿不通”。鄭振鐸認爲毛詩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牽強附會,“與詩意相違背的”。由於毛詩的解釋,“於是一部很好的蒐集古代詩歌很完備的《詩經》,被他一解釋便變成一部毫無意義而艱深若盤誥的懸戒之書了”。
爲了使自己的觀點有說服力,鄭振鐸在文中大量舉例,他所採用的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毛詩序》的矛盾、牽強之處進行了“剝洋蔥”式的分析。具體說來就是“假使我們退一百步而承認《詩序》所說的美刺之義是不錯的,我們竟用了他的美刺之義去讀《詩》”。但是按照《詩序》所宣揚的“美刺”理論去分析,結果卻發現“《詩序》之所美刺,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譬如有兩篇同樣意思,甚至於詞句也很相似的詩,在《周南》裏是美,在《鄭風》裏卻會變成是刺。或是有兩篇同在《衛風》或《小雅》裏的同樣的詩,歸之武公或宣王則爲美,歸之幽王、厲王則爲刺。而我們讀這些詩的本文時卻不見它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鄭振鐸舉了許多例子,來證明自己的觀點。我們試舉一例來看他的分析的角度與方法。《關雎》、《陳風•月出》、《陳風•澤陂》,我們今天都認爲是情詩,鄭振鐸認爲“先讀這三首詩的本文,我們立刻便知道《關雎》是寫男子思慕女子,至於‘寤寐求之’、‘輾轉反側’的;《月出》是寫男子在月下徘徊,見明月之光而思念所愛之人,以至於‘舒窈糾兮,勞心悄兮’的;《澤陂》所寫的更是悲慘,他思念所愛的人至於‘寤寐無爲,涕泗滂沱’了”。
但是這幾首動人的情詩在《毛詩序》眼中,都被賦予了不同的深意。《關雎》,《詩序》認爲:“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月出》,《詩序》的解釋是:“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也。”《陳風•澤陂》,在《詩序》看來是“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對於這種荒唐的解釋,鄭振鐸感到不可思議,他發出質問:“爲什麼同樣的三首情詩,意思也完全相同的,而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卻相差岐得如此之遠?……爲什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二句,在《周南•關雎》之詩裏便有這許多好的寓意,同樣的‘寤寐無爲,輾轉伏枕’二句,在《陳風•澤陂》之詩裏,便變成什麼‘刺時’,什麼‘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等等的壞意思呢?”
鄭振鐸舉的另一個例子是《召南•草蟲》、《王風•采葛》、《鄭風•風雨》、《秦風•晨風》、《小雅•菁菁者莪》、《小雅•裳裳者華》、《小雅•都人士》、《小雅•隰桑》八首,他認爲,這些詩“意思也差不多都是很相同的”,但是在《毛詩序》解釋中,它們都或美或刺,總是與政治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鄭振鐸感嘆:“這種美刺真是矛盾到極點了。……《詩序》的精神在美刺,而不料他的美刺卻是如此的無標準,如此的互相矛盾,如此的不顧詩文,隨意亂說。他的立足點已根本動搖了。”
鄭振鐸所採用的這種比較的方式,雖然並不是自他開始,但是他比較集中地對於《詩經》中的相似或者相同的詩句在不同的詩歌中美刺不同的現象進行了比較,對於《詩經》研究的深化是有比較大的促進作用。事實上,這也涉及到了《詩經》中“成語”的問題,在後來的《詩》學研究中,對於“成語”的分析日益普遍而深入,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從這方面來說,鄭振鐸對於《詩經》研究新角度的確立是起了促進作用的。
鄭振鐸《詩》學中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有一點,就是他對於《詩經》中詩的本旨抱着樂觀的態度,在這點上他是不同於顧頡剛等學者的。我們都知道,顧頡剛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他認爲科學的最終鑰匙鎖在上帝的小盒子裏,無論多麼努力,都是無法知道的,體現在《詩》學上,就是他反覆強調的詩的本事和作者,是無法去知道了。
但是,鄭振鐸對此抱着樂觀的態度。他在《讀毛詩序》中反駁了不可知論的觀點。他說:
我知道一定有人要出來反駁我。他們一定以爲詩意本來是深邃不易知的;《詩序》由來已久,其所說必有所據。安知《草蟲》與《隰桑》之本義不是如《詩序》所說的一樣呢?豈能以生於千載下的人的臆想來決斷千載上的事情?
鄭振鐸對於這個問題從兩方面進行了分析。首先,他根據文學史上的常理推斷,“古人作詩,詞旨俱極明白,決無故爲艱深之理”。他認爲,在“唐以前的詩便可知道”,因爲“《詩經》裏的詩,文辭俱極樸質,更不會包括什麼啞迷在裏面。……詩文固極明瞭,固不艱深也”。後世的《詩經》之所以難以索解,都是因爲“《詩序》之曲說附會有以致之”。
其次,對於“詩序由來已久,其說必有據的話”的觀點,鄭振鐸則對“《詩序》必古”的觀點進行了質疑,這其實就牽涉到了《詩序》作者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鄭振鐸支持衛宏說,但他並沒有把話說死,他認爲“即使說《詩序》不是衛宏作,而其作者也決不會在毛公衛宏之前”。事實上,關於這一點,歷史上已經有許多人進行了論爭,鄭振鐸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提出新的證據,他只是將前人的相關材料進行了歸納,爲己所用。最終的結論是:“《詩序》是後漢的產物,是非古的。漢人傳經,其說本靠不住:一方面保殘守缺,死守師說,而不肯看經文;一方面又希望立於學官,堅學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託,多方引證,以明自己的淵源有自。”他借用明代豐坊僞《詩》學來比照《詩序》,指出“《毛詩序》是沒有根據的,是後漢的人雜採經傳,以附會詩文的;與明豐坊之僞作子貢詩傳,以己意釋詩是一樣的”。
在這點上,鄭振鐸也比顧頡剛等古史辨學者顯出了更加靈活的態度,顯然,他意識到了《詩序》中諸多不一致之處,有可能是經過多人之手,這一點一直到現在都被大多數學者所公認。
不過,對於鄭振鐸的早期《詩經》學研究,有學者評價並不高。例如洪湛侯在評價《讀毛詩序》的時候認爲:“本文見解與顧文一致,其中有一部分舉例,還是顧先生提供的。原文雖長達萬言,卻看不到有什麼新的見解與發現,文筆亦不甚酣暢警策,與顧文相較,似嫌稍遜一籌。”
我們認爲對於鄭振鐸的《讀毛詩序》的學術價值要分兩部分來看,首先,確實存在上述所列舉的毛病,這是毋庸諱言的。“部分舉例”是顧頡剛提供,是指鄭振鐸在文中所用的幾個表,鄭振鐸對此是標明的:“本文裏第四節所引的幾首詩的三個比較表,都是我的朋友顧頡剛先生制的,但允許我先在此處引用它們,這是我所最爲感謝的。”顧頡剛的文章發表於1920年,鄭振鐸此文寫於1923年,兩人又交好,鄭振鐸受顧頡剛的影響並不奇怪,而且在文章中,確實存在着許多顧頡剛觀點的痕跡,這並不奇怪。而且古史辨學者作爲一個“學派”,自然有着近似的“學術觀點”。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鄭振鐸的論文就是對於顧頡剛文章的簡單重複,其中同樣有鄭振鐸自己的思考,正如我們在具體分析中所強調的,鄭振鐸的《詩經》學有自己的特色,不僅在具體《詩》學觀點上與顧頡剛有所區別,而且兩個人的風格並不一樣,相對於顧頡剛,鄭振鐸更理智一些,在具體觀點的把握與評點上也更注意分寸。
(作者單位: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博士後流動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