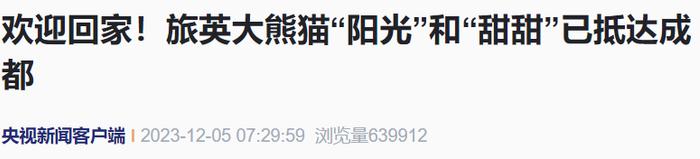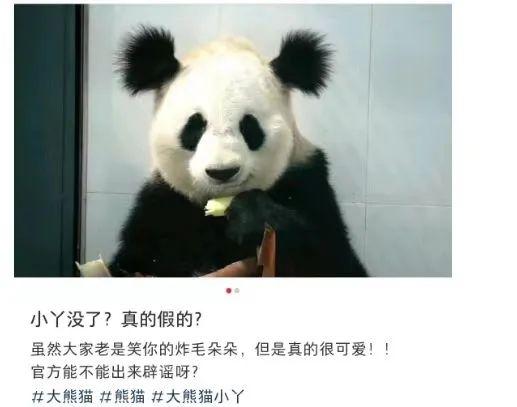《大熊貓的春天》:關於胖達你知道多少?
2016年,國寶大熊貓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將“瀕危物種”降爲“易危物種”。從一百多年前因爲法國傳教士將熊貓介紹給西方國家,得到世界的矚目的同時,也給這種僅生活在中國的川、陝、甘地區的深山密林的動物帶來諸多困擾,而後更是因爲獵殺和環境破壞,導致在20世紀70年代的統計中,全球大熊貓數量僅不到兩千只。
最近,全面紀實大熊貓科研保護工作的非虛構作品《大熊貓的春天》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三位作者張志忠、張和民、王永躍都是早年到四川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工作,是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的一線工作人員。書中,作爲親歷者的他們講述了四十年間他們的團隊爲熊貓的繁育做的工作。
從瀕危到易危,大熊貓經歷了什麼?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把物種劃分爲七個等級,由高到低分別爲滅絕、野外滅絕、極危、瀕危、易危、近危和無危。其中極危、瀕危和易危物種又被統稱爲受威脅物種。雖然大熊貓依然面臨着滅絕的威脅,但中國大熊保護研究中心的科研工作初顯成效,大熊貓種羣數量在穩定增長。
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在有大熊貓分佈的四川、陝西、甘肅建立了首批大熊貓自然保護區,正式開啓大熊貓棲息地保護工作。爲了拯救這一瀕危物種,1980年前後,中國政府與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合作,成立了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後,致力於大熊貓野生種羣動態研究,承擔大熊貓飼養、繁殖、疾病防控和野化放歸,大熊貓國際合作交流,以及大熊貓文化和公衆教育發展四項工作。以期通過研究野生大熊貓種羣生態行爲,破譯遺傳密碼,以人工圈養種羣補充壯大野生種羣的方式,實現拯救大熊貓的願景。
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成立的三十多年來,主要攻克了大熊貓繁殖領域“發情難、配種受孕難、育幼成活難”三個難關,圈養大熊貓種羣基因多樣性不斷上升,數量穩定增長,截至目前,達到了二百八十八隻,已基本形成了一個健康的、有活力的、可持續發展的種羣。同時,大熊貓保護中心在大熊貓野化放歸、重返自然的道路上也取得了技術突破,已有十一隻大熊貓經野化培訓後成功走向了大自然並存活。
但是隨着研究的深入,新的問題又顯現——大熊貓基因日趨於近親,且人工圈養種羣種公獸的不足,也導致遺傳基因匱乏。對此,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提出了大熊貓野外引種試驗,於2016年春天啓動了大熊貓野外引種工作。兩年時間兩次試驗,通過將圈養大熊貓母獸放歸至野外與野生大熊貓自然交配,引進野生大熊貓遺傳基因的試驗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18年7月,一對帶着野生大熊貓遺傳基因的大熊貓寶寶出生並存活。
2019年,這項試驗繼續執行,9月16日,參與野外引種項目的大熊貓喬喬在天台山的森林中產下來只熊貓幼崽,它們是圈養大熊貓野外引種後,全球首對在野外出生的大熊貓幼仔,爲野生種羣和圈養種羣血緣交換做出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貢獻。

喬喬

帶有野生基因的喬喬幼崽
與此同時,根據熊貓中心跟蹤人員的持續監測,大熊貓淘淘、華妍、張夢等通過培訓後放歸自然的大熊貓在四川栗子坪自由生活。而2018年冬放歸至都江堰龍溪虹口一帶的琴心和小核桃也順利存活……
可愛?狡猾?機靈?兇猛?哪個是真正的國寶
科幻小說作家尼爾·蓋曼曾描述,把熊貓抱在懷裏的那種感覺,是無法形容的快樂。他還說:“我相信如果全世界的人,每個禮拜去看一次熊貓,那麼世界和平在一個星期就實現了。”
小眼睛、圓滾滾、身上只有兩種顏色,永遠不能拍彩色照片的可愛溫順的模樣是熊貓的本性嗎?其實不然。大熊貓的本性和棕熊、狗熊這些動物沒多大區別,而且它們也是雜食動物,會喫肉,所以它們也會有雜食動物的暴躁和兇狠,在某些時候戰鬥力很強,是出了名的“打手”。並且早在古代,它們就有了非常霸氣的名字:食鐵獸。

熊貓也是性格複雜,內心豐富的物種,《大熊貓的春天》中就記錄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野外勘測的獸醫湯純香就講述道:大熊貓和很多孩子一樣,都喜歡喫甜的東西。最初的時候,湯純香把當知青時學到的本事拿出來:“我是打算給它們喫中藥的。但是隻要聞到中藥的氣味,熊貓就使性子,拿屁股對着你,一副我就是不喫的樣子。最後,想到了一個辦法,將中藥做成糖丸,餵給它們喫。它們還就乖乖地喫下去了。”

大熊貓改變了臥龍
最早的大熊貓保護研究工作者之一、八旬老人田致祥也在書中介紹了臥龍自然保護區的工作。
臥龍自然保護區成立之初劃地僅爲兩萬公頃,田致祥的職責就是守護這兩萬公頃的棲息地及大熊貓。但是,隨着紅旗森工局進駐,保護區域外的森林被大量砍伐。大熊貓的棲息地受到嚴重破壞。1973年,田致祥執筆寫了一封信給黨中央,報告了森林砍伐對大熊貓生存造成的嚴重威脅,記者們寫的內參也不斷呈報給中央。1975年,國務院將臥龍的大熊貓保護區從兩萬公頃擴大到二十萬公頃,紅旗森工局撤出,臥龍成爲首個國家級的,面積最大的大熊貓自然保護區。
臥龍地方雖好,但生活條件艱苦,很難留得住人。加上大熊貓繁育工作一度低迷,外國專家們紛紛撤退,20世紀80年代分配來的一百多名大學生走得只剩下六個。1989年,派往美國學習的張和民學成回國後,團結王鵬彥、湯純香、周小平、黃炎、張貴權等,擔起了林業部下達的大熊貓繁育攻關計劃。他們背水一戰,終於在2000年後攻克了人工圈養熊貓繁殖育幼的“三大難關”,實現了大熊貓人工圈養種羣的迅速壯大。
大熊貓改變了臥龍,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尤其強烈。由於核桃坪受災嚴重,次生災害頻發,圈養大熊貓不得不轉移。當地老百姓眼含熱淚,依依不捨地送走大熊貓。他們擔心熊貓都遷走了,國家不再管他們。張和民安慰鄉親們:“大熊貓,一定會回來,國家不僅要管我們,而且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對口援建臥龍,幫助臥龍災後重建!”幾年後,由香港援建的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在神樹坪建成,大熊貓們又回來了。
“據我所知,大熊貓改變的還不僅僅是臥龍。20世紀80年代初,原林業部曾調集川、陝、甘三省大熊貓棲息地保護區各山頭的技術骨幹到五一棚學習,而今他們都在各自的山頭推進大熊貓保護研究事業,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田致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