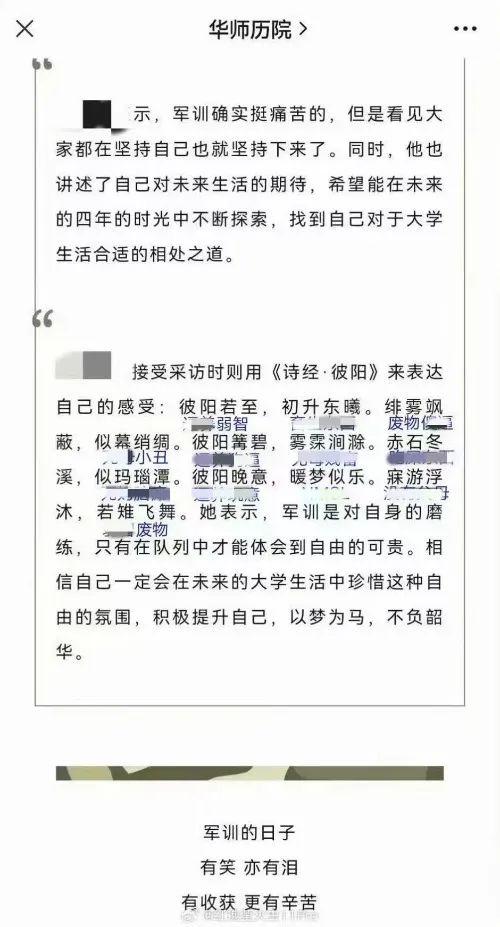楊聯陞:書評經驗談
摘要:今天要講的第一篇是孫念禮譯註《漢書·食貨志》書後或讀記,英文叫review article,著者 Nancy Lee Swann(漢名孫念禮是胡先生起的,見於她介紹班昭《女誡》書的扉頁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年出版,我的評介初見於《哈佛亞洲學報》(HJAS),後收入我的《中國製度史論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當時“教 育部長”張其昀曉峯先生召開大會,贈我文化獎章,獎狀頌詞說有人以我的書評比伯希和,實是稱許過實,萬不敢當。
1984年12月17 日,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開幕前一天, 我被邀作胡適之先生生日紀念講演,題是“書評經驗談”,地是美國文化研究所大講堂。原定吳大猷院長主持,因正有會議,改請總幹事韓忠謨先生主席。準時開講。
聽衆之中,師友不少,不及一一下臺致謝,只講後得與胡頌平先生寒暄數語,見頌平先生紅光滿面,爲之一慰。這次講演,因有數年不講課,不免生疏,只有綱要一頁,講時斟酌增減。又因對大講堂擴音設備不熟悉,未能善爲利用。可能座中有人聽不清楚,聯陞深爲抱歉。
今爲稍稍補救,試用綱目體,把要講的話,同補充未講的話,草爲一篇,呈請諸位指教。
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今天是胡適之先生的陽曆生日,大家同來紀念,很有意義。
(胡先生不喜歡用誕辰,他以爲《詩經》“誕彌厥月”之誕,未必是誕生之義。自然,以誕爲生,已是約定俗成了。)
今年紀念胡先生,添了一種重要的資料,就是胡頌平先生以多年的精力完成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共十數冊。此書誠如余英時院士在序中所說,是中國年譜史上最偉大的一種工 程。能早日問世,要感謝聯經的王惕吾先生。(多謝賜贈 !)
(《年譜長編初稿》油印本,我曾得一部,是前院長王雪艇先生特許。這部已轉贈哈佛漢和圖書館。當時每收到若干冊,就盡力就所知補充資料,多蒙頌平先生採納。今本第五冊、第七冊較多。)
除了餘教授對頌平先生的崇高評價之外,我想加重的是:此書下筆極爲慎重而令讀者有親切之感,往往如見其人。頌平先生有些年的日記,可能很像適之先生的起居注。
英時教授的序,實在是一篇可貴的長文。題爲“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英時教授與適之先生雖相知而從未會面,卻以他在思想史上的素養,寫成洋洋大文。文思細密,文筆流暢,全文充實而有光輝,可爲模楷。適之先生天上有靈,也必然欣賞。
《書評經驗談》題目是仿嚴耕望院士的《治史經驗談》。他此書深受學林推重,真是現身說法,爲初學之津樑。論學力他比我堅實甚多。雜家遇專家,小巫見大巫,豈敢相比。只我是所謂華裔漢學家(指西洋式),混了幾十年,評論別人賣的中國膏藥,或有可供參考之處。
許多人認爲書評不重要。我則以爲一門學問之進展,常有賴於公平的評介。很盼望像西洋、日本,養成良好的風氣。
(只以史學言之,《美國曆史評論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比我們早一百幾十年。1979年見到《史學評論》第一期,是幾位少壯學人創辦的,內容美富,頗覺欣慰。希望大家繼續努力,造成風氣。)
今天要舉的我所作的西文書評之例,多出在陶希聖先生主持的食貨社爲我在去年印布的《漢學論評集》。內有五篇西文論文,四十多篇英文書評。
(陶希聖先生在清華大學開的中國社會史課,引導我入了中國社會經濟史的門。陶先生在給《論評集》賜序時也提到。他也是我終身銘感的恩師。1935年《食貨》有我一篇《從四民月令所見到的漢代家族的生產》,是我在陶先生班中的寫作。提到農民身份,妄用奴隸社會一詞。後來日本有人指摘。實則我在次年《清華學報》《東漢的豪族》已引“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試證其時奴婢[不自由人]不如徒附[半自由人,包括客與略後之部曲] 之多,可能相差十倍,已經不再用奴隸社會這一類的模糊概念。奴與客的比例要實事求是,不應用框框亂套。)
今天要講的第一篇是孫念禮譯註《漢書·食貨志》書後或讀記,英文叫review article,著者 Nancy Lee Swann(漢名孫念禮是胡先生起的,見於她介紹班昭《女誡》書的扉頁 ),Food and Money in Ancient China,1950 年出版,我的評介初見於《哈佛亞洲學報》(HJAS),後收入我的《中國製度史論集》(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孫念禮博士對《漢書·食貨志》,有多年的功力,有許多地方,頗能深入,值得參考。當時她在普林斯頓,任 Gest Library 主任。以胡適之先生的介紹,我曾爲孫念禮博士看過兩次她的譯稿,提出若干意見。她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例如關於官俸半錢半穀的解釋,她曾教訓過我說:“年輕人 ! 半不必是整整一半啊 !”這話確有道理,不過若分別米(已舂)與粟(未舂),爲三與五之比,有幾條計算,可以算成半錢半穀,日本友人宇都宮清吉博士曾有異議,後來也承認了。
孫念禮博士還固執一點,即是“賦”在《漢書·食貨志》不論何處,都指軍賦。我以爲要分別而論。她不肯接受,只好在讀記中發揮了。
這篇讀記,我自覺尚爲有用的,是關於井田的討論。當時彙集李劍農(論貢助徹)、郭沫若(特別是《詩經》“中田有廬”之廬應爲蘆,即蘆菔,高本漢即譯爲radishes)、徐中舒三家之說。徐說包括東方(齊)多用四進位,西方(周)多用十進位,東西對立。可以解釋《周禮》的田制(十進)與孟子所說的八家同井(二四爲八)。而且假定周征服了商之後,國(包括近郊)與野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所居之地,兩者稅役不同。征服者服兵役(國中什 一,使自賦,即軍賦),被征服者服力役納稅。春秋時初稅畝,用田賦,及作丘賦等,均可依此解釋。我至今以爲徐先生之 說是通論,國與野之別,從傅斯年先生強調《論語·先進篇》以來,學人已瞭然於野人(被征服的商人爲多)君子(國人)之別, 周禮田制,也有人細考,似不出徐說之系統。
當時胡先生看了我這一段,不以爲然,說是爭論井田,總是“後息者勝”。我們尊重胡先生提倡的科學精神,要“拿證據來”。今日有若干條甲骨文、金文可證,有奏簡可證。學人要自強不息 ! 井田的討論,還可以繼續。不過不可忽略前人的成果。
以下討論我評德效騫譯註《王莽傳》關於“新”之國號爲地名還是美號引起的爭論。德氏爲此給 HJAS 編輯部寫信,因爲我以爲肇命於新都,王莽曾封新都侯,地名之說雖有據,但不可堅持此說,而否定胡適之先生以新爲 New 之說。兩說似宜並存。德效騫的異議同我的答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不必是不故)都收入《漢學論評集》。
讀《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有1956年5月16日適之先生給我的長信,由讖語“代漢者當塗高”(即魏)發揮先生之說“魏晉都不是簡單的地名,都是應讖的美號”。這個大有啓發性的爭論,我未能引入答辯,大約是當時我希望胡先生爲新是美號兼地名另撰一文之故。讖語大有宣傳意味,即拉斯威爾所謂符號之運用(Manipulation of Symbols)。
寫書評最重要的,是要先知道這一門學問的現狀、行情,這自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我的主要功力,用在四十年代。當時漢學中心在西方仍在巴黎,沙畹、馬伯樂(先後任法蘭西學院中文教授,故去之後,講座由戴密微教授繼任。伯希和在同學院任中亞語文講座)、伯希和三大賢戰後只剩下伯希和一位,主編《通報》, 常寫書評,對被評者往往失於刻薄, 不留餘地,自稱漢學界之警犬。我有幸在哈佛聽過他演講(中亞基督教史一題),參加過賈德納先生請他的宴會。同席有胡適之先生,但伯希和並未表示多少敬意。胡先生大約因爲他知道多種語文,目錄學很可觀,中文頗好,人特別聰明,就讓他幾分。我是後學,難免有幾分不快。
(1957 年,我代表哈佛燕京學社來臺灣組織中國學會。當時“教 育部長”張其昀曉峯先生召開大會,贈我文化獎章,獎狀頌詞說有人以我的書評比伯希和,實是稱許過實,萬不敢當。我的書評很少火氣,作風與伯希和大不相同,在《漢學論評集》的自序已有申明,讀者可以共鑑。)
與伯希和有關的書評只有一兩篇,一是法文譯註米芾《畫史》,著者旺迪埃-尼古拉夫人,在印布前曾來哈佛,把譯稿給我看,說這是她老師伯希和審正過的。我說那也不一定沒有問題。當時草草閱過,指出幾條錯誤。她可能沒全記住,正式出版,還有十 幾處有問題,然則伯希和也不能保險。夫人這本書同她另一本講 米芾的書,都顯出功力,有參考價值。
另一件事是《魏書·釋老志·釋部》的英文譯註,原有魏楷 先生的譯註,是博士論文,受梅光迪先生同伯希和指導,很可觀。後來有郝立庵在日本參加冢本善隆對這部分的講讀會,因魏楷先 生未分析“常樂我淨”爲四事,就另起爐竈,用英文改譯。我的書評是與陳觀勝博士同寫的,我只指出中文解釋的問題,有多少處魏楷錯了,多少處郝立庵錯了,多少處兩位都錯了。最末我加重說明,如果一本書或一個文件,已有前人認真處理,縱然過了50年,後人再作譯註,必須參考前人之作。這條規矩,頗爲同行前輩所賞。
與陳觀勝教授合寫書評是一樂,因爲他的佛教史非常高明,又會梵文、巴利文、藏文, 當時是同僚,合作方便。另一位合作的是柯立夫教授。他會的文字很多,蒙文蒙古史在今日已是唯一的泰斗。他主持HJAS有年,那時我幾乎是書評編輯(review editor),有意無意地與《通報》爭先。書評確有人注意,例如德國漢學家福·赫伯特(Herbert France)所著《漢學》一書,就列舉我不少書評。
荷蘭萊頓的戴文達(Duyvendak)與法國的戴密微同是歐洲漢學領袖,年輩相當,又同編《通報》,當時並稱二戴,兩位都是古道熱腸。戴文達常被哥倫比亞大學邀請,我旁聽過他講梁武帝與佛教。有一次美國東方學會在紐約開會,戴文達講但丁《神曲》中之地獄與羅懋登《西洋記》之地獄,主張後者可能受了前者影響,說其中有似是外來的金錢與椰瓢(鬼所持者)。我不知《西洋記》中所提是黃邊錢,當時在講後說中國原有金銀錢之金錢,不足爲外來影響之證,椰瓢待考。後來在《醒世姻緣傳》查到老黃邊,是一種好銅錢,又查到關於椰瓢的文獻,不止一處,寄與戴文達。蒙他在《通報》刊爲通訊,我的《漢學論評集》也收入作爲紀念。我常說戴文達先生是君子,此等處最見他老人家的氣量,能容忍後輩。
(後來他還幫我寫《西伯利亞之漢鏡》一文,見《通報》與《漢學散策》。)
1951 年在萊頓重晤(魏楷譯“有朋自遠方來”之來爲 return,此處合用)戴文達教授,在漢學研究院講皮黃戲,學生旦淨老旦小生各種嗓音,念“漢學研究院”五個字,頗受歡迎。戴教授介紹說 :“楊君弓上搭箭甚多,不止史學,語學論漢字分獨用(free) 合用(bound)爲前人所未發。”(實則 Bloomfield 已有相近之論。)另外快晤何四維(Hulseve)先生,他精於漢律,通各種語言,導我出遊竟日全說國語,命我隨時改正,實則無懈可擊。後來繼任院長,退休後住瑞士。
在英國倫敦見西門·華德(Walter Simon)、衛理(Waley),都是前輩。已退休的藝術史教授葉慈(Yetts)陪我到老人休養院 去看由劍橋退休的 Moule 教授。出乎意外,Moule 突然問我 :“你想我們西洋人真能讀懂中文嗎?”我說 :“焉有不能之理,只有深淺之別而已。”後來我寫衛理白居易傳評介,也挑了些錯誤(如“聖人”之用法),可能他還滿意。
在牛津做了德效騫的客(住宿舍 )。吳世昌在大學做 reader(近於教授,講課,教授可講可不講,但要預備考題)。劍橋教授夏倫 Haloun(在柏林與陳寅恪爲友)甚忙,抽暇快晤。
(次年遊此,夏倫教授逝世,遺命請柯立夫繼任,柯不去,又正式請我,我也不願意去。白樂日來信 :知君不欲以 Cambridge England易Cambridge Mass.。後來戴文達謝世,也有人問我是否願去萊頓,也謝了。)
在劍橋主要是做李約瑟的客(宿舍規矩不同,早餐時同桌有寒暄者,有隻自看報者)。看他所藏的書。談到赫連勃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並築之”,他大有興趣,立刻檢出《晉書》原文,要我口譯,他在卡片上打字。其勤真不可及。那時的助手是王鈴,有時在鄭德坤博士家會晤,鄭講考古與藝術,是哈佛前輩。後來李約瑟等的大著第一冊(近於通史)出版,我在HJAS有長評,指出若干錯誤。再會面時就有些冷落了。
衛理告訴我,他評此冊說其中有許多錯誤(many mistakes),李約瑟告訴衛理:“你必須再舉二十多條錯處纔可以說許多錯誤。”衛理說:“我又寄給他十幾條,也就罷休了。”
由此可見,書評用數量詞,特別要慎重。如 a few 是三五個, several 就多些,可說五七個,some,a number of 若干(前者較少)都有分別。定冠詞 the 的使用,更是重要。西洋人自己有時也不敢定,有人說如果可冠可不冠之時以不用爲宜,亦是一法。
李約瑟、王鈴合著第一冊討論沈括,提到《忘懷錄》,有遊山水必備之器物的單子。有一處需要泥船(mud boats),我覺得奇怪,檢書原來是泥靴(mud boots),可能王鈴發音欠準確,李約瑟沒聽清,致誤。不過,若依常情推測,亦可能猜出此類錯誤,只是他們做的是開荒的工作,一年不知要看要譯多少書,豈能毫無失誤 ! 讀者要心存恕道。我對於李約瑟的鉅著還是十分敬佩的!
結末講一個我幾乎搞錯的關於序數的事。曾有一位印度學者,英譯龍樹的《大智度論》,要我對照漢文審閱(他的大名是Romanan,譯註早已出版)。我看到一句“如無名指,亦長亦短”,他把無名指譯爲第二指(second finger),我覺得奇怪。沒敢說他錯了,先問他無名指所在,他指對了。我說何以是第二指,他說:“我們是從小指起數的。”大家也許說是倒數,但正倒何以爲定?
又查字典此字可說ring finger,可是第四指,也可是第三指,那是不算大拇指,實在不簡單。
有人喜歡問你在某一門學者中,是第幾名。我想最方便的回答是第二名,可以正數,可以倒數。反正最好的第一名同最壞的最末都讓給別人,無咎無譽,也許是處世之道吧。
講完,主席宣佈可以討論,有兩位先後發言,雖有內容,略嫌冗長。一位是胡鍾吾先生,說井田之制,有關國防。另一位未得大名,主旨似說文學史乃至文藝也應有書評,我自然同意。他提到《胡笳十八拍》。我想他必然知道這與《悲憤詩》(五言及騷體)都傳爲蔡琰文姬之作,不過專家認爲尚有問題。大陸在 1959 年出了一冊《胡笳十八拍討論集》,收了三十多篇文章。郭沫若有六篇,贊成《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所作。劉大傑、劉盼遂等都反對。雙方都舉了證據。我個人認爲中華書局此書,無妨影印,以免有人見了,改頭換面,取爲己有。
又,耶魯大學中文系教授傅漢思(Hans Frankel)對蔡琰《悲憤詩》有研究有譯註,曾來哈佛講讀,結束說,看來嫁與胡兒,未必非才女之福,聽衆爲之莞爾,傅夫人是書畫詞曲四者兼長鼎 鼎大名的才女張充和。漢思教授的幽默甚爲中肯。
附記,有人問 :國外寫書評有無稿費?答 : 學報沒有,給抽印本的也不多,但如是有名的大報副刊,特別是文學副刊,酬報可能甚豐,但也看評者的地位。學報邀人寫書評,往往限字數,先得評者應允才寄書來。若是長篇評論,可以投稿,學報認爲可取才收入。書評之前可就內容加一題目,引起編者讀者注意,實已近似論文。著作目錄書評可以列入。
寫書評可以長學問,交朋友,今日雖無科舉,新進亦頗願有大力者推薦,爲己而亦爲人,何樂而不爲哉!
《大陸雜誌》第79卷第3期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