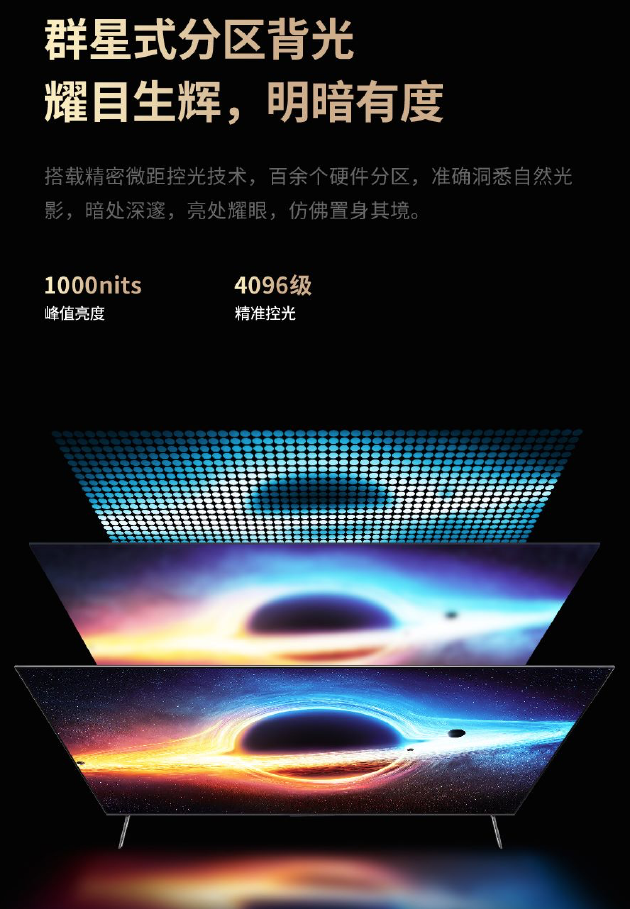被圍觀的“鍾美美”:更多人賦予其新的期待
原標題:被圍觀的“鍾美美”
一兩個月的時間裏,鍾美美的走紅,把鍾宇升推入到成年人的世界裏,他被無數人圍觀,被無數人評價,也被無數人賦予新的期待。他的好朋友小藝說:“我希望他以後能考到自己心儀的學校,幹自己喜歡乾的事情,無拘無束,特別自由。
從“普通人”變成“網紅”之後,鍾美美對如今的生活“喜歡又不喜歡”:喜歡是因爲被很多人關注,不喜歡也是因爲被很多人關注。
說到這些,鍾美美抬起右手放在耳邊,細着嗓子模仿給他打電話的人:“喂,你好,是小鐘同學嗎?”
採訪、代言、簽約、帶貨等詞彙反覆出現,大多數時候,鍾美美會回覆說“我考慮一下”,然後禮貌且委婉地拒絕。
打來的電話實在太多了,被關注的開心逐漸被煩取代。“從早上四五點打到晚上十二點,平均每兩小時接一個,多的時候每小時接兩個,能把手機打到沒電。”鍾美美說。
這是這個13歲初中生最近生活的常態,他因爲在網上發佈模仿老師的視頻走紅,精到的表演讓他擁有了第一批粉絲,隨後,被“約談”並將作品下架的傳言再次把他捲入輿論場,並擁有了更多的關注。
短短几天時間裏,鍾美美被圍觀、被討論,被推上陌生的軌道,疾馳向前,並在內外力的影響下,不停修正方向。

6月6日,鍾美美在學校操場。圖片來源:我們視頻
“圍觀者”
6月6日,電視臺的相機和自媒體的手機陸續擠進門,學校老師和領導、當地宣傳部和教育局的工作人員等,也出現在鍾美美家裏,不到百平的小房子,客廳被擠得滿滿當當。
“主角”鍾美美坐在臥室的書桌前,少年個頭不高,瘦瘦的,穿黑色T恤和運動鞋,和每個在大街上瘋跑的中學生別無二致。
“圍觀者”則分成兩部分,搶先進入臥室的在牀邊空地架起攝像機,其餘人則分成兩列站在門口,舉着相機或者手機,站着或者蹲着,等待鍾美美“登場”。

6月6日,媒體記者在鍾美美家採訪拍攝。新京報記者王雙興攝
幾乎每個到訪者都希望他能“現場模仿一段”。鍾美美很快同意了,比起在十多個鏡頭前乾坐着,模仿對他來說容易了不少。
他支起平板,盯着屏幕,手指在“鍵盤”上敲了敲,開始模仿東北售票員,“往前走一走啊,都不能插隊啊!”
鍾媽媽臨時被鍾美美叫了過來,扮演購票人。確定時間、選座、刷身份證、出票,一問一答中完成了購票流程。遞出“票”,鍾美美繼續招呼後面的人排隊,鍾媽媽打斷他,即興問了句:“不好意思啊,我想換張票,換個……臥鋪。”
鍾美美舉起手朝後指:“換票不在我這兒,你到那邊兒去,F窗口。”然後繼續敲鍵盤,嘴裏小聲嘟囔了一句:“換張票?早想啥了。”說完,繼續自顧自地演,“上哪兒啊?哈爾濱今天沒票。”
像是有意考察鍾美美的反應速度,人羣中又冒出一句:“上車補行不行啊。”
小鐘看了一眼對方,接過話:“這邊兒沒票,進不了站啊。”
不到兩分鐘,表演結束了,幹練的售票員變回羞澀的中學生,他把手擋在嘴邊笑:“完事兒了。”
同一天,他在另一個拍攝現場模仿了媽媽:臭着臉推門、掃地、拉窗簾,然後一把抓起牀上的被子:“都幾點了還擱那兒睡!不知道起來喫飯?”
圍觀者們忍俊不禁,又因爲攝像機正在拍攝,只能把笑憋回去。
人羣中有人咂着嘴點頭,有人感慨一句“確實是天賦”,一旁家人和學校領導也跟着笑。
類似的評價也曾無數次出現在他發佈的短視頻的評論中。六月伊始的這幾天,那些視頻曾引來百萬網友圍觀。
鍾美美最初的作品以模仿老師爲主,視頻裏,他模仿女性的聲音和造型,有時生氣,扔書、踢椅子:“我不用講了,有啥可講的啊。”有時抱着胳膊開班會,給學生髮獎盃:“魔方比賽一等獎,非常棒,但你學習要是有這麼大勁就好了。”有時候在公開課過後批評學生,“叫一個不會叫一個不會……後面的陳老師楊老師咯咯樂。”
有一次,鍾美美扮演班主任哭着進教室,“她”因爲佔體育老師的課被學生告了狀,一通訴苦後,問:“你們知道錯了嗎?知道了就行,那剛纔都有誰告我的狀了?”二十個學生站了起來,“班主任”話鋒一轉:“來,都給我出去,走廊站一排,一會我給你媽打電話啊。”彈幕上飄滿了“害怕”。
一組視頻陸續發出後,鍾美美“火了”。
視頻播放量不斷增加,粉絲數也在幾萬幾萬地漲。編劇史航評論:這孩子以一己之力,把我一腳踹回了少年時代。

鍾美美模仿老師視頻截圖。
普通人“鍾宇升”
“鍾美美”是鍾宇升給自己隨便起的網名。被鏡頭環繞着的鐘宇升比拍攝模仿視頻的鐘美美拘謹了不少。手臂搭在一起,攥住胳膊,用課堂上聽講時的姿勢,抬起眼睛打量這十多張陌生面孔。
問題不停地丟過來,鍾宇升兩隻手十指交叉,不停拱起手掌再握下去。他回答問題時的聲音不大、簡短,並常常冒出“我不知道啊”,有時說着說着便瞥向提問者:“這樣說可以嗎?”
聽說他喜歡地理,電視臺記者希望他在鏡頭前背一背地理知識,比如“和中國隔海相望的國家”。鍾宇升有點懵,磕磕巴巴說了幾個。等人羣從房間裏散去後,校領導有點遺憾地說了句:“你地理不是挺好的嗎,怎麼隔海相望的國家還弄不清了呢?”鍾宇升沒說話。
採訪間隙,到訪者們聚在客廳,鍾宇升留在臥室裏。喧躁中,他從桌上抻出一套試卷,開始做題。三四個鏡頭再次回到房間裏,對準試卷上的地理題目。

6月6日,接受採訪的間隙,鍾美美在手機上看短視頻。圖片來源:我們視頻
拍攝、採訪了一上午,午飯時間,攝像機關機,鍾宇升這才鬆弛了下來,託着下巴左看右看,打量飯桌上每一個人。一會睜大眼睛問“這是你第一次來東北嗎”,一會感嘆“你的手機這麼薄啊”。
鶴崗太陽猛烈,曬得人犯困。一羣大人閒聊起午休的話題,鍾宇升很快加入其中。
他說,小學時午休,大家都不想睡覺,跑去操場的柵欄旁,找小商販買零食。“他們都說要去買,然後就一起跑過去,結果他們停在後面了,就剩我自己跑去,老師就從樓上下來了……”鍾宇升邊笑邊說。那次,老師把他媽媽叫去了學校。
“我都說了,不讓帶錢來學校,他不但帶錢了,連錢包都帶來了!”男孩挺直背模仿老師,然後斜靠到椅背上,和“聽衆”們一起笑。
上一次,這座位於黑龍江北部的小城聚集這麼多媒體記者,還是因爲房價,“五萬塊買了套房”的故事傳遍社交網絡。
這座東北小城太小了,鍾宇升家所在的墾區尤甚。午飯時,鍾宇升在去餐廳洗手間的路上被一箇中年男人攔住,“你不是那個鍾美美嗎?!”
離開洗手間時,一個16歲男孩認出了他,等鍾美美離開,他打開手機,將鍾美美近期接受採訪的視頻,從頭到尾看完了。
成爲“網紅”後,鍾美美無論走到哪裏都會被發現。去超市購物,會被認出;去廣場散步,會被人拉着拍合影;就連走在路上,也總能碰到有人過來打招呼。
上網課的同學們紛紛發來微信,感慨他粉絲多、演得好,還有很多人跑來牽線搭橋,“這是我同學的同學,你通過一下他的好友請求”。
閒聊的時候,記者和鍾宇升開玩笑:“是個商機啊,出售小鐘微信號,十元一位。”
“十元一位,不保加!”鍾宇升咧着嘴壞笑。

6月6日,接受採訪的間隙,鍾美美在手機上看短視頻。圖片來源:我們視頻
成爲“鍾美美”
鍾美美的好朋友小藝被無數人問起“聽說鍾美美是你同學啊”,有人發來他一百多萬粉絲的截圖,還有人興致沖沖地索求聯繫方式。
小藝的媽媽在醫院工作,前陣子,她在休息時間總能聽到同事聊起鍾美美,或是打聽他家住哪裏。“我對這孩子太瞭解了,從小看着長大的。”小藝媽媽一副自豪語氣。同事們立刻圍過來,打聽鍾美美的年紀、性格、成績,以及關於“表演天賦”的點點滴滴。

鍾美美家中貼的兒時照片。新京報記者王雙興攝
於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片段不停地被同學講給同學、家長講給家長。同學們說他“會照顧人,幫大家買奶茶”“有想法,出去玩告訴我們下一步怎麼做”“很幽默,可以一直不停地講笑話”;家長們說他“有禮貌,見面會打打招呼”“懂事,幫家人照顧妹妹,每次出去玩都和家裏老人打招呼”“熱心,同學有矛盾他能從中化解開”……
小藝媽媽告訴鍾宇升姥姥,“突然之間身邊出了個明星,我都要成他的發言人了。”
最廣泛傳播的是有關鍾宇升的“表演天賦”。涵涵曾經和鍾宇升同桌,她記得,他從小學起就參加過表演類的興趣班,還曾在元旦晚會上演潘長江的小品,《甄嬛傳》熱播的時候,他在課間給同學們模仿甄嬛,笑聲一片。
小藝回憶,一次大家去野餐,鍾美美還曾模仿過《從前有座靈劍山》裏的情節,徒弟王路跟着師父王舞練劍,不停捱打,鍾宇升分飾兩角,“一個人就能演起來,還自己加了旁白,厲害。”
在鶴崗,城市的榮光隨着資源枯竭不復存在,很多年輕人從小便有了“去遠方”的概念,但對小朋友來說,所謂“遠方”常常是模糊的。小藝記得,讀小學的時候,他們曾經一起坐在學校操場上,聊未來的打算,有人說“我要去外地”,有人說“我要考重點大學”,小藝說“我想去上海”,所有答案裏,鍾宇升的最具體,他說,“我想考北京電影學院”。

6月6日,鍾美美在學校操場。圖片來源:我們視頻
那些年,鍾宇升的父母在哈爾濱工作,他和外公外婆生活在鶴崗,偶爾坐火車去哈爾濱探親。家人發現,很多時候他都在默默觀察,走過一遍的陌生街道,返程時可以準確地“預告”路標;回家後還常常推着妹妹的玩具小推車模仿列車員:“香菸瓜子礦泉水,把腳收一收收一收啊。”
家人和到訪的記者們開玩笑:“等你們走了,說不定他會模仿你們。”
平日裏,他喜歡四處打量,自言自語,時不時還把家裏的獎狀“改造”了,將獎項名稱改爲“表演獎”、“小品獎”等等。
大人們要忙於工作和家務,多數時候,鍾宇升在家中的模仿秀只有一個觀衆:不滿四歲的妹妹。
比起洋娃娃和小零食,哥哥的手舞足蹈對這位觀衆實在沒有什麼吸引力,她甚至搞不懂他在幹嘛。但有一次,鍾宇升心血來潮模仿媽媽搞衛生的樣子,一邊假裝揮掃把,一邊加重語氣抱怨:“造得皮兒片兒的……”妹妹在一旁,奶聲奶氣地說了句:“這不是媽媽嗎。”
直到今年4月底,鍾宇升在短視頻平臺上看到其他人模仿老師的視頻,覺得“好玩兒”,他也試了試。
“劇情”是自己設計的,道具一般只需要手機和窗臺,或者媽媽和姥姥的衣服;沒有劇本,沒有提詞器。
拍攝時他不喜歡有人圍觀,鑽到房間裏,把手機立在窗臺上,就開始表演。演完甚至不需要花什麼功夫進行剪輯,偶爾要用到轉場和配樂,就從軟件上隨便選一個。然後發佈到網上。
天南海北的觀衆,都在鍾美美的視頻裏看到自己老師的影子,有人開玩笑:“他一定是上課最認真聽講的那個。”
爭議“鍾美美”
五月底,粉絲們突然發現,鍾美美拍攝的模仿老師的短視頻在平臺上“消失了”,模仿網絡主播、鐵路人員、東北媽媽、景區售票員等角色的視頻則依然留在主頁。緊接着,鍾美美“被約談”的消息在網上傳播,他和他的家人、老師,當地的教育部門都被推入更大的輿論場。
進入輿論旋渦的三四天時間裏,鍾美美粉絲從十幾萬漲到了一百多萬。
事後,鍾美美本人解釋:“換個風格,不模仿老師了,看他們挺多看膩了。”“因爲有一些網友說我在醜化老師,我和我媽就聊了一下這個問題,自己確實意識到了可能給老師帶來一些不良的影響,最後和我媽達成一致,就把這個視頻隱藏了。”

6月6日,鍾美美在家中接受電視臺的採訪。新京報記者王雙興攝
鍾美美母親接受採訪時也曾表示:“評論裏有好的也有壞的,我覺得對孩子影響更大,就讓他隱藏了。”
6月3日,寶泉嶺農墾管理局教育局工作人員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說:“學校可能和孩子接觸了,我們分局的意思就是從正面去引導孩子,拍一些正能量的作品,多宣傳一些疫情期間的好人好事,加一些老師的正能量的東西。”
“走紅”之前,鍾美美曾將模仿老師的視頻向當地一家自媒體投稿,該自媒體負責人表示,在鍾美美將個人平臺上模仿老師的視頻下架的同一時間,“學校找過來讓把我們這邊的視頻刪了。”
但在6月6日,該教育局的一位負責人告訴新京報記者,“‘約談’是堅決不存在的,是大家的一種誤解。鼓勵孩子發揮特長是我們教育工作者要做的,所以說這件事出來以後,我們都是本着關心愛護的角度,把孩子特長保護好,讓他在發揮特長的同時,文化課也要抓好,並駕齊驅。”
他還說,教育局也要從鍾美美的作品中發現一些問題,“瞭解一下老師隊伍裏面是不是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真的存在,我們要從師德師風建設這一塊做好。”
“約談”風波之下,關於“該不該擁有諷刺的藝術”“如何保護孩子的創造力”等話題被網友不停討論,擁有二百餘萬粉絲的教育博主王悅微在微博裏提及此事,她說:我教過很多不聽話的男生,被他們頂撞過,質疑過,在課堂上跟我唱反調,跟我辯論,無法被我說服,我覺得這都是年輕人該有的樣子。我欣賞這樣生機勃勃的小孩,他們是眼睛裏有光芒的人。和他們成爲師生,更成爲朋友,看他們桀驁而自信地對這個世界發起挑戰,我覺得,這就是教育的意義。
短短几天時間裏,互聯網成爲學生展示才藝的平臺,又成爲社會輿論的放大鏡,如今風波漸漸平息,在對鍾美美的“圍觀”中,家長和老師們也開始重新思考互聯網時代的教育。
頭髮白了的校領導們開始意識到,這羣互聯網原住民,給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以往從沒下載過相關APP的書記最近看起了短視頻,學校主任和老師也在考慮網課結束後如何應對學生和網絡的關係。
好朋友小藝的媽媽說,小藝喜歡彈吉他,早在幾年前,他就開始嘗試着把自己的彈唱視頻發佈到網上。身邊一些朋友家的小孩也在做類似的事情,有的發自己練習毛筆字的視頻,有的拍視頻教別人做奧數題,還有的擅長跳舞,就拍成片段發在網上。
小藝媽媽覺得,互聯網和短視頻太耗費時間,漸漸地,便“用上一代人的要求去要求這一代的孩子”,讓小藝把精力放在學習上,中止了視頻拍攝。
最近,鍾美美突然走紅,小藝媽媽也開始思考這件事,“沒想到孩子們玩也能玩出名堂。”她意識到,這羣年輕人會去琢磨自己喜歡和擅長什麼,然後通過網絡展現出來,網友的認可對他們而言也是很大的鼓勵。
“會自責當初怎麼把孩子這種好的想法給抹殺了。” 小藝媽媽有點後悔,“不應該讓孩子千篇一律地去成長。”
“我希望他能幹自己喜歡乾的事情”
13歲的白紙上,可以天馬行空畫任何圖案,但被圍觀的日子裏,鍾宇升越來越緊密地和鍾美美捆在一起,並一同接受外界對“圖案”們的“修正”。
好朋友小藝不太能理解:“這不就純娛樂嘛,我覺得這種視頻平臺是要給人帶來快樂的,現在就有點像熱點輿論了。但是沒必要,就是玩兒。”
“就是玩兒。”這和鍾美美起初的想法一樣,但如今,面對外界的一次次爭論,他也開始重新思考它們。

6月6日,鍾美美在學校操場。圖片來源:我們視頻
鍾美美說,他漸漸意識到“醜化”的存在。“雖然我不是出於那個目的,但是後來確實看了一眼,可能是稍稍有一點太誇張了。”
“那你覺得哪個更好玩呢?列車員、志願者、老師……”有記者問。
“老師。”在老師和校領導的注視下,鍾美美小聲回答。
但他開始接納學校給出的“多拍正能量作品”的建議,他說:“挺好的。確實社會上如果每個人更加正能量,也是一個好事。”風波過後,鍾美美拍攝了模仿志願者的視頻。
當下的他,不僅要面對外界對這些視頻賦予的意義,還要面對隨之而來的名氣以及財富誘惑。
來電提示頻繁跳出到手機屏幕上,儘管有被關注的欣喜,但時間久了,鍾美美還是覺得困擾,他特意發了一段視頻聲明:“每天給我打電話,你知道對一個人有很大騷擾嗎?網課打,幹嘛都打……”
除了絡繹不絕的採訪邀約,談“合作”的電話也不停打進來。有的希望鍾美美能給自己的品牌做廣告,有的則希望他在自己的視頻裏“帶貨”,還有很多人開門見山,希望和他簽約。
一天,有電話打到媽媽手機上,掛斷後,媽媽當成玩笑轉述給鍾美美:“又有人想籤你,一年一百萬。”
鍾美美對這個數字沒太多概念,可能是上百部蘋果手機,或是幾千雙運動鞋。他和媽媽說:“一百萬挺多哈,要不……我去看看?”
擔心他被光環和金錢裹挾,媽媽把他罵了一頓。
鍾美美還是耐不住好奇,趁媽媽不在,偷偷翻了她的手機通訊錄,想給對方打回去,問問籤多長時間,都要做什麼。電話沒打通。
鍾媽媽把這些“合作”請求全都拒絕了,“我怕他榮譽和光環太多了,就浮躁了。錢的誘惑其實挺大的,但是對這麼大的孩子,我是不希望他把錢看得太重。”
這也是班主任田廣霄最擔心的,他反覆囑咐鍾宇升,“要正確面對流量高低,流量高是好事,流量低也不是壞事。你通過自己知識的豐富,內涵修養的提高,將來無論走不走上演藝這個行業,都能有自己的選擇。”
至於捲入巨大的流量網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小鐘倒沒像大人們那樣緊張。他覺得,就算有一天“不火了”,也不會有太大的失落,“流量不可能一直在大衆視野裏面,就像買了東西肯定喫完了,不可能只放着不喫。”
一兩個月的時間裏,鍾美美的走紅,把鍾宇升推入到成年人的世界裏,他被無數人圍觀,被無數人評價,也被無數人賦予新的期待。有人希望他拍更多正能量的短視頻,有人希望他簽約公司或是做廣告代言,有人希望他以學業爲重考上重點高中……
我把同樣的問題拋給他的同齡人、好朋友小藝,小藝說:“我希望他以後能考到自己心儀的學校,幹自己喜歡乾的事情,無拘無束,特別自由。”
(感謝本報記者王昆鵬對本文提供的幫助)
文 | 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 許研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