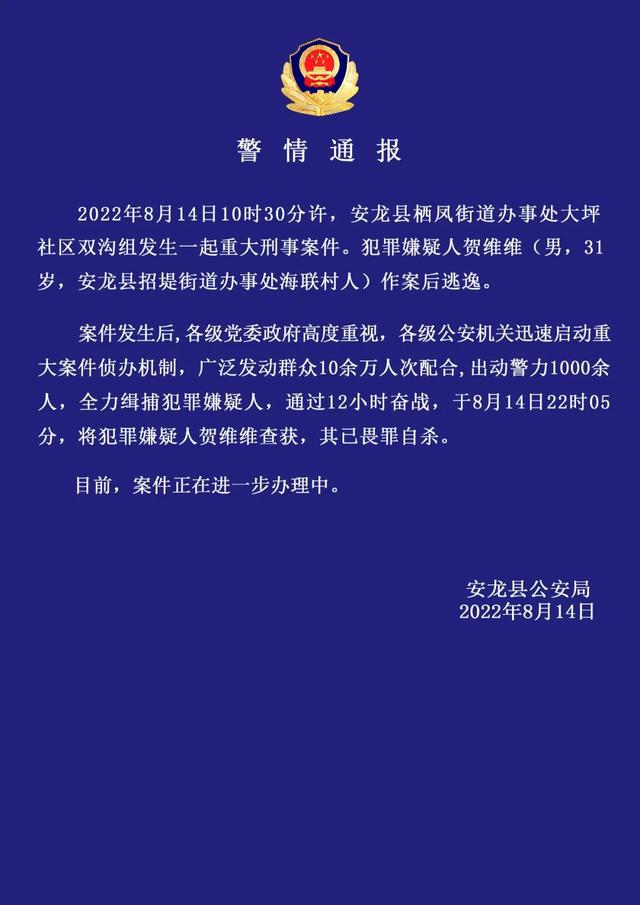兒子送養後被拐賣,一位母親的29年尋子路
(原標題:兒子送養後被拐賣,一位母親的29年尋子路)
眼前的青年,個子很高,相貌俊朗,頭髮微微上翹,像蓬起來的公雞頭。
朱彩娟不住地打量着,從他身上看到了丈夫的影子,是她與這個孩子血脈相連的證明。多年來無數不確定的想象,終於變成了眼前“真實的兒子”。
29年前,迫於經濟壓力,朱彩娟同意了丈夫將兒子送養的決定。孩子卻在被抱走後遭遇拐賣失蹤。
從此後,找到兒子,成爲朱彩娟一生的執念。
29年尋子路,她獨自一人,在愧疚、自責、悔恨中漫無目的地尋找,卻始終不肯放棄。直到她拿到了兒子被拐賣案的判決書,在浙江省樂清市檢察院當年公訴檢察官張培獻的幫助下,找到了兒子。
見面那天,朱彩娟很想抱抱兒子,最終卻只是拉住了兒子的手,將他的手指在自己手心裏合攏到一起。
朱彩娟沒有等來一聲“媽媽”,從始至終,兒子只在告別的時候跟她說了一句話,“常聯繫。”
“我一直都沒有拋棄他,我一直在找他。”
10月15日,朱彩娟(左三)爲張培獻(左二)送去錦旗表達感激。樂清市檢察院供圖
新生
1991年農曆正月十七。朱彩娟永遠忘不了這個日子,那天凌晨一點二十分,她在陣痛中生下了自己的第三個兒子。
孩子出生於半山腰一處廢棄的舊房子中,朱彩娟只知道那是杭州附近的一個村莊,說不清楚究竟是哪幾個字。
她沒上過學,文化水平是“讀過毛澤東語錄”。但這並不妨礙她對孩子寄予厚望,剛生下來的男嬰白白胖胖,朱彩娟給他取名“丁丁”,還特意找了一個漂亮的奶孃,“希望兒子長大後也會漂亮”。
新的生命給朱彩娟帶來了難以替代的喜悅,但並不能給深陷債務泥沼的家庭帶來任何起色。
那時,朱彩娟奔走於各個村莊間,給人當裁縫,每天只能賺1塊2毛錢。丈夫項金照則在附近的工地幹苦力。爲了還債,項金照計劃借錢去河南三門峽做生意。他覺得帶着丁丁不方便,幾次提出送人,朱彩娟“一萬個不同意”。
這個“一路苦過來”的女人,先後爲兩任丈夫生下了四個兒子,第一任丈夫因意外去世,第二任丈夫又債臺高築。她從未想過放棄任何一個孩子,“不管多苦多累,只要有一口吃,孩子就不會餓死。”
家裏充斥着爭吵聲,哭泣聲,朱彩娟的、孩子的。
真正讓朱彩娟讓步的,是項金照告訴她,老家仙居縣有一戶黃姓人家,條件很好,想收養孩子,他可以託朋友張良(化名)將丁丁送過去。
朱彩娟的孃家和這戶黃姓人家算是世交,丁丁可以在更好的家庭條件中成長,朱彩娟覺得比跟着她這個母親強。
送走孩子前,朱彩娟反覆追問項金照,“張良可靠嗎?”
“可靠。”
執念
29年前,1991年7月,母子分離。朱彩娟不敢去打擾,卻又忍不住惦念,只想再遠遠地看上一眼。
在家默默哭了幾天後,她找到張良,這才得知孩子並沒有被送到黃家。張良始終不肯告訴朱彩娟,丁丁在哪,每次都用“收養人不希望你去打擾”爲理由打發她。
案卷中的被拐男嬰。樂清市檢察院供圖
尋找丁丁,成了朱彩娟的執念。
此後多年,朱彩娟和項金照輾轉河南、上海等地打工,一邊賺錢還債,一邊拉扯孩子。朱彩娟雷打不動地擠出時間回老家找孩子。
她每年都去找張良,次次都被拒絕。她四處向人打聽,甚至會挨家挨戶敲門詢問,“發神經似的”,卻一無所獲。
聽說張良有個姐姐不能生育,朱彩娟找上了門,鄰居告訴她,他們搬到新疆去了。新疆,對朱彩娟來說是個過於陌生的概念,在她腦海中存在的無數猜測中,有一個畫面是兒子在草原、在沙漠中長大。
15年前,有個戲班子經過家門口,十幾個小孩子表演“變戲法”。朱彩娟看到其中一個男孩“長得很像丁丁”,急忙買了一個麪包給他。她擔心丁丁像這些孩子一樣流落街頭,“哭得止也止不住”。
“長得像丁丁”,只是朱彩娟的想象。她只能透過其他兒子去想象丁丁長大後的樣子,個子高不高,長得帥不帥,手指軟不軟,耳朵上的小洞還在不在。她也只能拿着其他三個兒子的照片去找那些長得像的人。
11年前,有人告訴她,仙居縣一家網吧裏有個長得像她二兒子的青年。當晚,朱彩娟就帶着二兒子從上海趕回了老家,一家家網吧找過來,一個個人仔細端詳着,最終還是失望而歸。臨走前,朱彩娟將寫有自己聯繫方式的二兒子的照片留給了網吧工作人員,懇求他們看到長相相似的人一定要聯繫自己。
3年前,民間公益組織“十指連心”做活動。朱彩娟連忙提交了資料,還到舞臺上“出風頭”——她覺得這樣也許能夠引起兒子的注意。爲了加入“十指連心”羣,她還學會了在微信上編輯文字,羣裏有許多尋找親生父母的年輕人,朱彩娟隱隱希望裏面有一個是她的丁丁。
半年前,她看到鄰村一個26歲的青年和自己有幾分相像,總覺得他可能是丁丁。得知對方並不是被抱養的孩子,朱彩娟怎麼也不肯相信,“像着了魔似的”非要和小夥子去做親子鑑定。
朱彩娟已經記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將年齡相近、長相相似的人錯認爲丁丁。當現實讓她感到無望的時候,她開始求神拜佛。
她向菩薩許願:希望兒子一切安好。
愧疚
朱彩娟最擔心丁丁走上“歪路”,這種不確定的惶恐多年來一直如影隨形,像一條毒蛇緊緊纏繞在她心上,“那會讓我更加愧疚”。
愧疚,自責,悔恨。她怪自己當初的妥協,怪丈夫當初的無情。丁丁的“消失”擾動了這個家的“平靜”。
踩着縫紉機做衣服時,她會想起丁丁,嘴裏輕輕哼唱着自己編的歌,“我在家裏等着你,等着你回來看看我”、“你在哪裏?你來看看媽媽嗎?”,唱着唱着就淚流滿面。
和丈夫吵架時,話題總是會回到丁丁身上,“當初我問你姓張的可靠不可靠,你說可靠,結果把我的兒子弄丟了……”
兩人鬧上過法庭要離婚,吵得最激烈時,朱彩娟崩潰到想自殺。她手握電線想要自殺,沒有成功,想到自己還沒有找到丁丁,從此再也沒有動過自殺的念頭。“我一定要堅強,我一定要找到孩子。”
在朱彩娟印象中,丈夫項金照曾跟她一起出門找過一兩次兒子,但總是“不急不忙”的——一旦遇到熟人,就和對方聊起了天。她看不慣,索性把丈夫扔在原地,自己先走。
她一度覺得項金照不能理解她身爲人母失去兒子的痛苦,以爲他從不後悔也不曾在意過丁丁。
2006年,項金照患癌去世。彌留之際,他囑託朱彩娟,“一定要找到兒子。”
年輕時的朱彩娟和四兒子,拍攝於河南。受訪者供圖
判決書
“我是一個倔強的人,我知道很多事情只有做了纔不會後悔。”
2015年,朱彩娟再次找到張良,強忍24年的怒火噴薄而出,她雙手掐住對方的脖子,逼問丁丁的下落,“你如果不說,我就殺了你女兒!”
“我把你的孩子弄丟了。”張良終於說了實話。他轉身回屋,拿出一份皺皺巴巴的判決書。
判決書只有三張紙,用幾個訂書針歪歪扭扭地連在一起。落款時間是1992年5月9日。上面寫着:項軍明、應明文和盛堅德等三名雙廟鄉村民,因拐賣兒童罪被判處五年六個月至七年不等刑期。
朱彩娟2015年獲得的判決書,記錄了兒子被拐賣的過程。受訪者供圖
丁丁是被拐賣了。
當年,張良將丁丁送給另一戶人家撫養。期間,項軍明謊稱“自己的朋友沒有男孩”,騙走丁丁。後以2000元轉賣給應明文、盛堅德。1991年12月6日,應明文、盛堅德到樂清準備販賣孩子時被抓獲。
朱彩娟輾轉找到了項軍明,但對方並不清楚孩子的下落。朱彩娟又去找其他的案犯和當時的法官,“很多人不是去世了就是找不到了。”
一晃五年過去了,已經66歲的朱彩娟頭髮愈發花白,判決書已滿是摺痕,尾頁破損的地方用膠帶粘在一起。
今年8月的一天,朱彩娟戴上老花鏡,打開判決書,一字一行地讀了起來。這個動作,五年來她重複了無數次。
“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樂清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指派代檢察員張培獻出庭支持公訴。” 張培獻,朱彩娟發現,這個名字她還沒有聯繫過。
當樂清市檢察院確認有張培獻這個人時,朱彩娟突然感覺“心裏有塊石頭落了地。”
“你已經是我最後的希望了,一定要幫幫我!”電話那頭的張培獻感受到了一個母親的無助,決定幫忙找人。
但他已記不起來這個案子了。當年雖由張培獻出庭公訴,經辦檢察官卻是他人。卷宗上並未寫明被拐孩子的去向,所涉經辦人員大都已去世或退休,唯一在任的經辦人也無法回憶起此案。
9月11日,張培獻聯繫法院調取了公安偵查卷宗。卷宗中,有一名他熟識的公安經辦人。在公安經辦人模糊的記憶中,孩子登報尋親無果後,被大荊鎮一戶人家合法領養。
29年前的丁丁,如今名叫小新(化名)。
重逢
10月13日,朱彩娟得知通過DNA檢測,自己與小新確爲親生母子,她激動地“又是哭又是笑”。
從沒奢望過兒子可以回家生活,她還是忍不住把屋子裏裏外外收拾得乾淨整潔。洗了被子,曬了棉絮,鋪好了新的牀鋪,給丁丁的牙刷、牙膏、毛巾、拖鞋也都準備齊當。
見面的前一晚,朱彩娟邀請朋友在家裏包了“接風”的餃子,親手剝了一大碗桂圓放在冰箱裏。這是一位母親對“團圓”的期盼。
那天夜裏,她輾轉反側,只在牀上躺了兩個鐘頭。時間好像變慢了,從家到樂清市檢察院兩個小時的車程,朱彩娟不停地向窗外張望,“只想車能跑快一點”。
10月15日上午,當朱彩娟邁入檢察院辦公室的瞬間,一眼就鎖定了那個坐在沙發上的年輕人。
年輕人站了起來,個子高高的,長得帥帥的,朱彩娟在他的臉上看到了丈夫的影子,是她無論怎麼想象也無法確切描摹出來的模樣。
當期盼了29年的兒子真切地站在自己面前時,朱彩娟“整個人都呆住了”,她說不出話,只是很想抱抱他。
擔心兒子不願意,擔心兒子的養母傷心,朱彩娟只是拉住了兒子的手,將他的手指在自己手心裏合攏到一起,軟軟的,像他的父親。她又仰頭看向兒子的左耳,那裏曾經有一個針孔大的小洞,現在已經消失了。
母子間失去的29年,讓這場久別重逢與想象中大不一樣,沒有抱頭痛哭,沒有互訴思念,反而有些尷尬、拘束,一種無處不在又無法拉近的距離感。
朱彩娟抱住了兒子的養母,號啕大哭,29年的牽掛、愧疚和遺憾在這一刻釋放了出來。“千言萬語匯成一句話,謝謝你們”,還有一句就是,“我不是來搶孩子的。”
她怕丁丁怨恨,向他解釋,她不想拋棄他,她一直在找他,她願意給他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接受,她不奢求能被叫一聲“媽媽”。丁丁始終一言不發,告別的時候說了句,“常聯繫。”
生活又回到了原本的軌道。朱彩娟繼續經營着她的服裝店,不敢給兒子打電話。
她想給兒子足夠的空間,把全部惦念寄託在了母子倆的合照上——認親那天在檢察院門口拍的。“一天看好幾遍”,熟人來了也要翻出來給人看,朱彩娟仔細揣摩兒子的眉眼,想找出與自己相像的地方,有人說孩子的嘴巴長得像她,朱彩娟覺得不像。她只發現丁丁的頭髮和他哥哥很像,“都是往上翹起來,像蓬起來的公雞頭。”
朱彩娟計劃着,要去丈夫墳前親口告訴他,丁丁找到了。“他給我的任務我算是完成了。”她還打算,等下次丁丁回家的時候,要把兒子們都叫回來,一家人一起喫個飯,拍一張全家福。
如果說生活有什麼變化,那就是朱彩娟比以前哭的次數更多了。親朋好友紛紛打電話來恭喜她,誇她是個“偉大的母親”、“了不起的女人”,聽到這些,朱彩娟只是哭。
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朱彩娟哽咽着反問,“你說,我是不是一個偉大的母親?”
“我不知道。”她自問自答,忍不住哭出了聲。
新京報記者 張熙廷
編輯 劉倩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