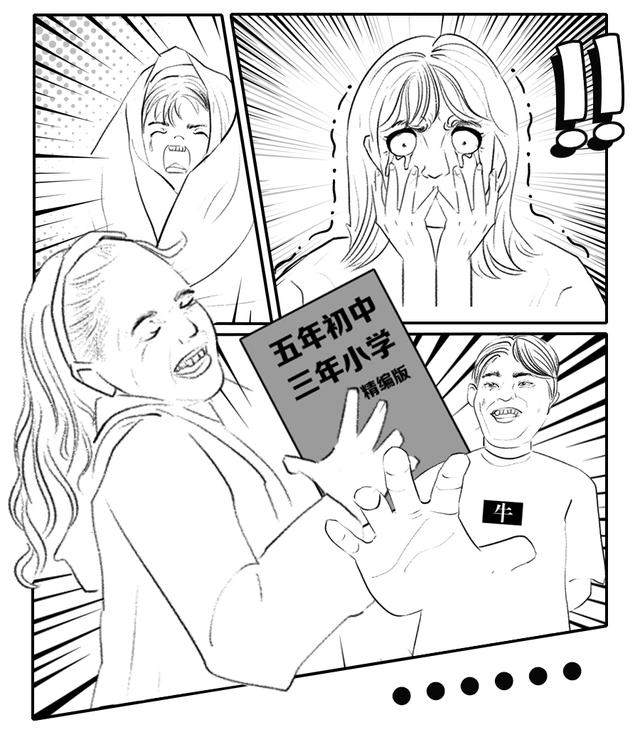孔乙己爲何總被誤讀?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蔡輝
“十日晴。錄文稿一篇訖,約四千餘字,寄高一涵並函,由二弟持去。夜風。”這是魯迅於1919年3月10日,寫下的日記。
《魯迅全集》三次提及高一涵,他是陳獨秀的同鄉和好友,被視爲當時《新青年》的二號人物。1918年1月(4卷1號),周作人開始在《新青年》上發稿,到4卷5號,魯迅發表《狂人日記》,此後發表作品50餘篇。
魯迅不是北京大學正式教員,也非《新青年》編委,與陳獨秀、高一涵往來不多,成稿多託“二弟”(即周作人)帶去。
一般認爲,日記中的“文稿”即魯迅的第二篇白話小說《孔乙己》(魯迅在1912年寫過文言小說《懷舊》,發表在1913年的《小說月報》上),但《孔乙己》僅2600多字,加上附記,不到2800字,“四千餘字”從何而來?
對於《孔乙己》,評價紛紜。
成仿吾說:“作者前期中的《孔乙己》《藥》《明天》等作,都是勞而無功的作品,與一般庸俗之徒無異。”
葉公超也認爲:“魯迅的諷刺作品還有一點缺憾,就是雜耍的成分太多,如孔乙己的‘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孔乙己》是魯迅最滿意的一篇小說,他的學生孫伏園說:“譯者要先問原作者的意見,準備先譯原作者最喜歡的一篇,那麼據我所知道,魯迅先生也一定先薦《孔乙己》。”
看法不同是小說的魅力之一。《孔乙己》寫於104年前,如今又成網友的議論焦點,但閱讀也應進步,已澄清的種種誤解,不必再重複。

趙延年《孔乙己》插圖
孔乙己本姓孟?
《孔乙己》是名篇,相關研究頗多。據周作人《魯迅小說裏的人物》,孔乙己的原型是家鄉的“孟夫子”:
本來姓孟,大家叫他作孟夫子,他的本名因此失傳……他是一個破落大戶人家的子弟和窮讀書人的代表,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寫出了這一羣人的末路。他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以致窮得幾乎討飯。他替人家抄書,可是歡喜喝酒,有時候連書籍紙筆都賣掉了,窮極時混進書房裏去偷東西,被人抓住,硬說是“竊”書不能算偷,這些都是事實。他常到咸亨酒店來喫酒,可能住在近地,卻也始終沒人知道,後來他用蒲包墊着坐在地上,兩手撐了走路,也還來喫過酒,末了便不見了。魯迅在本家中間也見過類似的人物,不過只具一鱗一爪,沒有像他那麼整個那麼突出的,所以就描寫了他。
至於本家中“類似人物”,指“四七伯伯”周秉模,曾當幕友、師爺,擅書法,晚年嗜鴉片和酒,瘦得皮包骨,縮在破棉袍中凍死。
另有傳說稱,紹興某讀書人生計無着,穿長衫賣蔬菜(一說賣燒餅油條),恥於叫賣,別的小販喊“小白菜五分一斤”,便喊“亦然”,被譏爲“亦然先生”,“亦然先生”也曾“多乎哉?不多也”,似屬臆說。
魯迅曾寫道:“作家的取人爲模特兒,有兩法。一是專用一個人,言談舉動,不必說了,連微細的癖性,衣服的式樣,也不加改變……二是雜取種種人,合成一個,從和作者相關的人們裏去找,是不能發見切合的了。”
顯然,孔乙己屬於“雜取種種人”。
小夥計有魯迅的影子
《孔乙己》發生在魯鎮,無此地,“咸亨酒店”實有。
周作人說:“這是一個小酒店,卻有雙間店面,坐南朝北,正對着魯迅故家新臺門的大門。這是周家的幾個人所開設,請了一個夥計一個徒弟照管着,但是不到兩年就關門了。”
孫伏園卻說:“‘咸亨酒店’卻是一個真店號,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斜對門,我還見過多少回,大概至今還在,這種小規模的老字號是不大容易倒的。”
《孔乙己》用第一人稱,被視爲“匠心”,或屬過度解讀。當時白話小說技術不成熟,第一人稱易帶入,《狂人日記》便用第一人稱,較晦澀,《孔乙己》更流暢,日本學者竹內好認爲:“作爲小說家的魯迅正式完成的作品……應該要等到《孔乙己》的出現。”
《孔乙己》中的“我”有魯迅的影子。
小說中,“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咸亨酒店裏當夥計,掌櫃說,樣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魯迅自己在十一二歲時,父親周伯宜患病,“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日本學者丸尾常喜在《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中說:“關於父親的脾氣,魯迅則幾乎沒有說及。只是據周建人回憶,有一次父親突然無來由地大發脾氣,把飯碗和酒杯扔到窗外,而平日裏總是沉於自我苛責之中居多,臨死前也自言自語說‘呆子孫’。”
魯迅曾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爲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與小說中“掌櫃是一副兇臉孔,主顧也沒有好聲氣,教人活潑不得”契合。
不想和林紓摻和
《孔乙己》發表時,附一段說明:
這一篇很拙的小說,還是去年冬天做成的。那時的意思,單在描寫社會上的或一種生活,請讀者看看,並沒有別的深意。但用活字排印了發表,卻已在這時候——便是忽然有人用了小說盛行人身攻擊的時候。大抵著者走入暗路,每每能引讀者的思想跟他墮落:以爲小說是一種潑穢水的器具,裏面糟蹋的是誰。這實在是一件極可嘆可憐的事。所以我在此聲明,免得發生猜度,害了讀者的人格。
這是爲與林紓區別。
林紓寫文言小說《荊生》,稱皖人田其美(指陳獨秀,田姓出於陳姓,美即秀)、浙人金心異(指錢玄同,金即錢,異對同)、“不知其何許人”狄莫(指胡適,狄即胡,《論語》中有“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楊伯峻先生釋爲:君子對天下事,無親疏之分。莫、適相對)。三人遊山,醜詆孔子,“偉丈夫”荊生挺身而出,痛揍三人。
一說荊生即“經生”,林紓曾隨宗鶴拳祖師方世培習武,“被酒時時帶劍行”,荊生就是林紓。
一說荊生是軍閥徐樹錚,劉半農說:“衛道士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藉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爲小徐的徐樹錚。”徐樹錚喜桐城派,他的心腹幕僚臧蔭松與林紓有往來。
林紓另有文言小說《妖夢》,提到“元緒公”,影射蔡元培,因杜預注《左傳》中有:“大蔡,大龜也,一言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每日評論》回罵稱:“這竟是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門上畫烏龜的行徑了。”
孔乙己是一羣人
魯迅如此小心,說明《孔乙己》易被誤會成“諷刺林紓”。
1905年12月,清政府廢科舉,到《孔乙己》寫作時,已歷13年,大批傳統讀書人陷入赤貧,成“邊緣人”。在《退想齋日記》中,山西舉人劉大鵬抱怨:“學堂之害,良非淺鮮,自學堂設立以來,不但老師宿儒坐困家鄉,仰屋而嘆,即聰慧弟子,亦多棄儒而就商。”
1914年,58歲的劉大鵬實在找不到工作,在日記中寫道:“予因窮,厄於鄉,無一求食處,不得已而就煤窯之生涯。”
學堂替代私塾後,教育成本大增,普通家庭難以負擔。傳統讀書人中,富而年輕者或去城市發展,或成劣紳,魚肉鄉里。老而貧窮者謀生無門,鄉村識字率大降。鄉土世界既有尊師重教的傳統,也有鄙夷讀書人的傳統,世風推漲下,後者惡性膨脹。
丸尾常喜注意到,孔乙己很像魯迅家鄉目連戲中的“科場鬼”,每到節日,戲班深入鄉村,“科場鬼”描摹落魄讀書人的各種姿態,引鄉民發笑。
在《孔乙己》中,14次寫到“笑”,很多是“鬨笑”。鄉民故意問孔乙己“當真識字麼”,孔乙己不屑於回答,鄉民挖苦說:“你怎的連半個秀才也撈不到呢?”半個秀才指“佾生”,是童試未成但成績較好者,下次考試時可免縣試、府試。
嘲笑孔乙己,是爲表達對知識的鄙夷,以撫慰身份焦慮。而失去圈子的孔乙己只能配合這種戲弄,以免“無緣社會”,他躲在長衫、文言文、“竊書不算偷論”等背後,才能找到自己,才能支撐起卑微的自尊。
魯迅寫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羣人。
批評源於沒看懂
《孔乙己》問世不久,便被選入中學課本,但葉公超批評說:“魯迅的諷刺小說都不如他的抒情的成功,大概也是性情的關係。我感覺阿Q、孔乙己、木叔和愛姑等等都似乎是舊戲裏的角色,丑角的色彩尤其濃厚。”
葉公超犯了一個常見錯誤:把《孔乙己》看成諷刺小說。
唐弢先生將該誤會升華爲:“中國文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善變’,應時而變、應勢而變、應利而變,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對文人的身份缺乏最起碼的尊重和持守。”
“趨利避害”是成年人的通則,各社會羣體均擅長。這些議論完全脫離了魯迅的創作本意。
據曾秋士(即孫伏園)的《關於魯迅先生》:“我曾問先生,其中哪一篇最好,他說他最喜歡《孔乙己》,所以已經譯了外國文。我問它的好處。他說能於寥寥數頁之中,將社會對於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寫出來,諷刺又不很顯露,有大家的作風。”
《孔乙己》的主旨是寫“社會對於苦人的冷淡”,殺害孔乙己的兇手,一是未出場的丁舉人,一是“鬨笑”的看客們。葉公超顯然沒理解這一層,如果《孔乙己》只爲諷刺,魯迅豈不也成“鬨笑”的看客?
日本記者丸山昏迷早在1923年便指出:“(魯迅)作爲創作家同時又是社會改革家,他在其作品裏濃厚地表現出這種色彩,《孔乙己》等就是其中之一例。因爲他非難了許多中國人對於過去舊中國的留念,而把這種留念貶得一文不值。”
《孔乙己》的諷刺中寄寓着無限同情,想不到100年後,很多讀者反而讀不出這層意思。
勿忘《孔乙己》之美
成仿吾、葉公超等批評《孔乙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它太簡單了”,人物漫畫化,難與歐洲小說比肩。
一方面,西方經典小說多聚焦城市生活,而當時農村佔中國人口比例的90%,鄉村社會舞臺小,自我呈現充滿戲劇性,這是時代的真實寫照,不能爲了寫作高級,便背離真實。
另一方面,正如學者王富仁所說:“成仿吾對魯迅描寫的中國社會人生還缺乏起碼的人生體驗,因而他也根本不瞭解這個世界。”深入分析中國城市生活中的複雜體驗,仍可見深厚的鄉土文化習慣、認知習慣、傳統觀念等的影響。《孔乙己》不簡單,其困境在今天仍有反思價值。
遺憾的是,對《孔乙己》的解讀多是社會的、政治的,而非審美的。
據學者苗順芳的《〈孔乙己〉教學史研究》,1956年第一部《語文教學大綱》,便將《孔乙己》的教學重點定位在:“孔乙己的善良、迂腐和好喫懶做,封建科舉制度對他的毒害,丁舉人的殘酷橫暴;作者諷刺像孔乙己這樣的知識分子的迂腐無能,同情他們的不幸遭遇;作品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識分子的罪惡;人物性格的描寫。”
上世紀80年代後,解讀多元化,但仍圍繞社會意義等展開,較少關注審美意味。
《孔乙己》是如何在諷刺與同情之間切換的?如何延續傳統白話小說的手法?如何描繪“反同情”?如何在如此短的篇幅中,層層鋪墊出悲劇感?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何……凡此種種,介紹不多。
小說首先是美的,離開美去談時代意義、問題意識等,則種種誤讀,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