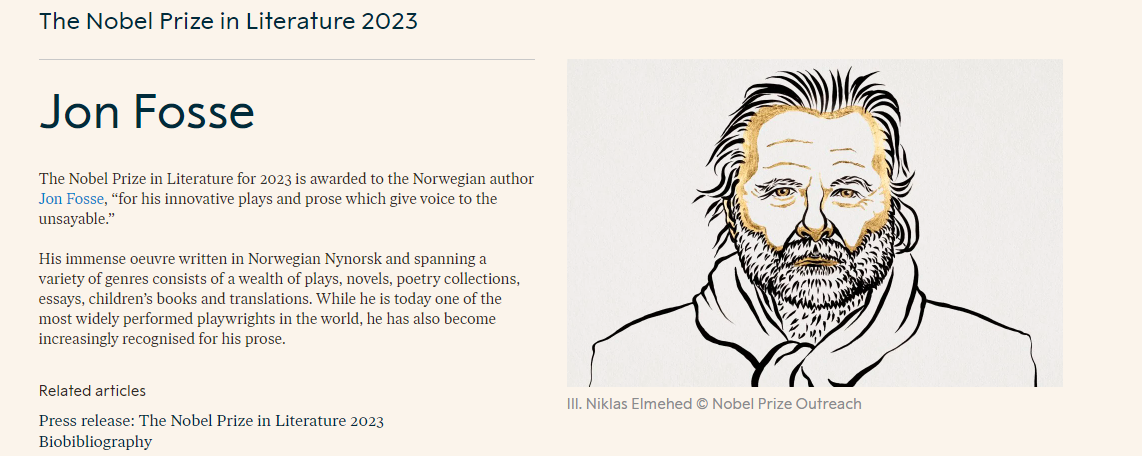202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恩·福瑟是誰?
轉自:澎湃新聞
有“新易卜生”之稱的約恩·福瑟是當代歐美劇壇最富盛名、作品被搬演最多的在世劇作家。其作品迄今已被譯成四十多種文字,並曾多次獲得各類國際藝術大獎。此外,他也是近兩年來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
對大多數中國讀者而言,相較於他的同行,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約恩·福瑟無疑是一個更陌生的名字。在易卜生和斯特林堡之後,北歐的劇作(甚至文學)似乎都被更喧譁熱鬧的英美文學圈給淹沒了。

約恩·福瑟
但約恩·福瑟可不是一個應該被忽略的作家。在易卜生獎評委會的授獎詞中這樣寫道:“約恩·福瑟是當代戲劇界最頂尖的名字之一。他創造了一個自成一格的戲劇世界,他是一個宇宙、一片大陸,自他居住的西挪威延伸至亞洲、南美、東歐和世界其他區域。”
然而,福瑟坦言,早年作爲一名作家,面對戲劇世界,他常常感到自己是個邊緣的外圍人士。九十年代初期,他就已經出版過小說、散文和詩歌集,並在挪威文學界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但他並不經常上劇院,寫過的幾個劇本都是奉命而爲,尚不確定戲劇是否他的真正專長。“我不喜歡戲劇,”他曾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我認爲它很蠢,因爲戲劇總是因循守舊——不少當代戲劇依然如此。觀衆表現得很傳統,劇本也都固步自封。那不是藝術,那只是因循守舊。”
只是戲劇又恰恰符合他寫作的興趣。“在小說裏,你只能運用詞語,而在戲劇裏,你可以使用停頓、空白還有沉默:那些沒有被說出口的東西。一種啓示。” 在歐洲,福瑟被冠以“新易卜生”、“新品特”或“新貝克特”的名號,但他的作品更抽象、更富詩意,從某種意義上而言,也更殘酷。
他的易卜生文學獎獲獎作品《名字》講述了一個同一屋檐下相互疏遠的家庭的故事。一個懷孕的女孩和這個孩子的父親無處可去,他們回到了女孩的父母家,城外一個離海很近的地方。但是女孩的父母從未見過這個準爸爸男孩,並且對懷孕的事也一無所知。這個懷孕的女孩其實非常不想住在這裏,男孩也感覺到了他不受歡迎。這是一個功能缺失的家庭,對話幾乎無法進行;所有必要之事都變爲習慣性的姿態,每個人都感到孤獨。本劇也討論瞭如何給這個未出生的孩子起名的問題,以及我們如何運用語言來創造一個對我們來說有特殊含義的更加深刻的內涵。在《有人將至》裏,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買下一座海邊的老房子,爲的是遠離生活的紛擾,但事實是他們無法擺脫“有人將至”的念頭。當一位鄰居突如其來地敲響他們的屋門,一種不確定感悄然打破了兩人間的平衡。《一個夏日》(2000年北歐國家戲劇獎獲獎作品)和《死亡變奏曲》(2002年北歐國家戲劇獎獲獎作品)都探討了死亡、記憶與孤獨對生者的糾纏。在《一個夏日》中,丈夫在某一天毫無預兆的選擇了死亡。他離開家走向大海,從此再也沒有回來。而妻子則自此日復一日地站在窗前,面對着大海,無法擺脫記憶的糾纏。在另一部作品《死亡變奏曲》中,大海吞噬了他和她的女兒,迫使愛情早已死去多年的他們重新面對彼此,面對記憶和過往,爲這場突如其來的悲劇困惑着,卻無從尋找答案。
閱讀他的作品會讓你產生一種幻覺,這些“他”和“她”其實是同一個人,一遍又一遍地經歷着同樣的疏離、悲抑、誤解與孤獨。與傳統的西方現實主義戲劇不同,福瑟戲劇中的衝突更多地以一種暗示而非直接表達的形式存在舞臺上。他筆下的角色們將自己的想法和感知納藏於心,以至於我們無法確定他們的表達是否就是促成他們行爲的原因,也不確定我們是否能夠真正理解這些男人和女人,甚至,我們自己。

《有人將至》
或許正是福瑟作品中人物面目的模糊與其經歷情感的普世性讓他的劇作在全球各地都找到了觀衆。2010年,福瑟最早、也是最知名的作品之一《有人將至》(Somebody is going to come)在十月的北京迎來首演;幾乎同一時刻,法國已故導演帕特里斯·候夏(他也是電影《瑪戈皇后》的導演)在倫敦執導了他的近作《我是風》(I am the Wind)。唯一沒能被他征服的只有英國人。2002年,《夜曲》(Nightsongs)在皇家宮廷劇院的演出後,《獨立報》的劇評家拿他的名字開起了玩笑:“‘約恩’,像它的挪威發音一樣,讓我們都打起了哈欠(Jon的挪威發音和yawn確實接近)。”《每日電訊》說的更不客氣:“他的劇作矯揉造作得可悲,冗長得令人生厭。”2005年,他的另一齣戲《暖意》(Warm)又遭到《衛報》的吐槽:“(觀看他的作品)像是對着一幅一團糟的拼圖,你感覺自己應該要把它完成,但最後能得到的獎賞卻少之又少。”在這個固守於社會現實主義戲劇、患有“後劇場恐慌症”的海島上,約恩·福瑟的作品始終沒能打開屬於他的受衆羣——儘管它們都找到了最棒的英語譯者。
福瑟的戲劇都是用新挪威語,或稱尼諾斯克語(以口語爲基礎的挪威書面語)寫成的,一種“事實上從沒有人用來說話”的語言。如同法國或德國的劇場,他的戲劇語言和人們在街上談話的方式截然不同。福瑟將筆下人物的對話成爲“生命的基本樂音”:簡短的句子、大片的空白和停頓。有些人認爲他的戲劇令人抑鬱,對此福瑟無法否認。但他也同樣拒絕闡釋自己的作品:“我坐下、傾聽,我書寫聽到的一切。在我動筆之前,我對整個故事和其中的人物毫無概念。那是很棒的經歷。我探入了未知,並帶回了某種曾經未知的東西。”
我們很難將福瑟歸類爲某種類型的寫作者。他的寫作確實受到了貝克特的影響,《有人將至》規避戲劇動作的表現形式毫無疑問有着《等待戈多》的影子,但這並不意味着福瑟就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描寫城市與鄉村生活的分歧、留守鄉鎮的老人等待着移居城市的孩子來訪、在新環境中感到迷失的茫然,以及無處可依的悵惘與荒蕪。這麼看來,他幾乎又成了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作家。除了孤獨、痛苦、絕望和死亡,他偶爾也不經意地透出幾筆希望。《一個夏日》中的年老女人這樣吟誦:“從我的內心深處/從那空虛的黑暗中/我感覺到那空虛的黑暗靜默地/向外發着光。”
這種模糊的不確定性讓福瑟成了一個頗具挑戰性的作家,但越來越多的導演和演員開始願意接受這項挑戰。這個十一月,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將連續上演五場福瑟的作品,其中包括了本書收錄的《一個夏日》、《死亡變奏曲》及《有人將至》。對大多數中國觀衆而言,觀看或閱讀福瑟的作品也將成爲一段探入未知的旅途,在那些空白過後,他將促使我們以全新的方式進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