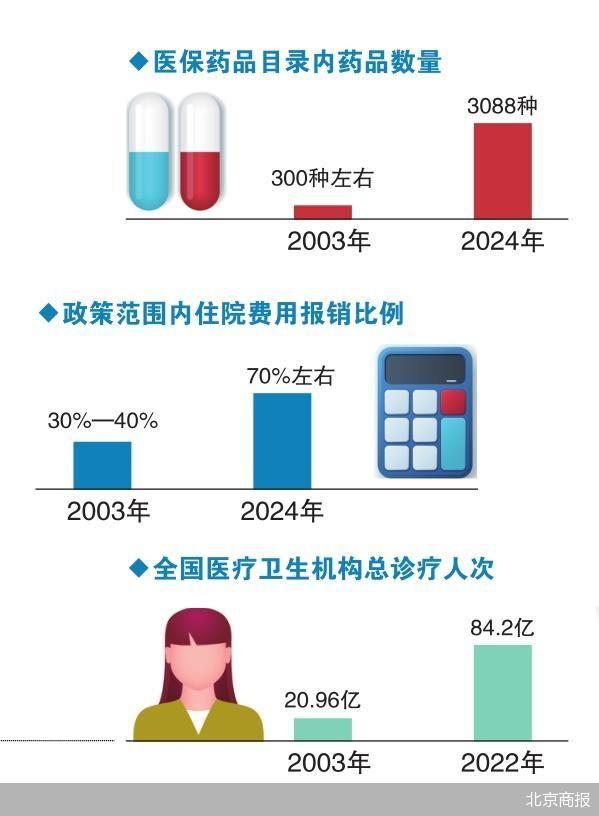醫院領導帶頭騙保億元,藥代篡改患者報告,“兩高”曝光這些醫保詐騙案
我國將進一步做好打擊醫保騙保的行刑銜接,對醫保詐騙犯罪零容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3月1日印發的《關於辦理醫保騙保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稱:將加大對醫保騙保的犯罪人員的財產刑力度;對部分重複收費、超標準收費、分解項目收費等更加隱蔽的醫保騙保行爲,以詐騙罪論處;對“職業騙保人”“幕後組織者”等犯罪分子嚴肅追究刑事責任。
同日,“兩高”還公示了8起依法懲治醫保騙保犯罪典型案例,此時距離最高法官網上一批典型案例公佈已間隔2年多的時間。本次典型案例中納入了“醫藥公司醫藥代表篡改患者檢測報告騙取醫保基金”的例子,此外還囊括了民營醫院犯罪集團中的首要分子因詐騙罪被判“頂格處罰”,衛生院院長合謀挪用醫保基金近2000萬被判貪污罪等例子。
在過去的一年,我國共偵破醫保詐騙案件2179起,抓獲犯罪嫌疑人6220名,打掉犯罪團伙346個,移送醫保部門查處違法違規醫藥機構263家。
公安部刑事偵查局副局長、一級巡視員陳士渠近日公佈了上述這組數據。陳士渠說,2021年至2023年,公安部會同國家醫保局、國家衛健委等部門持續專項打擊整治醫保詐騙違法犯罪,針對虛假診療、虛開票據、篡改檢測報告、串換藥品耗材、購銷醫保“迴流藥”等詐騙醫保基金行爲,組織開展專案攻堅;快偵快破了44起性質惡劣、案值較大、涉案人員較多的跨地域重特大案件。
其中,浙江摧毀兩個利用特病病人套銷醫保藥品的犯罪團伙,涉案金額12.5億元;遼寧破獲某療養院涉嫌詐騙醫保案,涉案金額4億元;重慶破獲2家民營醫院和1家醫藥公司涉嫌詐騙醫保案件,涉案金額3億元。
隨着專項整治工作的全面開展,打擊欺詐騙保高壓態勢日漸鞏固,但部分騙保行爲由臺前轉入幕後,醫保詐騙犯罪仍然高發多發。爲此,去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和財政部加入醫保騙保專項整治工作,與醫保、衛健和公安形成五部門聯合執法,開發出“特種病藥物”“異常人員就醫”“空刷醫保統籌基金賬戶”等數十種詐騙醫保基金案件數字監督模型。
加大財產刑的力度
“兩高”公佈的首起案件,是一起民營醫院長期實施騙取醫保基金的“大案”,涉案金額過億。
2013年1月至2016年8月間,被告人劉某甲、劉某乙、劉某丙作爲天津某民營醫院的投資人、實際經營者、利益所得者,組織、領導醫院員工通過虛假宣傳、虛開藥方、虛增售藥、虛假住院等手段空刷醫保卡。
犯罪期間,上述涉案人員還發展辛某蓮等人作爲聯絡員,聯絡員又發展張某文、王某森等人作爲村級斂卡人或司機,在天津市濱海新區、靜海區等地進行宣傳,以持醫保卡到醫院看病可以免費治病、免費接送、免費喫飯、免費住院以及出院時獲贈藥品或現金等爲噱頭,吸引大量城鄉醫保持卡人到醫院虛假診治、住院,通過空刷醫保卡方式騙取醫保基金。
根據調查,該醫院人員通過以上方式騙取天津市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中心(後相關職能的承接轉爲天津市醫療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共計1億餘元。
天津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爲,劉某甲、劉某乙、劉某丙以非法佔有爲目的,採用空刷醫保卡的方式騙取醫保基金1億餘元,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爲均已構成詐騙罪。劉某甲、劉某乙、劉某丙招募大量醫護、工作人員、宣傳人員實施犯罪,持續時間久、範圍廣、數額大、人員多,已形成犯罪集團。
據此,依法認定劉某甲、劉某乙、劉某丙犯詐騙罪,判處劉某甲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處劉某乙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判處劉某丙有期徒刑十三年,並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
根據我國刑法第266條規定,構成詐騙罪,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典型案例中對劉某甲的刑罰已經屬於‘頂格判罰’了,顯示出司法機關依法嚴懲醫保領域欺詐騙保犯罪的態度。”醫法匯創始人、律師張勇對一財表示。
對“職業騙保人”“幕後組織者”等人員重點打擊,是“兩高”近年來多次提到的問題。此次指導意見中不僅予以再次強調,還提出了具體從嚴打擊的措施,包括:對幕後組織者、職業騙保人等,即使具有退贓退賠、認罪認罰等從寬情節的,也要從嚴把握從寬幅度,並明確列舉了四種可以從重處罰的情形。
爲加強追贓挽損,指導意見還明確:加大財產刑的力度,規範罰金刑適用,從嚴掌握緩刑適用。
之所以要“加大財產刑的力度”,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合夥人、律師劉豔燕在接受一財採訪時稱,這是因爲詐騙罪屬於逐利型犯罪,在對犯罪分子判處主刑的同時,要從經濟上嚴肅制裁,提高醫保騙保犯罪成本,剝奪犯罪分子再犯能力,實現預防效果,有效遏制該類犯罪的發生。
對於“規範罰金刑適用”,劉豔燕說,我國刑法對詐騙罪的刑罰規定中,罰金刑採用了無限額罰金的立法模式,也就是說對罰金數額的確定沒有明確的標準和範圍,因此,司法實踐中詐騙罪的罰金刑量刑可能存在不均衡的情形,類似案件在不同地區甚至同一地區的判決中,罰金數額可能相差數倍。有必要對罰金刑的適用予以規範,避免造成“同案不同判”的局面。
至於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對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職業騙保人等重點人員一般不適用緩刑,劉豔燕表示,對這些重點打擊對象,即使沒有前述規定,司法實踐中考慮犯罪情節、主觀惡性等,適用緩刑概率也較低。指導意見明確規定後,適法標準更加清晰、具體、可操作,對這些人員也形成強有力的震懾。
醫藥代表虛構基因檢測被判詐騙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長陳學勇在指導意見發佈會上提到,近年來,儘管醫保騙保的犯罪主體主要爲參保人員(54.08%),但也呈多元化趨勢,有部分案件涉及藥品生產企業。
兩年前,跨國藥企阿斯利康因員工騙保被國家醫保局聯合深圳公安局“點明”。該起事件的輿論發酵讓“醫藥代表篡改腫瘤患者基因檢測結果”的新型騙保行爲,一度進入公衆視野。
兩年後,在“兩高”此次公佈的8起典型案件中,也納入了一起醫藥代表騙保案件。該起案件發生在另一一線城市北京。無獨有偶的是,涉案醫藥代表騙取醫保基金的方式也是與虛構基因檢測有關。
在該起案件中,被告人高某系某醫藥科技公司醫藥代表,負責推銷公司用於治療肺癌患者的藥品,每銷售一盒,提成200元至300元。2018年10月,該藥納入國家醫保目錄,醫保報銷的條件是相關基因檢測結果爲陽性。患者李某診斷爲肺癌,手術後自費購買該藥。2020年7月,高某找到李某,聯繫檢測機構爲李某做基因檢測,檢測結果爲陰性。2020年8月至2021年2月,高某明知國家肺癌用藥政策,在北京朝陽中西醫結合急診搶救醫院等地,以編造患者基因檢測陽性結果的方式,使患者通過醫保報銷開藥,造成醫保基金支出8萬餘元。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爲,高某以非法佔有爲目的,虛構基因檢測結果,騙取醫保基金,數額較大,其行爲已構成詐騙罪。高某如實供述所犯罪行,認罪認罰,全額退賠,依法可從輕處罰。據此,依法認定高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判決已生效。
值得一提的是,“兩高”在典型案件解析中還特別對醫藥公司醫藥代表爲達到銷售藥品以獲取業績獎金目的,“私自接觸患者”的行爲作出警示。
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對一財表示,隨着精準醫學發展,目前靶向藥在腫瘤治療等領域的應用更加廣泛。由於此類新藥使用之前,需事先進行基因檢測,從某種程度上也滋生了一些醫藥代表和基因檢測公司的逐利驅動。堵住醫藥企業營銷環節的監管漏洞,已成爲全國各地在打擊新興欺詐騙保行爲的一個重要方面。
醫院“重複收費”情節嚴重者,可判詐騙罪
隨着我國打擊欺詐騙保的力度持續加大,部分騙保行爲也由臺前轉入幕後,逐漸向過度診療、超標準收費等行爲轉變。
在過去的一年,多地對醫保定點醫院超收醫療費給予行政處罰。
呼和浩特市醫保局1月底公佈的“2023年對27例醫療保障基金監管典型案例曝光”通報顯示,該市當年有27家醫療機構因超標準收費、重複收費、多收費、超限制範圍用藥、過度檢查、過度診療等問題被責令整改,追回違規費用,其中包含13家公立醫院。
另據湖南省醫保局去年12月發佈的相關通報,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因違法違規使用醫保基金,被判約98萬元的罰金。
而根據新規,發生前述騙保行爲的醫務人員,情節嚴重者,也會面臨刑事處罰。指導意見稱,定點醫藥機構(醫療機構、藥品經營單位)以非法佔有爲目的,實施“重複收費、超標準收費、分解項目收費”,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的規定,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金春林認爲,“過度診療”是醫保騙保查處中的一個難題,由於醫療服務的高度專業化、醫生診治的差異化,如感冒懷疑可能肺炎而做CT檢查等現象,往往難以準確界定其合理性。此外,之前也有很多報道,ICU 搶救時使用的輸液數量和相關醫用材料遠超正常合理範圍。
至於是否構成詐騙犯罪,劉豔燕認爲,要嚴格依據詐騙罪的構成要件來認定,例如對超標準收費部分是否具有非法佔有目的,是否明知故意,是否採取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詐騙手段,以及超過標準的比例大小等,綜合認定。不能機械套用規定,給醫療醫藥行業正常發展造成障礙。
加強行刑銜接
由於前述“重複收費”等醫保騙保行爲,按照不同情節,既可能處以行政處罰,也可能處以刑事處罰。對此,指導意見強調,建立健全協同配合機制,規範健全行刑銜接機制。
張勇認爲,要將這種“行刑銜接”機制落地實施,下一步仍需在加強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信息溝通、以及明確案件移送的標準和程序等方面下功夫。
“還要形成相應的反向刑行銜接機制。”劉豔燕認爲,對不構成犯罪、依法不起訴或免予刑事處罰的醫保騙保行爲人或者單位,不能一放了之,需要給予行政處罰、政務處分或者其他處分的,應當依法移送醫保部門等有關機關處理。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對2021-2023年醫保騙保犯罪案件的梳理,罪名呈現集中化趨勢。其中詐騙罪佔93.65%。
劉豔燕對此表示,儘管刑罰與行政處罰性質不同,不能簡單對兩種處罰進行數額比較。但在處罰措施上,鑑於詐騙罪可以給予單處罰金的刑罰,而目前罰金刑的適用又沒有明確標準,相對於行政處罰的罰款而言,如果只比較金額,部分案件可能會形成構成犯罪的罰金數額比不構成犯罪的罰款數額還低的情形,可能出現所謂的處罰“倒掛”的情況。爲避免誤解,也需要司法機關與行政部門做好案件處置的協同配合工作,在案件處理結果上充分體現差異性和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