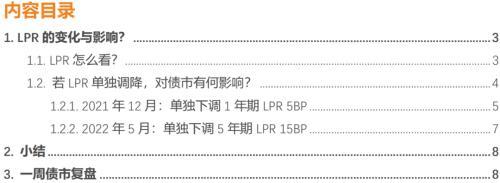當槓桿遇到平臺
【超級平臺】
——平臺跨界競爭的反壟斷問題
在上一篇專欄中,我們對平臺利用包抄戰略進行跨界競爭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了平臺可能利用自身已有的資源,將自己在一個市場上的市場力量傳遞到另一個市場中。在反壟斷的文獻中,企業的這種行爲有一個專門的名詞——槓桿傳導。
在實踐當中,反壟斷機構很早就開始關注槓桿傳導的影響,並經常援引它來作爲裁決的理由。例如,在前幾年的可口可樂併購匯源案中,併購會導致可口可樂將其在碳酸飲料市場上的支配地位傳導到果汁飲料市場就是商務部否決可口可樂併購請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這一決定背後的理論基礎,就是關於槓桿傳導的相關理論。
在平臺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跨界競爭現象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規模上,都要比傳統經濟條件下大得多。由於平臺的多邊市場性質,其在一個市場進行競爭時,往往會引用到在其他市場上的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市場上出現的槓桿傳導現象可能要比過去任何時間都要多、都要頻繁。那麼,這類現象對於市場的運作效率、對於消費者福利來說,究竟會產生什麼影響?爲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先對槓桿傳導本身進行一番分析。
槓桿傳導的前世今生
1、早期理論:一個壟斷不好,兩個壟斷更糟
早期,人們對於槓桿傳導理論的認識是十分樸素的:既然壟斷對於市場運作效率、消費者福利都會產生負面影響,那麼一個市場被壟斷本身就已經是很糟糕的了,如果讓這種壟斷衍生出新的壟斷,就更是一件糟糕透頂的事情。基於這種樸素的認識,反壟斷機構在一開始就對企業跨市場傳導其市場力量的現象十分警惕——無論在實踐中,企業究竟利用什麼手段實現了這點。
儘管這種樸素思想的影響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案例(例如1936年的IBM案),但一般認爲,對這種思想的首次正式司法應用是1948年的格里芬斯案。在這個案例中,被告格里芬斯名下的幾家關聯企業在美國西部的85個城鎮中擁有影院。在其中的53個城鎮,格里芬斯的電影院擁有壟斷地位,在另外的32個城鎮中則面臨着競爭。在和發行商的談判中,格里芬斯告訴他們,如果想在僅有格里芬斯影院的53個城鎮播放電影的話,他們就必須將其他32個小鎮的電影首映也安排在格里芬斯影院。美國最高法院在審覈該案時強調,利用已有的壟斷力量來阻礙對手或者獲取競爭優勢是違法的,即使這種壟斷力量本身是通過合法手段獲取的也不行。據此,法院判定格里芬斯的行爲違反了《謝爾曼法》的相關規定。
在格里芬斯案之後,槓桿傳導理論就經常被應用到涉及跨市場進行壟斷力量傳導的案件,尤其是與搭售相關的案件中。在很多著名案件,例如1953年的泰晤士-皮卡尤恩案,1958年的北太平洋鐵路案、1969年的福特納案、1980年的伯克案的審理過程中,都涉及到了槓桿傳導理論。
2、芝加哥學派的觀點:企業不會這麼做
作爲堅定的“市場派”,芝加哥學派學者們對早期的槓桿傳導理論頗不以爲然。在他們看來,儘管從理論上講,企業確實可以通過槓桿傳導實現多個市場的壟斷,但是這並不會爲它們帶來切實的好處,因此,在實際中它們並不會這麼做。芝加哥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狄雷克特(Aaron Direc-toe)和李維(Edward Levi)曾在195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首次將這一思想表述爲“定額理論”(Fixed Sum Theory),即企業傳不傳導壟斷力量,它可以獲得的利潤總是那樣,不增不減。既然如此,他們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在狄雷克特和李維的基礎上,後來的芝加哥學者們進一步利用價格理論對槓桿理論提出了質疑。其中,最有代表性工作的是鮑曼(Ward Bowman)於1957年發表在《Yale Law Journal》的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鮑曼論證了企業並沒有激勵通過搭售的手段來進行市場力量的傳導。他的邏輯很簡單:如果企業要利用搭售進行市場力量的傳導,那麼前提就是用以搭售的兩種商品應該是彼此互補的。而互補品有個特點,那就是其中一種商品的價格上升,就會導致另一種商品銷量的下降。這樣,企業就不可能利用其市場力量同時抬高兩個市場的價格,獲得更多的利潤。
在這篇著名的論文中,鮑曼曾給出過一個直觀的例子來對此進行說明:一個商人在螺釘的市場上具有壟斷地位,因此可以通過調整價格來獲得超額的壟斷利潤。但他對此還不滿足,希望將這種壟斷地位傳導到原本是競爭性的螺母市場上。
他能不能做到呢?當然是可以的。只要他將螺釘和螺母進行搭售,然後將其價格定得低於單件商品價格之和就行。通過這樣的處理,他就可以排擠掉螺母市場上的對手,從而獲得支配性的市場地位。但是,這樣做對他有好處嗎?答案是沒有!既然這位商人進入螺母市場的前提就是其出售的螺釘螺母價格之和要比原來更低,因此如果將兩樣商品分開看,他至少對其中一類商品做出了降價。爲了便於分析,我們假設他並沒有改變螺母價格,將其按照原本的競爭性價格出售,只是調整了螺釘的價格。這樣,由於螺母價格是競爭性的,因此他並不能從螺母市場上獲取利潤。而在螺釘市場上呢?由於他降低了價格,讓其偏離了原本的壟斷價格水平,因此所能獲得的利潤也比原本降低了。將兩個市場上的利潤一加,這位試圖在兩個市場上同時謀求市場支配地位的商人就會發現,儘管他成功做到了這點,但他所賺到的利潤反而比原來更少了!
那麼,怎麼才能讓獲取的利潤比原來更高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讓經過搭售後的商品組合價格高於分開銷售之和。也就是說,至少要讓其中的一種商品漲價。但是這可能做到嗎?答案是不可能!因爲如果商人試圖這麼做,消費者就會偏好於分開購買兩件商品——以壟斷性的價格購買螺釘,再以競爭性的價格購買螺母,這樣他們付出的成本將小於搭售的情形。
經過以上分析,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儘管從理論上講,壟斷者可以成功地應用槓桿同時在市場上獲得支配地位,但是這對於他們來說其實是無利可圖的。如果他是一個精明的理性人,他就不會這麼做!
當然,企業傳導市場力量的方法並不只有搭售一種。比如,他們還可以進行“掠奪性定價”——利用在一個市場上獲得的壟斷利潤去補貼另一個市場,從而將新市場上的價格壓低到成本之下,進而爭奪市場。一般認爲,企業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排擠掉原有市場上的在位者。一旦在位者離開後,他們就可以提價,從而收割壟斷利潤。對於這種觀點,芝加哥學派的重要代表、法律經濟學的領軍人物——波斯納(Richard Posner)法官就曾進行過激烈的批判。在他看來,當一個企業通過“掠奪性定價”成功獲得了市場的支配性地位,並試圖漲價收割消費者時,超額的利潤就會激發潛在的競爭者進入。爲了阻擋這些競爭者的進入,它們就不得不把價格維持在一個低水平上。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掠奪性定價”需要投入的成本是固定的,而其帶來的收益卻是不確定的,理性的企業家不會作出這樣的選擇。
儘管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很犀利,但有不少人認爲這些觀點並不符合現實——既然企業通過槓桿傳導在多個市場上同時獲取市場力量是無利可圖的,但現實中爲什麼還有人這麼做呢?針對這些疑問,芝加哥學者也進行了回覆。例如,波斯納就曾通過對1936年IBM案的回顧,論證了搭售的合理性。在那個早期的案件中,IBM公司被控用打卡機市場上的壟斷力量來獲得卡片市場上的壟斷。在波斯納看來,IBM這麼做並不是爲了傳導市場力量,而是通過對卡片使用量的掌握,瞭解客戶的使用頻率,從而對其進行價格歧視——在芝加哥學派那裏,價格歧視本身並不是什麼壞事。從這個角度看,搭售似乎就是合理的了(當然,其實這種論述並不能爲常見的一對一捆綁銷售給出合理性解釋,因此還是頗受詬病)。
隨着波斯納、伯克(Robert Bork)、伊斯特布魯克(Frank Easter-brook)等芝加哥學派學者相繼成爲聯邦法官,這一學派的影響開始擴散到反壟斷實踐當中。在後來的一系列著名案件(例如阿拉斯加航空案、法恩曼公司訴阿姆斯特朗世界工業案)中,法院都採用了類似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對槓桿傳導理論進行了否定。
3、芝加哥學派之後:槓桿傳導依然是可能的,必須小心評價
芝加哥學派對於槓桿傳導理論批判的要害在於“誅心”——它並不否認企業利用槓桿進行市場力量傳導的可能性,但認爲企業不會有激勵這麼做。既然如此,傳導壟斷力量當然就不能作爲審理案件的出發點了。
面對芝加哥學派的這種觀點,槓桿傳導理論的支持者如果要維護這個理論,首先就必須重新對企業進行這類行爲的合理性做出解釋。事實上,在與芝加哥學派進行論戰的過程中,就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例如,哈佛大學的兩位教授卡普洛(Louis Kaplow)和沙維爾(Steven Shavell)就指出,芝加哥學派僅僅考慮了靜態的情形,而從動態的角度看,至少在一些特定的條件下,槓桿傳導可以讓企業實現利潤的增進。不過,在芝加哥學派大行其道的背景下,這些聲音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真正對芝加哥學派觀點提出挑戰的理論是“提升對手成本理論”(Raising Rivial’s Cost Theory)。這個理論的出發點基於一個常識性的觀察:要贏得相對優勢,無外乎有兩種辦法,一是讓自己做得更好,二是讓對手變得更糟。儘管在勵志的商業書籍中,對前一種方法的介紹要遠遠多於後一種方法,但在現實中,後一類方法的應用並不比前一種少。
在1987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的一篇論文中,薩洛普(Steven Salop)和謝夫曼(David Scheffman)就把這類大家一直心照不宣的“暗黑”方法用數學模型表達了出來。在這篇簡短的論文中,兩位作者把提升對手成本的努力作爲一種競爭策略引入了模型。我們知道,寡頭企業在市場上競爭,價格是重要的決定因素,而產品的價格定多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企業的成本究竟有多高。這樣,如果能夠設法抬高對手的成本,就等於抬高了對手的價格,會讓自己在市場上變得更有利。那麼企業有沒有辦法成功地讓對手的成本提升呢?當然有,而且有很多!例如,企業可以直接遊說政府,讓政府對其對手進行管制,這樣對手的成本就上去了。如果嫌這樣的做法太簡單粗暴,沒關係,它們還可以選擇更爲“溫柔”的做法,例如採用壓制對手市場份額、提高對手的投入品價格、採用縱向一體化控制供貨商,或者與供貨商簽訂排他性交易協議等手法來達到打擊對手的目的。
我們可以用壓制對手市場份額爲例來對這一理論進行說明。我們知道,企業要想運作,首先要投入比較大量的固定成本,這樣,產量越高,分攤在每單位產品上的平均固定成本就會越低。而與此同時,企業生產每單位的產量還會產生對應的“邊際成本”,由於技術等因素的作用,一般來說邊際成本會在某個點後隨着產量的上升而上升。將這兩種因素疊加在一起,企業面臨的平均成本就會呈現出一種U型的走勢——在達到一定的規模之前,它會隨產量增加而降低,而在達到這個規模之後,它就會隨產量增加而不斷上升。這個臨界的規模,就是所謂的MES。由於在實踐當中,企業會盡可能選擇較小的成本和對手競爭,因此MES對於市場結構的影響就會十分重要。可以想象,如果某個產業的MES只要求這個市場1%的市場份額,那麼這個產業中就可能同時擁有很多互相競爭的企業;而如果某個產業的MES要求一半或更高的市場份額,那麼這個產業就可能會是一家獨大的,率先達到MES的企業可以通過價格上的優勢將對手徹底排擠出市場。一旦有了MES的概念,我們就知道,企業如果要想讓對手的成本上升,從而降低其競爭優勢,並不需要將其徹底擠出市場,而只需要採取手段將它們的市場份額壓縮到MES之下就可以。
根據“提升對手成本理論”,企業利用一個市場上的優勢去爭奪另一個市場的槓桿行爲就可以得到解釋了。在更多的時候,企業其實並不指望完全搶走他人的市場,而只希望擠進去分一杯羹,而憑藉在原有市場上的優勢,它們其實很容易達到這一目標。在某些特殊的條件下,這種跨界的狙擊甚至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如果某個市場的MES很高,在位企業需要很高的市場份額才能進行有效率的生產,如果產量沒達到這一規模就會虧損。那麼,侵入者只需要利用原有市場上的優勢,搶到很小一點的市場份額,就可以成功地打掉在位者的優勢,從而在它手中搶得一大塊利潤。
應該說,“提升對手成本理論”成功地回應了芝加哥學派對於槓桿傳導的“誅心”之論,從而比較好地解釋了現實中槓桿傳導存在的合理性。由於槓桿傳導是切實存在的,因此在面對具體的案例時,就需要根據“合理性原則”對它們進行更爲具體的分析。正如我們在之前的專欄中強調過的那樣,無論是搭售、縱向協議,或者其他用以傳導市場力量的手段,其產生的效果都有正負兩面,我們必須對這兩方面後果產生的成本收益加以比較,才能作出最終的判斷。
平臺時代的槓桿傳導
在對槓桿傳導理論進行了一番長長的回顧後,我們終於可以把關注點回到平臺時代的槓桿問題中來了。
無論是在傳統經濟條件還是在平臺經濟條件下,槓桿理論的作用機理都是類似的,所不同的是,平臺經濟的一些特殊因素會對其作用後果產生影響。和傳統時代相比,平臺的不同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平臺具有很強的跨邊網絡外部性,從而在市場份額變化時會產生類似於“滾雪球”的效應。二是多歸屬可能的存在。在傳統競爭條件下,我們很少會同時去兩家企業購買同品類商品,買了蘋果手機,就很少會買三星手機。但在平臺競爭條件下,我們卻經常會“消費”多個平臺,例如我們可能同時是淘寶和京東的會員、同時使用微信和釘釘。這兩個特徵,對於槓桿的作用效果都是非常重要的。
先看跨邊網絡外部性的影響。顯然,這種效應的存在給不同市場結構帶來的後果是不一樣的。爲了簡化起見,我們先考慮一種情形:即兩個市場的競爭主體都是平臺,但其中的A市場已經被某平臺企業壟斷,而B市場則正在形成,處於多個平臺的競爭階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A市場上的壟斷者通過搭售、掠奪性定價等行爲將自己的市場力量傳導到B市場,就很容易獲得較大的市場份額。通過“跨邊網絡外部性”,它可以進一步地將這種地位鎖定,從而將對手排擠到市場之外。在這種情況下,槓桿行爲可能會產生比較嚴重的反競爭效果
(當然,由於平臺的“二重性”,這對於消費者福利的影響是不確定的)。而如果兩個市場都已經比較成熟,都有較強的在位企業,情況可能就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槓桿傳導就會產生很好的“鯰魚效應”,促進兩個市場之間的競爭。事實上,在平臺經濟條件下,市場的進入門檻會變得比較高,因此新生的競爭者很難對在位者構成挑戰。而這種不同市場上的在位者的跨界競爭,其實已經成爲了促進市場競爭的最有效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看到的“送飯的做約車,約車的做送飯”的所謂“競爭亂象”,其實是有利於市場、有利於消費者的。
再看多歸屬的影響。2010年發表在《產業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上的一篇文章曾經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探討。這篇論文所考慮的槓桿傳導手段是搭售,根據這篇論文,如果消費者可以同時使用多個平臺,那麼平臺企業的搭售進行槓桿傳導,其實會提升消費者的福利;而如果消費者只能使用一個平臺,那麼這就會降低消費者的福利。雖然這個結論是基於十分嚴格的數學推導給出的,但其含義卻比較直觀。以我們熟悉的網約車大戰爲例,美團、攜程、高德這些企業原來都不做網約車業務。在進軍網約車市場時,它們都依託了在原有市場的優勢,將網約車業務和原有業務進行了捆綁。這樣的結果是什麼呢?就是給消費者帶來了更爲多樣化的消費場景選擇。例如,消費者需要同時考慮美食消費選擇和用車服務時,就可以選擇美團的約車,而消費者在選擇從賓館到機場的用車時,就可以考慮用攜程的約車。所有這些場景的切換,他們只需要在同一個手機上完成,幾乎不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從這個角度上講,各巨頭的槓桿傳導行爲其實是爲消費者帶來了福利的增進。但如果我們只允許消費者選擇一種網約車,那麼綜合考慮到槓桿傳導產生的各種負面影響,它給消費者帶來的總體影響就更可能是負面的。
總而言之,槓桿傳導作爲企業的一種競爭策略,既不像芝加哥學者想象的那麼好,也沒有像另一些學者說得那麼糟。它的後果,需要結合具體的條件進行具體分析。在平臺經濟條件下,競爭有了很多新的特徵。在分析涉及槓桿傳導的反壟斷問題時,我們必須要重點考察跨邊網絡外部性、多歸屬等因素的影響,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對這一問題的影響給出公正、客觀的評價。
查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