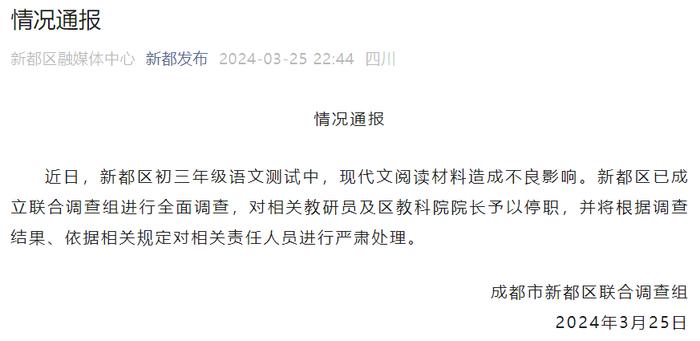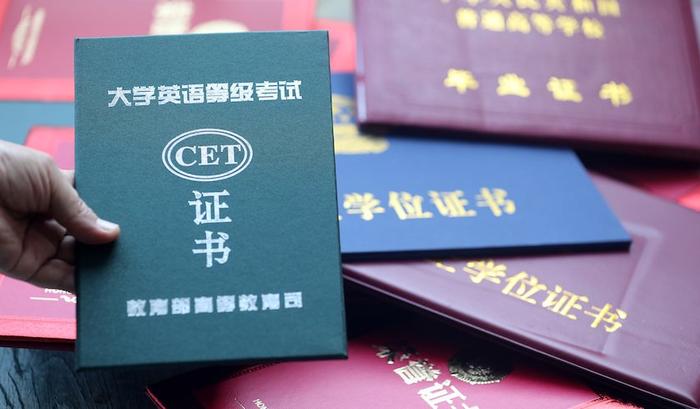二孩變三孩?執筆畫家揭祕語文教材封面背後的故事
原標題:二孩變三孩?執筆畫家揭祕語文教材封面背後的故事
“統編教材的編寫團隊和專家們頗費心思,經大家反覆研究討論,最終議定選擇風箏、糖葫蘆、皮影、布老虎、泥塑、端午、臉譜、對聯、圍棋、剪紙、國畫寫生、賞宮燈這12種題材爲主題,對應小學的12冊教材。”
新京報記者 馮琪
二孩變三孩?課本封面媽媽也不打扮了?爸爸掙錢去了?……新學期以來,小學生統編語文教材封面引起網友們熱議。近日,教材出版方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教社)對這一“民間解讀”進行澄清:五年級上冊封面中的人物實爲“小哥哥、小姐姐”,而非讀者認爲的“爸爸、媽媽”。
同時,這套教材封面背後的執筆者也引起大家的好奇和關注。2016年統編版義務教育教科書小學《語文》12冊教材封面均由著名繪本畫家、動畫導演景紹宗來繪製。他採用了傳統的手繪水彩的表現手法,分別選擇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與孩子貼近的題材爲表現點,包括風箏、糖葫蘆、皮影、布老虎等12種題材。

▲國家統編版小學語文教材全12冊封面。受訪者供圖
景紹宗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出生於典型的民俗世家。北京天壇旁邊有條衚衕,景紹宗在這裏出生和成長。他的曾祖父是京城民間花會四大前引之一景祿;爺爺是位京劇老生;父親熱衷國畫……從小的民俗浸潤與藝術滋養,使景紹宗自小就對老一輩人流傳下來的藝術非常着迷。
記者瞭解到,景紹宗初中開始在雜誌上發表漫畫,後來專注於動畫與繪本領域的創作,繪本代表作有《景紹宗繪童謠》《城裏來了一條龍》《飛吧!爸爸!!》《梅里的雪山怪獸》等,榮獲各類獎項及國內外展出;還曾繪製中國郵政《兒童遊戲》(系列)特種紀念郵票;並與動畫團隊完成了第一部原創漫畫的“動畫化”,逐漸形成從原創繪本到動畫的創作模式。
統編語文教材封面插圖是如何出爐的?背後融入了哪些設計和巧思?景紹宗的童年是什麼樣子、對他的創作產生了哪些影響?新京報記者對話著名繪本畫家景紹宗,揭祕教材封面背後的故事。

▲國家統編版小學語文教材封面插圖執筆畫家景紹宗。受訪者供圖
━━━━━
談熱點:語文書以更親民的方式走進熱點
新京報:看到網友們對教材封面“二孩變三孩”的調侃,第一反應是什麼?
景紹宗:最近大家就這個話題一起調皮了一下,身邊好多家長朋友們也參與其中,我和家人也覺得甚是歡樂。
一般來講開學季,家長們就進入了帶娃學習的焦慮期,但今年在“雙減”政策的影響下,我們欣喜地發現問題在逐步緩解,家長、學校更重視校內課本知識的學習,學習重點回到了教材,教材封面也自然而然進入了家長、老師的視野。於是,教材封面貼近生活的溫馨家庭畫面引發了全民“再創作”,圍繞着爸爸、媽媽、娃,二孩、三孩歡脫展開,這熱情的再創作背後正是我們對當下美滿家庭、和諧社會、幸福生活的關注、認同與美好追求。
作爲封面創作者,我感覺很有意思,也很有意義,語文書以更親民的方式再次走進了熱點。作爲孩子的父母,我和愛人也希望,並且準備努力生個二孩(笑)。
新京報:是什麼機緣開始畫教材封面的?
景紹宗:人教社的張蓓老師和李宏慶老師代表社裏,邀請我爲全國小朋友創作統編版小學《語文》教材的封面,在和兩位老師見面的交流中,我們彼此的創作理念十分契合。之後我們一起參觀了人教社的百年教科書陳列館,每一本封面都精緻美麗,令我大開眼界,我尤其注意到自己小時候用過的教材,那真是難忘美好的回憶。在回去的路上我思緒萬千,想起童年最好的朋友、小學的同桌、時而追打時而手拉手的弟弟和姐姐還有一本本用掛曆包書皮的課本、下課衝進小賣部一起買來的“雙棒兒”、衚衕裏玩彈球時的吵吵嚷嚷,那個沒有負擔、既簡單又快樂的童年時光……我欣然接受了這份邀請,這是一份爲全國小朋友獻上的童年禮物。
新京報:繪製教材封面和繪製其他作品相比,有什麼特殊考慮?
景紹宗:這份工作比我以往的工作更艱鉅且有挑戰性,據社裏介紹,在我參與這份工作之前,教材已編寫近4年時間,其間不斷修改、調整、甚至推翻,經由國家相關部門、各領域專家層層審覈把關,每一個字、每一個詞都反覆推敲、打磨。封面設計也同樣會經歷這般“千錘百煉”,但想到這是我們的孩子童年學習朝夕相伴的書本,點滴間滲透影響到孩子的民族自信、文化審美,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
談封面設計:將傳統文化融入童年的生活與遊戲
新京報:各學期的語文封面主題是怎麼選定的?主要考慮到哪些因素?
景紹宗:統編教材的編寫團隊和專家們頗費心思,經大家反覆研究討論,最終議定選擇風箏、糖葫蘆、皮影、布老虎、泥塑、端午、臉譜、對聯、圍棋、剪紙、國畫寫生、賞宮燈這12種題材爲主題,對應小學的12冊教材。
在決定主題後,如何與孩子們的快樂童年緊密貼切,將傳統文化自然地融入其中,便成了首要考慮的問題。我決定嘗試將其融入童年的生活與遊戲之中,再現童年時光的美好場景,讓每一幅畫面都有情節,每一個情節充滿情懷,每一份情懷背後都有獨屬於每一位讀者的童年往事。於是設計了孩子們一起跑着、跳着、你追我趕地放風箏;孩子們品嚐着糖葫蘆的美味甚至也給小雪人來一根;孩子們在廟會比着誰戴的老虎帽更好看;孩子們一起泥塑可愛的小動物、爺爺爲孩子畫張“孫悟空”的小臉譜……畫面重現這幸福的童年時光,成人也會沉浸於這美好的回憶。
新京報:這些教材封面背後藏着哪些細節和設計巧思?
景紹宗:決定內容後,就開始考慮畫面設計。比如每個年紀的孩子要符合同年齡層兒童的特點,每個年級的上下冊都對應着使用時的季節。在創作時,我們極力展現遊戲的過程而不是結果,比如三年級上冊,將泥塑中揉泥、塑形、上色幾個泥塑步驟同時安排在一個畫面中,近景再放置孩子們製作的各種泥塑小動物,讓畫面既有情景又溫暖安靜。四年級上冊的京劇臉譜,沒有表現舞臺上的表演畫面,而是安排了表演前勾臉的片段,爲孩子勾臉的是一位長者爺爺,隱含着國粹京劇在新一代中的傳承。三年級下冊的包糉子,是兩個孩子在奶奶的指導下包糉子,包含了家庭、秉持傳統、勤勞這幾個元素,這些也是我們傳統文化中十分重視和弘揚的內容。
決定設計後要爲畫面思考細節,如畫面中添加了小動物會讓畫面更活潑有趣,添加的小道具讓畫面更有情景感,在人物之間的目光、動作增加了互動使畫面更生動等等。在色彩上我們儘量選用飽和度高的顏色,來體現童年的單純和明快,凸顯孩子活躍的童年天性和天真爛漫的世界。
新京報:封面作品經歷了怎樣的修改過程?
景紹宗:在一次次反覆嘗試、討論、打磨中,作品逐漸成形,在每一冊封面創作中,都歷經了線稿草圖、色稿草圖、搭配設計好的封面版式,與教材編寫團隊一起討論每冊畫面的表現角度以及畫面內容細節。在審查環節,會聽取審查委員、各專業領域專家的意見和全國百名特級教師的建議,還會在全國一些地區試教試用,徵詢孩子們對插圖的想法。接受意見後,再次調整內容、調整構圖,之後是線稿正稿、色稿正稿,直至最終的政府相關部門審查,每一個環節均有數遍乃至十幾遍的修改調整,甚至推翻重畫。最終以集體智慧爲大家呈現出來這套與傳統文化、傳統情感結合,畫面溫暖童真童趣的封面作品。

▲教材封面線稿排版測試。受訪者供圖
━━━━━
談個人經歷:被曾祖父傳奇故事吸引的童年
新京報:你繪製了很多童趣、懷舊題材的作品,這與你個人童年體驗有關聯嗎?
景紹宗:在北京天壇的旁邊有條衚衕,我在那條衚衕裏出生和成長。家裏有個小小的院子,被我父親種滿了花花草草,還經常養些金魚、小鳥、蟈蟈、小烏龜,很愜意生活的一個小院兒。院外有棵駝背的大柳樹,映着不經調和的藍顏料直接刷下來的天空,柳風總是特別溫柔,樹上住着小螞蟻、天牛、蟬,還常有一些小鳥來樹上覓食。衚衕裏的孩子們都在大柳樹的老脊背上跳上跳下,沒有目的,只是爲了跳而跳,爲了笑而笑,我想這纔是童年。
新京報:爲什麼會對傳統文化藝術如此着迷?
景紹宗:我的曾祖父是民間“花會”的四大前引之一,叫景祿,民間稱爲“會頭”。逢年過節的廟會或是香會法會,爺爺家院外都會聚集來自天南海北的傳統藝人,大家在院外的衚衕牆上貼上大紅帖,上面寫着自己是哪路英雄,來拜見“會頭”。“出會”時場面甚大,四挑八籠,八面巨號,金黃的“門旗”迎風而起,上繡“會頭”姓名,門旗下“會頭” 不怒自威,隊伍走起來半條街長,慕名而來看熱鬧的人、街坊鄰居、經過的行人無不立足圍觀。他們遊走於金頂妙峯山這樣的場所進香演藝,什麼雲車、五虎棍、霸王鞭,現在都是難得一見的傳統演藝了。我小時候每次到爺爺家,最愛問的就是他們那些故事,爺爺講的故事總是亦真亦假,充滿着傳奇色彩,但童年的我相信,現在的我也願意相信,因爲“故事”正是對生活的憧憬、熱情,和美好的期望。
新京報:在當下藝術創作環境中如何繪製出讓孩子喜歡的作品?
景紹宗:我一直從事繪本和動畫的創作,在剛從業時,國內動畫行業正處於加工片大熱的時期,繪本也大多爲國外引進,在這種大背景下國內原創力量非常薄弱,生存也非常艱難。我們的民族文化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這是民族的靈魂,只要沉下心,肯學肯做,國內的原創力一定能做出國際一流水準的作品,乃至超越現有一流,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文化自信。
繪本是爲孩子們創作,在故事方面,要創作出孩子們真心喜歡的作品,就要融入他們的生活,和他們交流,一邊和孩子玩一邊進行創作,多爲孩子們講述,多觀察他們的反應,其實每一個大人心裏都偷偷藏着一個孩子,這樣單純的小美好,也會讓每個成人開心快樂。作爲一名創作人,以與時俱進的手法或新媒介來呈現我們的文化,也是對文化的熱愛與堅守。

▲景紹宗繪製《兒童遊戲》系列郵票。受訪者供圖
━━━━━
作者簡介
景紹宗,動畫導演,繪本畫家;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北京文藝家協會會員。創辦神奇一天國際傳媒(北京)有限公司 、清泉小魚國際藝術傳媒;2016統編版義務教育教科書小學《語文》教材封面畫家,中國郵政《兒童遊戲》(系列)特種紀念郵票畫家。原創系列繪本有《景紹宗繪童謠》《布老虎》《父親》《母親》《梅里的雪山怪獸》《城裏來了一條龍》《飛吧!爸爸!!》等,多次獲國內外獎項及國家廣電總局政府扶持。從業動畫20餘年,導演參與多部央視及國外重要動畫作品,目前擔任導演,帶領團隊製作其原創繪本改編的動畫電影《龍屋》及劇集動畫《城裏來了一條龍》。
微博熱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