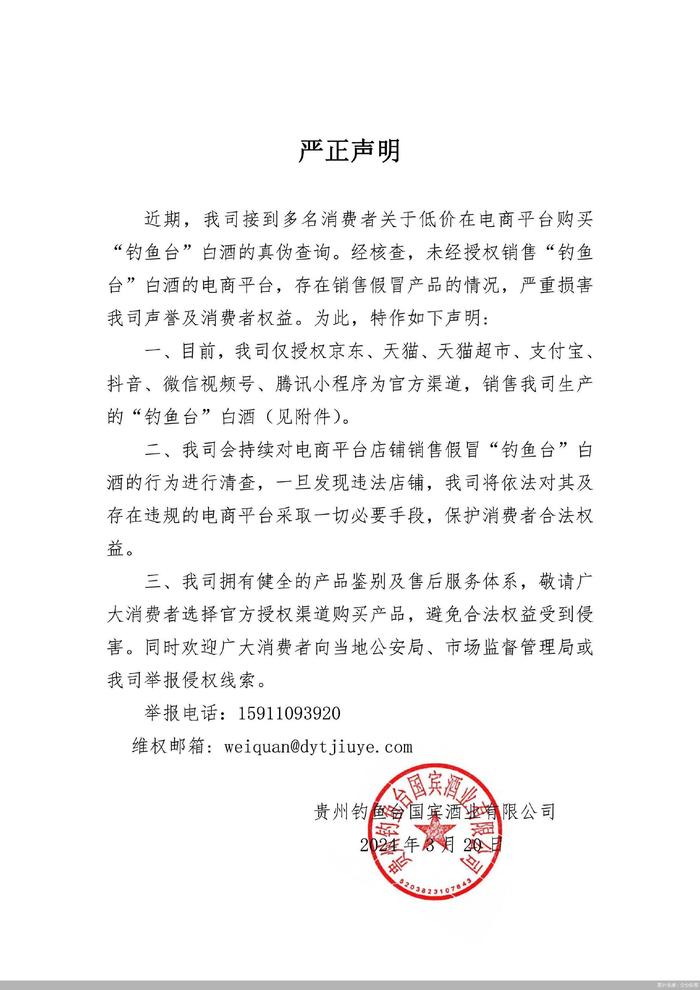戰報消失,GMV不死
 雙十一期間買了大量預售商品,卻忘記支付尾款,咋辦?周旭亮解讀
雙十一期間買了大量預售商品,卻忘記支付尾款,咋辦?周旭亮解讀

歡迎關注“新浪科技”的微信訂閱號:techsina
文/金璵璠
來源/開菠蘿財經(ID:kaiboluocaijing)
2021年雙11,不再比拼GMV數字,一反常態。
在電商平臺、在直播間,GMV都指商品交易總額,雖然不等於實際交易額,但在歷年大促中都是穩居C位的指標。每個參與方都想拿到一串漂亮的數字,因爲它是外界衡量電子商務平臺、品牌商家、帶貨主播競爭力最直觀的數據。
GMV的統計口徑是用戶下單金額,即除去真實成交額,還包含未付款訂單金額(指下單但未付款)、退貨訂單金額和刷單金額。多位電商行業人士和商家向開菠蘿財經表示,後三個部分都有“注水”的空間。
他們一致認爲,從傳統電商時代過渡到直播電商的新世界,GMV的統計口徑再次被打亂,注水空間有增無減。頭部主播的戰報裏,更是曾出現過至少三種GMV,引導GMV、GMV(下單GMV)、支付GMV。
但與此同時,GMV的參與方、受益方也在各自進化注水GMV的方式,手法從野蠻走向“精細”。商家從“發空單”到“模擬”真實成交,主播甚至只需要選幾款不愁賣的數碼產品、高客單價的珠寶等,就能輕鬆拉高GMV。
今年雙11,各大平臺不再急着公佈持續更新的GMV數字,各式戰報也不再霸屏,難道平臺、商家、主播終於都放下了GMV的包袱?
不止一位從業者的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行業內不少人嘴上說着“切莫把GMV當真”,可那些能做高GMV的公司,在雙11大促期間依然業務繁忙。
刷GMV,從野蠻到“精細”
“在行業裏,真實成交額比例有多小、水分有多大,可以充分發揮想象力。”某第三方數據公司負責人表示。業內公認的公式是,GMV=真實成交額+未付款訂單金額+退貨訂單金額+刷單金額。刷單,一直是給GMV數據人爲注水的方式之首。
電商時代,以品牌商家的自發刷單爲主,刷的是銷量,目的是提高店鋪、商品的搜索權重。
直播電商流行以來,“注水”的執行者增加了。一方主力是商家,爲了做爆款、發戰報,即便要按照一定比例付佣金給主播和平臺,刷單的動力也絲毫不減。另一方即主播團隊,受坑位費、佣金、行業競爭影響,做高直播間GMV的動力一直很強。
伴隨平臺監管力度加強、行業發展,兩方的刷單方式也一直在進化中。
作爲資深電商從業者,趙復曾經歷過“跑到某電商平臺總部,一手給現金,對方一手改銷量”的時代,彼時還需要平臺人員操作。
後來,他所在的團隊發現了某電商平臺批發系統中“改銷量”的“漏洞”。
“一款商品的價格是198元,我們設置成一折價格,19.8元,找人直接拍1000件,GMV成了19800元,然後發個假物流,讓對方點‘確認收貨’,這款商品的銷量就直接多了1000件。”相當於用低成本刷銷量。
當然,平臺不會因爲這樣增加的銷量給店鋪額外的流量,但商家還是能達到提高轉化率的目的。“因爲消費者點進鏈接一看,這款商品銷量幾千上萬件,下單動力會變強。轉化率提高了,相應的,獲得的流量和銷量都會有所提升。”趙復說道。
目前,趙覆在多個電商平臺、短視頻平臺同時開店。他透露,A平臺的店鋪會拿出1/3-1/2的利潤拿來刷單,B平臺和C平臺要拿出70%的利潤刷單。“這幾個平臺的刷單成本不同,同樣是客單價200元左右的商品,A平臺的成本最高,30元一單,C平臺比較低,6元一單。”
趙復的店鋪刷單,找的是刷數據團隊。MCN機構從業者李尋稱,從秀場直播時代開始,市場就生長出了大量刷單團隊,當電商盛行、直播帶貨踩上風口,這些團隊的業務範圍也覆蓋了電商刷單和直播間刷單。
來到直播電商時代,刷GMV的參與方變多了,只看近兩年雙11,手法也從野蠻走向了“精細”。
前電商從業者常波總結,商家一般刷的是“下單且付款”的部分,可有些主播,爲了提高坑位費,要的只是當場直播一個創紀錄的GMV數字,刷單“手法”就沒那麼地道了。
去年雙11期間,某護膚品品牌創始人武術哥本想找網紅直播帶貨衝一沖銷量,選定了一位1600萬粉絲、自稱曾創下6000萬帶貨記錄的抖音網紅,結果那場直播,連同三十多個商家,集體遭遇了刷單。
武術哥當時對開菠蘿財經形容,這個主播團隊的手法,不但不地道,而且荒謬。
“一過凌晨12點,在直播間購買商品的用戶,就紛紛發起了退單。”最終,武術哥的商品退單率高達97%,當晚成交額超過5萬,實際成交額只有千元左右。武術哥和其他商家覈對後臺發現,很多訂單的地址是編造的,買家名字也很奇怪,比如“圖片”。
一場直播下來,主播團隊收穫了高GMV數字,可包括武術哥在內的三十多個品牌方,備好的貨沒發出去,錢還全部打了水漂。在開播前,這些品牌方已經一併將坑位費100%全款打入了主辦方賬戶。
武術哥遭遇的是一場“單方面刷單”,同時,去年雙11期間,市面上還流行着一種“默契刷單”。許欣就“操作”過不少,以假髮貨、發空單爲主。
她是一名兼職刷單人員,日常在QQ等渠道接單,每到雙11等大促期間,她所在的一些叫“補單”、“退款單”、“派單”的羣聊,就尤爲忙碌。“618、雙11、雙12,刷單需求都會猛增,刷手忙不過來。”

需要強調的是,刷單屬於違法行爲,且被各大電商平臺嚴打。因此,這些刷單人員手法也較爲隱蔽。
許欣介紹,操作流程是,羣主收到佣金後,會把商品鏈接推到刷單羣裏,安排刷手按要求購買,品牌商家會寄送給刷手“信封快遞”或“空箱子快遞”,快遞內會裝皮筋、卡片等不值錢的物件,當刷手確認收貨,就算刷單完成。品牌商家和主播團隊對整個流程心知肚明,由於假包裹很容易被快遞方識別,因此還需要快遞方配合,拉快遞公司“入夥”。
今年以來,品牌方不再願意與“發空單”的主播合作,於是,進化出了接近真實成交的刷單方式。
新消費品牌負責人馮聖向開菠蘿財經透露,“現在一些刷單公司乾得很‘專業’,讓品牌方都識別不出來,還以爲是真實用戶。”
據其透露,這類型的刷單需求一般是通過第三方社交軟件或是境外軟件對接。手法是,真實下單、真實成交,收到貨後,低價轉賣給微商、社區團購、拼多多等下沉渠道。
有動力如此刷單的主播,一般是因爲與商家簽了保底協議,若帶貨成績達不到保證的銷售額,需要按比例給商家退還費用,但若照此方式刷單,反而是賺的。
這種刷單方式的成本較高,一方面取決於商品屬性,因爲需要再次流轉,“快消品的費用就低一些,難變現的小家電就高一些”,馮聖說,比如一單速食麪的刷單費用是10元左右,屬於較低的;另一方面,還取決於交易平臺,因爲這種方式操作不當很容易被平臺識別,治理力度大的平臺,成本就高。“淘系成本最高,抖音和快手相對便宜。”他表示,“重複下單、異常下單的地址會被平臺加入問題地址庫。”
說到底,被動刷單方和主動刷單方,就像貓捉老鼠的遊戲。當貓要的是GMV時,可以暫且忽視刷單的老鼠,當貓進化後,就需要老鼠貢獻更加真實的GMV。
GMV“三寶”:iPhone、珠寶、“優惠券”
讓GMV失真的,不只是刷單金額。“未支付訂單金額”、“退貨訂單金額”,也有一定的操作空間。
在大促期間,因爲顧客沒搞清楚優惠機制或系統故障,導致的重複下單等,都增加了未付款GMV。而當“7天無理由退貨”成爲主流,主播善用“不想要就隨時退款”等誘導話術,則無形中拉高了退貨GMV。
資深電商從業者田敬透露,在實際商品後臺,訂單分爲“已付款”、“已失效”、“已結算”三種狀態。“已失效”一般可以理解爲“加購未支付”;“已付款”則可以理解爲“加購且支付,但未確認收貨”,這種狀態下存在退單可能(先不區分僅退款和退貨退款的差異);商家真正到手的金額是“已結算”狀態加起來的“結算金額”。
其以某位主播近期帶貨的一款商品的後臺數據爲例,“已付款”、“已結算”、“已失效”三部分的佔比是6:2:2。商家是按照“已結算”狀態給主播結算佣金,平臺再從主播的佣金裏抽取技術服務費。截至到目前,這款商品的真實成交GMV佔比不到20%,剩下八成GMV全是水分。
一位數據平臺負責人判斷,直播間的退貨率要高於電商平臺整體的數據,在不考慮人爲注水的情況下,直播間退貨訂單的比例在20%左右,同時還要看產品的單價,單價越低、退貨率越低,單價越高、對GMV貢獻越大的SKU,退貨率越高。
另一位電商平臺負責人邊旭則認爲退貨比例更高,50%-80%的退貨率都是正常的,因爲即便是標品也存在大量衝動式消費。
“去年雙11,主播爲了讓商家放心掏錢,不得不籤保底協議,否則不合作,保底壓力下,刷單需求自然多,今年雙11,流行的是兩種方式,坑位費加佣金,或是純佣金,選用何種方式取決於主播的話語權。”馮聖表示,不過,主播依然有做高GMV的方式,比較主流的就是在選品上做文章。
不止一位從業者提到,蘋果的數碼產品、珠寶等,是最佳的拉高GMV商品,且無需刷單。

來源 / pexels
第一類,蘋果產品,真實銷售,主播不圖掙錢,就是爲了拉高GMV及直播間人氣。“大量主播自己貼錢賣蘋果產品,其實非但不會虧,效果反而比投流還要好。”田敬表示。
第二類,珠寶。“這個類目極其特殊,就算是‘良心商家’自己直播,退貨率也高達80-90%。”
田敬表示,那麼珠寶商家“留”給主播團隊的操作空間就比較大,或是商家主動配合,做高這場GMV,或是找團隊下單、再退款即可。不過退單有退單的操守,有操守的退單是在直播次日商家發貨前操作退款,這樣商家只損失坑位費,否則還損失物流費。
“很多高客單價的護膚品,比如天氣丹,和珠寶同理。”田敬提到,抖音、快手上有主播單場GMV做到2.5億,其中1個億是賣天氣丹,四成訂單在直播結束後迅速被退掉。
最後,到了統計環節,交易平臺和第三方數據平臺,也會“不小心”抬高GMV。
比如,平臺方每逢大促必有的“跨店滿減”,就拉高了GMV。
一方面,刺激了消費者購買,另一方面是,統計口徑本身就含有水分。“200-30”滿減之下,用戶真實成交額是170元,但平臺還是以200元計GMV。
而“拍立減”、“第二件0元”等優惠機制,也會“影響”第三方數據平臺的抓取邏輯,據介紹,其統計出的GMV都是以原價計算。
田敬對開菠蘿財經分析,第三方數據平臺抓的是“直播前後的銷量差”,再與提前抓取的頁面價格相乘,得出預估GMV。實際到了雙11當天,商品價格可能會自動優惠爲頁面價格的五折,但第三方數據平臺仍然按原價統計,得出的GMV幾乎是翻倍虛高。
在大促期間,第三方數據平臺的GMV會更加失真。他提到,比如某商品鏈接在某一天的相近時段被兩位主播帶貨,第三方數據平臺監測到的銷量差,其實是兩位主播累計的戰績,但是這個總數會被分別計入各自的GMV戰績。“當然這種情況在擁有專屬鏈接的主播身上是不存在的。”
GMV進化史,從“混亂”到“被淡化”?
“GMV本身就很水。”常波表示。
GMV是電商平臺的發明。他表示,各電商平臺也是在行業逐漸成熟、遊戲規則透明,才明確了一致的GMV統計口徑。這一點在頭部電商平臺的財報中都能找到對應的解釋,即平臺上所有已確認的商品與服務訂單的總值,無論商品是實際出售、交付還是退貨。
來到直播帶貨的新世界,GMV統計口徑再次陷入混亂。
邊旭稱,很長一段時間,部分直播帶貨平臺都是把加購(加到購物車的商品金額)也算進GMV,不過現在大部分都是以下單金額計算GMV 。
頭部主播的戰報裏,更是曾出現過至少三種GMV,引導GMV、GMV(下單GMV)、支付GMV。
2019年雙11期間,薇婭和李佳琦直播間就曾公佈過引導GMV。財經作家吳曉波的直播首秀公佈的也是引導GMV(5200萬),舉個例子,其在直播間銷售的是某品牌500元的櫥櫃券,但引導GMV是按照櫥櫃的實際售價20000元來計算。
而後,薇婭、李佳琦等主流主播,所講的GMV進化爲下單GMV,這也是電商行業通行的口徑。

但羅永浩是個特例。按照他本人的說法,他直播間的官方戰報是按照真實的支付金額計算GMV,即支付GMV,是指從下單GMV中刨去“未付款”部分。
不斷被刷新的GMV神話講到今年雙11,彷彿戛然而止了。朋友圈、網絡平臺上的各式戰報明顯變少了,主流平臺也安靜了許多。
雙11當天,到了下午,京東才更新GMV(京東11.11全球熱愛季累計下單金額超過3114億元),到夜裏24點,首次取消數字大屏的阿里終於低調公佈了GMV(雙11總交易額5403億)。
神奇的GMV從口徑不一到逐漸被“淡化”,是因爲平臺、商家、主播,終於都放下了GMV這個包袱?
先看平臺方。開菠蘿CEO王冉表示,作爲大促的發起方,平臺過去實時披露GMV,是擔心外界不相信雙11創造的鉅額GMV,爲的是吸引更多參與方入場。阿里最高調宣傳GMV的時期,一定是平臺處於強勢地位,自家GMV的增長指代了雙11大盤的增長。
到了今年,平臺從一家獨大到百花齊放,GMV勢必會被分流,單一平臺的增速很難再持續創新高。“現在外界已經有了共識,薇婭、李佳琦等頭部主播的GMV貢獻過於突出,平臺再高調宣傳GMV就很尷尬。”王冉稱。
站在商家和主播的角度看,看似大家對戰報的積極性沒去年雙11高了,但不止一位從業者認爲,是行業不得不理性面對GMV數字了。
常波表示,雙11對GMV的拉動作用在減弱,因爲日常的促銷、直播間的促銷,消費者雙11囤貨的理由變少了,品牌和主播的雙11戰報數據就沒那麼突出了。同時邊旭認爲,“監管加強,不允許虛假宣傳,去了水分的真實GMV一披露,誰在裸泳一目瞭然,換言之,動輒GMV破億的品牌沒那麼多,真正能出戰報的商家寥寥無幾。”
“平臺、商家、主播,對GMV的態度一直都沒有變,永遠是又愛又恨。”常波表示,只是經過這幾年的科普,不再唯GMV論了。
事實上,行業內不少人嘴上說的“切莫當真”,GMV不代表什麼,但只要還沒有找到下一個衡量電子商務平臺、品牌商家、帶貨主播競爭力最直觀的數據維度,GMV都不會消失,那些能做高GMV的公司依然有市場。
*題圖來源於視覺中國。應受訪者要求,文中許欣、邊旭、田敬、常波、李尋、馮聖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