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擠破頭”擁有教師編制,他們後悔了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近年來,我國教師職業吸引力明顯增強,報考師範專業,考取教師資格證和參加教師編制考試的人數大漲也頻頻成爲新聞。但同時,也有人已經在教師崗位了,卻想要或已經離開。想象與現實的差距,既來自一些人被潮流裹挾的認識誤區,也來自教師工作內容的時代變化。
一位採訪對象總結的一個悖論是,“人們越認爲老師很輕鬆,就越傾向給老師佈置更多社會任務。殊不知,很多老師已經被這些附加任務壓垮了。”她有時會感到自己有苦難言,“我們抱怨或者傾訴工作困難時,社會輿論甚至家人還往往認爲,是我們太嬌氣、喫不了苦。”
想象與現實
從上大學時,考上教師編制,就是趙恩的夢想。趙恩出生於1998年,生活在南方一個省會城市,她本科讀的是師範,專業是小學語文教育。對她來說,這個選擇非常自然,毫無懸念,趙恩的爸爸和姑姑都是初中老師,他們工作中呈現出的狀態清閒輕鬆。因此,趙恩從小就在心裏埋下了一顆未來當老師的種子。

《小別離》劇照
上大學後,趙恩本打算先考研,但後來發現,周圍的同學有人從大一就開始準備考編了,也有親戚勸她,教師編制越來越少,讀完研再考編,難度更大,趙恩於是放棄考研,本科畢業就直接開始考編了。對她的這個決定,父母是支持的,甚至承諾,只要考編成功,趙恩考到哪裏,就在哪裏爲她買房。
2021年4月底,也就是大四下學期,趙恩第一次正式參加所在省份的教師編制考試。根據趙恩的觀察,同年級100多人,除了三四個工作已有着落的,剩下的全都參加了這場考試。其中音樂美術等學科,錄取個比例大約是幾千人中錄取個位數。
趙恩考的是語文老師,錄取比例高一些,但她依然落榜了。因此,2021年9月,趙恩先應聘了當地一所小學,當語文代課老師,並根據學校慣例,成爲了班主任。在這所學校,趙恩的年薪大概只有九萬,但在編老師有獎金,年薪可以達到二十萬。這堅定了趙恩繼續考編的決心,但另一方面,她發現自己可能並不喜歡教師這份工作。

教師資格證考試前,考生們在考場外複習(圖 | 視覺中國)
趙恩讀的雖然是師範,大學期間也參加過實習,但實際上,她當時只需要在課堂旁聽,批批作業就可以了,並不需要直接接觸孩子和家長,對教師工作的理解不多。正式工作後,趙恩發現,光是每天在2-3節課上保持“亢奮”狀態,已經是巨大的消耗了。另一些繁瑣的工作也讓她感到疲倦,比如作爲班主任安排班級活動、班會課,對接當地社區、醫院或者消防局、交通局等政府機構,做疫情排查,做核酸檢測志願者。她記得,自己有一次是凌晨兩點被校領導叫起來,去做志願者的。
趙恩印象很深的另一件事是,有一次學校門口一位家長騎電動車沒戴頭盔,被監控攝像頭拍下來,刊登在了當地媒體上。學校開會時公佈了照片,並批評了該名家長的孩子所在班級的班主任,理由是,班主任沒有做好家長安全防範工作。此後,趙恩每天都會在家長的微信羣中強調,請大家遵守交通秩序,在公共場合舉止文明。
這些繁重的社會任務,讓趙恩感覺身心疲憊,這跟她選擇做教師的初衷背道而馳。趙恩把自己歸結爲“典型的當代年輕人”之一,她說自己從小生活在富裕穩定的家庭,不用考慮存款、買車買房,因此生性散淡,安於現狀,不愛動腦子,也不愛社交。她坦誠地說,自己當老師,只是因爲想找一份舒適區內的清閒工作,工資能養活自己就行。但如今,因爲讀師範和考編的人數激增,競爭甚至比其他行業更大。

《西小河的夏天》劇照
趙恩說,自己能感覺到,一直留在教師這個行業,持續考編,生活會變成一根越捆越緊的繩子困住她。但今年4月中旬的教師編制考試,趙恩還是報名了,因爲她不知道,不做老師的話,自己能幹什麼。
“三成教學任務,七成社會任務”
相比趙恩,張小徽對當老師和放棄編制的選擇,認知都更清晰,但也更堅決。和趙恩一樣,同爲90後的張小徽也是在父母的建議下報考師範的。
張小徽曾對教書懷有過極大的熱情。大學四年,趕上了中國的教培行業發展最快時期的張小徽,一直在校外教育機構做兼職老師,後來大四,她還在學校實習了一段時間。在這些實習和兼職經歷中,張小徽教過小學、初中和高中,她喜歡在課堂上拓展一些課外知識,包括自己在大學學到的本科知識。一些學生,尤其是高中階段的學生吸收得很好,還能跟她互動,讓張小徽感覺很有成就感。

(圖 | 視覺中國)
大四考編制時,張小徽考慮到可選擇的學校地區,選擇了一所小學,成了一名主課老師,並和趙恩一樣,成了班主任。她那時心想,小學雖然不是最理想的選擇,但起碼教學難度低,工作應該相對輕鬆。
但真的工作以後,張小徽發現,“輕鬆”只是她自己的想象。採訪時,她詳細回憶了自己當老師時的日程:每天八點前就要提前到班裏迎接學生,上午上兩節課,還要批改作業,帶學生做課間操,組織和監督學生做值日、記錄出勤情況、整理和上報學生的健康情況;中午和下午,張小徽沒有教學任務,但要管理學生喫午飯,監督午休,批改作業,回覆家長信息,參加學校會議等。下午四點學校就放學了,但張小徽要連續帶幾個託管班,七點左右才能下班。她說,回到家裏,自己還要備課,回覆家長信息,經常工作到晚上十一點多才能真正休息。
就是在這樣負荷的工作強度下,入職一個月左右,張小徽就萌生了辭職的想法。一開始,她懷疑自己是剛入職不適應,但後來,她雖然逐漸適應了工作強度,但嚴重的疲勞感並沒有消除,連身體都開始變差。張小徽還觀察到,許多同行患有乳腺結節、甲狀腺結節等疾病。意識到這可能不是自己想要的未來的時候,張小徽在工作半年後,堅定地選擇了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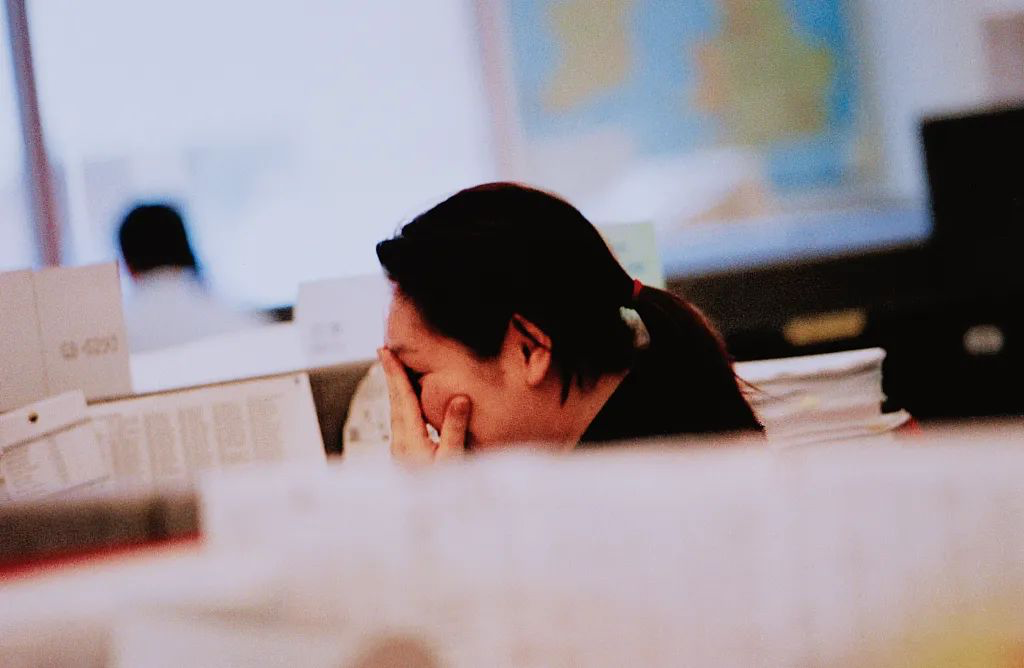
(圖 | 視覺中國)
離開之前和之後,張小徽在身邊和在網上找了數十位同行交流,囊括了不同年齡、不同學段、不同學校、不同地區的老師。張小徽說,在她交流過的老師裏,想要離職或已經離職的老師中,只有一位是高中老師,其餘的都是小學老師,以主課老師和班主任爲主。
結合自己的經歷和跟同行交流的結果,張小徽總結了小學班主任的壓力來源,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一是學校的課外活動豐富,大大增加了工作範圍,以張小徽工作的地區爲例,每所學校每學期都要舉辦不下5次大型文體活動,班主任要全程參與活動策劃、表演、宣傳、攝影,還要聯繫家長排練等,工作又多又繁瑣。
二是老師的安全責任重大。和很多學校一樣,張小徽原來工作的地區,要求老師的監管要覆蓋學生在校的所有時段,課間需要巡樓,午餐午休需要看管,禁止學生在課間追跑打鬧。
三是現在通訊工具發達,各種信息極大地侵佔了小學老師的業餘時間。張小徽說,當老師時,因爲一些家長都沒有尊重老師作息時間的概念,她每天下班後,幾乎都會收到七八個家長的信息。另外,各種工作羣消息也會全天候彈個不停。
四是和趙恩一樣,張小徽也需要對接交通安全部門、消防部門、司法部門等,並按照要求,提醒家長騎電動車戴頭盔,督促家長下載各類政務相關app,管理班上家長和孩子們的流調情況,組織學生打疫苗等。

《地球上的星星》劇照
張小徽估算了一下,她當小學主課老師和班主任時,只有三成工作是教書任務,其他七成,都是社會任務。在張小徽看來,這形成了一個悖論,“人們越認爲老師很輕鬆,就越傾向給老師佈置更多社會任務。殊不知,很多老師已經被這些附加任務壓垮了。”她有時會感到自己有苦難言,“我們抱怨或者傾訴工作困難時,社會輿論甚至家人還往往認爲,是我們太嬌氣、喫不了苦。”
家庭與人生
辭職前,張小徽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了父母,結果遭到了強烈反對,他們建議張小徽再忍耐和磨合一段時間。親戚們聽說後,也前來勸阻張小徽。但張小徽說,自己性格比較果斷,發現說服不了長輩後,就不再說服,直接辭職了。
和張小徽一樣,趙恩不想繼續考編,甚至想離職的想法也讓她的父母詫異。在同樣當老師的趙恩爸爸看來,她的一切困擾來自於,太幼稚,又不能喫苦,還追求太高,只要考編成功,這些問題都將迎刃而解,甚至能幫助她順利相親。也因此,要不要繼續考編,如今成了趙恩和父母矛盾的源頭,常常爲此爆發激烈爭吵。

《以家人之名》劇照
當了十年小學老師又辭職的王三川,跟父母倒沒有激烈矛盾,但她的離職,同樣跟父母有關。和趙恩、張小徽不一樣,王三川當的是美術老師,她說,自己10年前入職時,教師編制還不像現在這麼難考。她是在大四實習後,被學校領導挽留直接入職的。雖然10萬左右的年薪在王三川工作的上海不算高,但她喜歡美術,也喜歡孩子,學校離家還只有10分鐘步行路程,她當時覺得,自己算是找到了理想工作。
在學校裏,王三川先後擔任過學校大隊輔導員和班主任,又在身體出現嚴重報警後辭掉了相關職務,做回了單純的美術老師。此後,她身體的病痛有所緩解,但沒有完全停止,尤其是嗓子,在長期教學後,好幾年的時間裏,每節課的後半截,王三川只能服用咽喉含片或者使用咽喉噴霧緩解喉嚨腫痛。最嚴重的時候,每一次吞嚥都會撕裂般疼痛,她因此連水都不敢喝。
王三川記得,自己去就醫,剛說到自己是老師,對方就明白了她的病情,“可見有多少老師來看過一樣的病了。”正是在身體的病痛中,拿過一些市級及國家級獎項的王三川,對孩子的熱情和寵愛,一點點變成了對他們吵鬧和不可控的厭煩。
但即便如此,王三川以前也沒有想過辭職。直到2020至2021學年寒假,王三川去了海南旅遊,學習了一個月的衝浪,並漸漸迷戀上了這項水上運動。2021年的暑假,她又去了一次。再回到上海時,一想到開學,她就開始失眠。辭職的想法由此萌生。
王三川和爸爸媽媽以及學校校長表達辭職的想法後,大家都很震驚。但她父母並非不能理解她要辭職,而是不能理解她要離開上海,“尤其是我媽媽,可能因爲是家庭主婦,她的生活基本上都圍繞着我和爸爸,所以對我比較依賴,更希望能跟我生活在一起。”
但王三川沒有說出口的是,她想辭職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正是,工作以來跟父母生活得太久,距離太近了,“這當然也很幸福,還節省了生活成本。但我已經三十多歲了,我渴求獨立自由的生活,甚至早就想獨居了。”

《麪包和湯和貓咪好天氣》劇照
在海南,她認識了很多衝浪愛好者和長居在海邊的人,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狀態。正是這種自由,讓她決定即使冒着隨時會後悔的風險,仍然要辭職。王三川仔細考慮過,自己有兩個優勢,一是家庭條件不錯,沒有房貸車貸,不用擔心父母的養老問題;二是,她不準備結婚生育。
如今,王三川已經在海邊生活好幾個月了,除了衝浪,她也會擺攤,經營自己的自媒體賬號。她知道,如果有一天她後悔了,是不大可能重回編制內的,但她仍然希望,自己幾年後即使回到上海,也不會完全脫離社會和自己原本的狀態。
(趙恩、王三川、張小徽均爲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