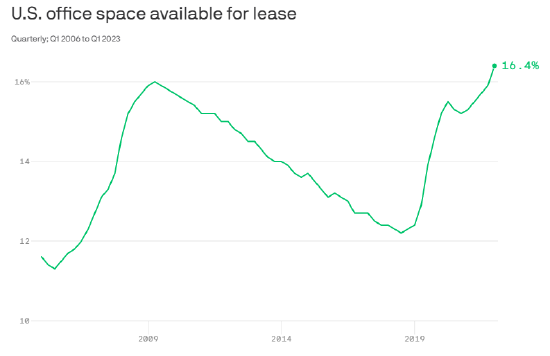睜眼工作,閉眼睡覺:我在出租屋裏居家辦公

圖片來源:圖蟲
記者 | 於浩 姜菁玲
編輯 | 文姝琪
5月6日的晚上十點,電腦上的線上會議遲遲沒有結束,這讓張翔有些煩躁。週五的夜晚、在家、身旁數米之外的PS5,種種因素看起來都和工作毫無關係。電腦裏會議還在繼續,但張翔已忍不住胡思亂想,“這個點兒了,我爲什麼還在聊工作?”
受疫情的影響,北京如朝陽、海淀、豐臺等區都倡導起了居家辦公。張翔所在的公司也不例外,儘管已經過了兩週居家的日子,他依然無法適應這種工作與生活混在一起的節奏。
有着類似體驗的職場人還有不少。工作時間可能被無限拉長也是居家辦公被廣爲詬病的一點。但對於另一部分人而言,居家卻意味着更舒適的辦公環境和更多的個人時間。
與張翔不同,居家辦公後的曉彤顯得如魚得水。省去通勤和職場社交的時間之後,她有了更多休息的時間。獨自在家不會被瑣事打擾,讓她可以整理出大段時間用於專注於單項任務,工作效率反而有所提高。
手機、筆記本電腦以及騰訊會議等遠程辦公軟件的普及,使得工作場景早已不僅僅侷限於辦公室內。早在2020年,微軟、谷歌等科技企業已經開始推行遠程居家辦公。
2021年領英發布的《2021未來職場工作方式調研》報告顯示,57%的受訪者更傾向於混合辦公模式,願意全部時間在家工作的受訪者則佔到11%。但在疫情的非常態化狀態下,由公司坐班向遠程居家辦公模式的突然轉變,依然讓人有些猝不及防。
“我需要工作和生活被區隔開”
在張翔位於北京的出租屋裏,日常用來打遊戲、休閒的桌子就擺在牀的正前方。平時週末起牀後只需一個起身,張翔就可以坐在這張桌子前。
居家辦公的日子裏,原本桌子上的遊戲手機、手柄、iPad都被晾在一邊,辦公電腦“喧賓奪主”似的佔了主位。“睜眼辦公,閉眼睡覺”,他有些無奈地描述。
在互聯網行業做產品經理的他時常需要和其他同事溝通工作細節。遠程辦公的環境下,一個接一個的線上會議替代了原先的線下討論。翻開他的時間表,最忙的一天,從早11點到晚8點被滿滿當當地插入了各種主題的線上會議。
但即便是這樣,張翔依然覺得自己很難像在公司那樣全身心投入工作,家裏的實在誘惑太多。“我的桌子就是用來喫喝玩樂的,讓我在上面工作心裏總是會有點牴觸。”他直言,“總是想着這時候要拖拖地,那時候要洗洗衣服,要照看的事情很多。”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遠程居家辦公更加自由的工作模式是許多人所認可的未來工作方式。但現實情況是,辦公室制度已經成爲數十年來職場中最普遍的一種辦公模式,突然的轉變直接導致了員工時間、空間、心理邊界的模糊,也讓一些人產生了緊張和焦慮情緒。
溝通效率的降低是張翔不習慣遠程居家辦公的另一個原因。原本在公司只需要抱着電腦跑幾個工位就能完成的溝通現在卻只能通過辦公軟件去約時間,這讓他有些疲憊。
在採訪的當天,張翔原本需要和一位同事對接工作。兩人從早上11點開始約時間,互相問“在嗎”的對話一直持續到下午三點,才終於成功對接上,討論完主題已經是下午四點。“我開始懷念起自己可以在工位上抓到某個人當面聊天的過程,在家真的很不爽。”他說。
對於曉彤而言,居家的辦公環境並不是問題,能夠用音響隨意放音樂反而讓她工作起來更加自在。而對針對“找不到人”的緊急場景,她會選擇在項目羣裏直接@同事,“老闆在羣裏會有一些隱形的壓力。”
但她偶爾也會感到居家的日子有些枯燥,每天見到的人和環境都一樣,掛念起公司的茶水間和同事偶爾聊起的八卦。“可能你不是參與者,但是你可以旁聽,聽見很多的新鮮事兒。”曉彤說。
桌子旁的PS5和小沙發曾經是張翔的“快樂小花園”,但最近因爲需要處理工作他已經很少打開遊戲。“對我來說,現在生活跟工作完全混到了一起,我還不能接受。”
在經過一段“自閉”的時間後,張翔現在也開始主動地調節自己,區隔開工作與生活的界限。他開始在晚飯後抽出時間下樓走走,時不時拿着滑板去小區滑兩圈,給自己營造些下班的儀式感,等待着回公司辦公的通知。
同樣焦慮的管理者們
最近張翔和曉彤都感覺到,自己的上司好像和往常相比有些不一樣了。原先管理風格較鬆散的上司近期在張翔的部門裏拉起了打卡羣,要求每天10點打卡;曉彤則明顯感覺到上司開始更頻繁地在工作羣裏關心下屬,“可能是爲了讓團隊有更強的歸屬感和凝聚力”。
以往熟悉的辦公室管理模式和組織形式不再適用,取而代之的是騰訊會議和微信羣裏的“虛擬下屬”,這對揹負管理壓力的上司們來說同樣是新的挑戰。線上打卡與問候等變化尚屬合理,但在近期職場上也不乏一些爭議性的做法。
5月份,在線教育公司尚德機構(NYSE:STG)被員工爆料稱,尚德機構在員工居家辦公期間,實現了嚴格的“監控措施”:每5分鐘抓拍一次人臉,如果幾次抓拍不到,就要扣除全部績效,領導和HR也跟着扣錢,以至於“大家不敢去上廁所”。
除此之外,有網友稱,居家辦公期間,公司規定工作時間員工不得外出,並啓動了“紀委”組織對員工的GPS定位進行隨時隨地抽查;還有公司規定如果收到人力資源部發出的抽查短信,在十分鐘內未回覆,則將算作缺勤。
辦公模式驟然變化的挑戰,讓部分管理者的不安全感大大提升,他們失去了對員工的監察,無法知道員工是否認真工作。這些管理者希望盡一切手段,至少實現和在辦公室一樣,對員工的“在崗”“產出”進行控制和了解。
儘管不少人認爲該“摸魚”的人即使在辦公室也會“摸魚”,但與遠程辦公模式相比,辦公室模式至少能控制的是員工的在崗時間,管理者能夠隨時看到“在工作”的員工,也能夠更加直接快速地與員工進行溝通。
來自Gartner的一項調研數據表明,在2020年和2021年之間,用監控工具追蹤員工的大公司數量翻了一番,達到了60%。有些公司則增加會議和電子郵件的數量,用另外一種方式追蹤員工在做什麼。
“步步緊逼”式的線上監管在效果上有時反而適得其反。一位互聯網大廠員工向界面新聞吐槽,自疫情以來,自己所在的小組的彙報週期從周變成了天。“每天10點晨會,說自己的工作計劃,晚上8點總結,彙報自己的產出。”這種按日彙報的模式讓他感到窒息。
遠程辦公會是未來的工作方式嗎?
在一個理想的遠程辦公場景下,管理者與員工之間應當充滿信任,雙方尊重契約精神。管理者更加目標導向而非過程導向,可以妥善處理自己的控制慾和不安全感;員工則更加自由而自驅,實現生活與工作的平衡。
家住上海的靖雯的經歷似乎是這一新職場模式更好的落地案例。自從3月末之後,她就一直處於被封控在家的狀態。經歷過搶菜潮和循環往復的核酸檢測之後,她有種“自己的時間停滯了”的錯覺。
“一直在家所處的環境一成不變,甚至這周的菜單和上週可能都是差不多的。”這讓她產生了些許恐慌。第一個月,爲了逃避負面情緒,她又重刷了一遍甄嬛傳。在這種狀態下,工作似乎成了一種日常生活中的“救贖”。
因爲靖雯所在的創業公司主要經營線上業務,所以工作上的溝通交流一直以線上的形式進行。項目一直在向前推進,這給了靖雯一種“生活仍在繼續”的情感支撐。疫情出現後,公司也表現出極大的理解與信任,全面線上辦公的同時還發放了補貼,部門內的同事也時常通過會議軟件拉起閒聊羣,營造出大家仍在一起辦公的氛圍。
沒有了眼神和肢體動作層面的交流,線上會議難免會有一些尷尬時刻。“在騰訊會議裏面沉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她笑稱,“所以現在我們開線上會議都是放BGM的,主持人做DJ,大家都可以點歌。”
藉着這一機會,她和同事們還嘗試起了如Gather等新型虛擬會議室,辦公之餘在裏面賽車、打德州撲克。這些都在封控期間給了靖雯一些精神上的撫慰。
溝通效率的問題依然存在。儘管Gather上提供了“坐下”和“離開桌子”的狀態提示,但仍然無法讓人能第一時間找到溝通對象。因此,在靖雯所在的公司裏形成了一條默認的規則——早11點之前和晚七點之後都不去私戳別人,所有溝通都務必在這一時間內完成。
表面上看,管理者與員工能否達成工作上的信任與默契是遠程辦公的基礎,管理風格鬆散、層級制度不明顯的創業公司似乎更容易達成這一條件。而細細探究,雙方的矛盾根源其實在於公司管理模式與遠程辦公制度的不匹配。
靖雯的公司重點關注青年文化,管理層對新模式的接受程度更高;曉彤長期對接國際化客戶,因爲時差的原因部門內同事也大多習慣了靈活的工作節奏。
遠程辦公之父Jack Nilles 曾說過:我很早就意識到,技術並不是接受遠程辦公的限制因素。組織和管理的文化變革對在家辦公的接受率更重要。一個能夠適應遠程辦公的公司文化,包括但不限於更合適的溝通流程、彙報節奏、管理風格,而這些是當下突如其來迎來“遠程辦公”的許多公司需要補課的部分。
正如如電影《辦公空間》裏曾提到過的一句臺詞,人被生下來,並不是爲了待在狹小的隔間內,對着計算機屏幕坐上一天又一天的。當公司文化足夠適應遠程辦公,當下員工在遠程辦公模式下的消耗會不斷減少,到那時,遠程辦公真正的潛力或許才能真正被激發。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張翔、曉彤、靖雯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