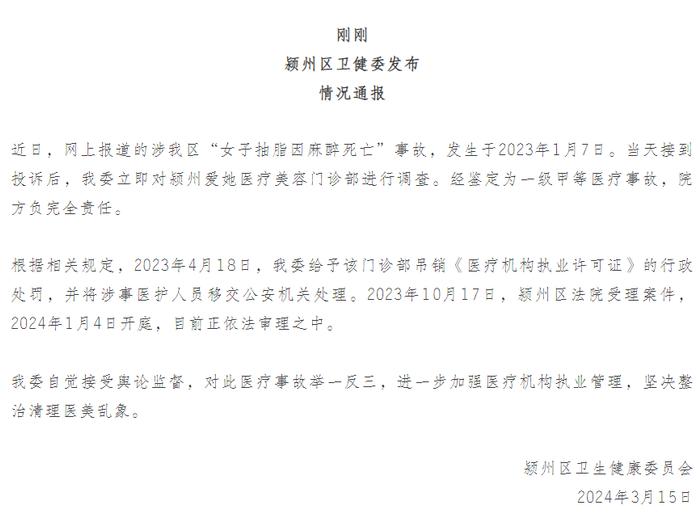我,一名外科醫生,被做了一次痔瘡手術
我,一名外科醫生,被做了一個小手術。
有朋友關心的地問起來,我都會很不好意思地說一句:「做了個痔瘡手術。」對方也會馬上哈哈一笑趕緊換個話題。
事實上,我的問題準確地說不是痔瘡,而是肛旁膿腫。簡單地說,就是菊花旁邊的長了癤子。
這個癤子肛竇腺逆行感染導致的,因此有一個小瘻管和肛管通着,時間長了反反覆覆容易形成肛瘻,要手術治療。
發病的情形是這樣的。
去年 6 月下旬,某日早晨空腹喫水果後導致腹瀉兩天,緊接着去外地參加畢業十週年同學聚會。
軍校畢業後天南海北的難得一聚,難免開懷暢飲,所有高危因素湊齊,如同集齊了龍珠最終召喚來了神龍。
次日上午在曾經大學的教室內點名時就感覺不對勁了,只敢用半個屁股着座,之後就在躺在酒店,什麼活動都無法參加。
當晚火燒火燎趕到機場欲早點返回,結果航班取消,又火燒火燎的返回酒店,第二天坐高鐵回京。
準確地說是站回來的,下面有癤子根本不敢坐啊。整個過程想起來都痛不欲生。
寫這麼詳細的原因,是反省作爲一個外科醫生,以前想當然的認爲「大瘤子纔是病,一個小癤子算啥」的錯誤認識。病不在大,部位才關鍵啊。
回來後,我馬上找到了肛腸科專家 C 醫生,行肛腸指診,俗語「爆菊」,酸爽得不要不要的。以前我也給別人做過,下手只求快速準確,忘了是否曾經溫柔對待。
檢查完畢,C 醫生乾脆地說:「肛旁膿腫,手術吧。」
我,一名外科醫生,天天把「手術」倆字掛在嘴邊,卻在聽到被手術人是自己的時候,不爭氣地腿軟了。
誰都知道,肛腸手術痛苦大、癒合慢,術後爆菊檢查換藥是經常性工作,想想就菊花一緊,虎軀一震。
再加上邊姬(作者的妻子,編者注)大個肚子,老大也不省心,我這一住院就是小一個月,家裏該玩不轉了。
於是我陪着笑臉小心地對 C 醫生說:「實在不想手術,你看能不能保守治療?」
以往聽到患者對我說這種話,我心裏總是有點不屑的,「手術明明就是最好的辦法,偏要喫藥,要麼就是不懂科學,要麼就是不信任醫生。」
當然我不會把這些表現在臉上,只會微微一笑開點藥。
C 醫生也是這麼做的,不過他開完藥還補了一句:「你這情況遲早得手術,想通了再來找我。」
接下來就是幾個月的拉鋸戰,我進敵退,我疲敵擾。又一次疼得受不了,我再次找到了 C 醫生。
他檢查後說:「你這再不做手術就要肛瘻了,到時候再手術痛苦更大。」
得,看來這一刀不挨不行了。於是我在痛飲三瓶啤酒後,辦了住院手續。
我院肛腸科病房條件不錯,一樓的綠植鬱鬱蔥蔥,每天早睡早起,定時三餐,都是清淡的病號飯,其他時間和病友們暢談人生,過着佛系生活。
手術當天,正在哺乳期的妻子拋下家中老二過來陪我。她一直問我緊不緊張,我都輕蔑地回答:「這麼小個手術有什麼緊張的!」
其實我緊張。
時間到了,我坐在輪椅上被護士推走。護士告訴邊姬:「手術室門口冷,你就在病房等着吧,我們一會兒就給你推回來了。」但邊姬執意要跟着。
以前遇到這樣緊張的家屬,我總覺得沒必要。但真輪到自己頭上,才知道當自己被推進手術室時,背後有家人關切的目光,是多麼重要。
手術是局麻,但我寧願全麻,因爲清醒着被做手術,實在太煎熬了。
儘管 C 醫生是專家和好友,但我躺在手術檯上,依然有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感覺。
以前聽患者說「醫生我的命就交到你手上了」這種話,我都覺得戲太多,但換成自己是患者,也想說出這句話。
打麻藥前,C 醫生跟我說:「麻藥打了會有耳鳴,做好思想準備。」
我嘴硬:「麻醉咱見得多了,全麻都沒事,何況這個,來吧!」
很快我就被打臉了。打完麻藥後,我迅速開始嚴重耳鳴,整個人像陷入深淵,周圍的事物都發出嗡嗡聲,感覺很不真切。這讓我害怕又無助。
我聲音發顫地說:「我什麼都聽不到了!」
C 醫生聞言安慰:「這是正常現象,沒關係,我在呢,別緊張。」
聽到這幾句話,好像在漩渦中拉住了一隻溫暖的手,安心了很多。現在躺在手術檯上,真切體會到到來自醫生的一句簡單的安慰,對患者有多大意義。
術中,C 醫生的一舉一動都牽動着我的心,他手上慢一下,嘴裏嘆口氣,我都要擔驚受怕。
突然,C 醫生「咦」了一聲,我一下緊張起來,怎麼了?發生什麼事?難不成出了什麼意外?是不是切斷了括約肌以後要失禁了?
實在沒忍住問了他,他笑着回答:「又發現兩個內痔,一起給你做了,做一送二,便宜你了哈哈。」
你們說嚇人不嚇人嚶嚶嚶!
手術順利結束,我回到了病房。所有人的表情都很輕鬆,彷彿這件事情已經告一段落。其實難熬的日子纔剛剛開始。
不像其他部位的創傷,切口可以用紗布包裹着保持無菌狀態讓它靜靜長好,肛門手術註定切口每天都要經受糞便的洗禮,是污染切口,沒法縫,只能敞在那裏。
每天多次清洗、換藥,保持相對乾淨,讓肉芽組織從基底部長起來,慢慢填充缺損。
而這就造成了兩個後果:
一是恢復慢。傷口每天被折騰,自然長得慢。邊姬總用這個嘲笑我:「我生那麼大個孩子,肚子上劃開 20 公分,才住了 5 天院,你切個痔瘡而已,卻要一個月!」
怪我咯?
二是痛苦大。因爲肛周皮膚痛覺神經非常豐富,所以術後採用局部長效鎮痛藥浸潤麻醉+規律口服+必要時靜脈注射三種鎮痛。
但是仍在排便時痛得不敢用力,或者是鎮痛過量後導致想拉拉不下來的內急,然後找護士灌腸。
每天兩次的換藥體現得尤爲明顯。病友們排着隊一個個面帶微笑地進去,面目猙獰地出來,光排隊等着已經嚇夠嗆了。
輪到自己,躺在那感受醫生拿着鑷子一點一點清理創面,時不常還要爆個菊探探裏面的情況,那滋味真是又痛又屈辱。
我這個人特別怕痛,一有點風吹草動馬上各種止痛藥往身上招呼,所以整個過程還算能夠忍受。我科裏一個哥們也做了這個手術,但術後沒用長效麻醉,每天換藥生不如死。
後來他咬着後槽牙跟我說:「我算是知道換藥的滋味了,每個患者都應被溫柔以待啊,以後從我做起!」
好在痛苦每一天都在減少,佛系生活又慢慢地回來了。
我順利度過了術後三週的住院,出院後又在家裏休養了三週纔算完全恢復,結束了兩個月的折騰。
過程雖然不舒服,但結果是很爽的啊。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剛喝着啤酒喫掉一盆毛血旺,手術前打死我都不敢這麼喫。
比起因爲怕做手術而各種忌口的扭扭捏捏,我更喜歡斬草除根後同飲慶功酒的快意恩仇。害怕手術、對手術謹慎、緊張,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拒絕手術,那就是自己的損失了。
肛腸科醫生真的不容易,每天兩次換藥,每次處理幾十個患者的菊花,不管是流血、流膿還是流屎,都要一點點清理乾淨。
護士更不容易,都是二十出頭的小姑娘,在家都不曾伺候過父母的人,卻要每天給各種糙漢灌腸,聊天中說經常會碰到術後菊花功能暫時失調的患者,需要一點一點往出扣,或者突然被噴一身。
這樣的職業,月薪三五萬都在情理之中。可他們的工資遠少於這個數。
我能做的,也只有以一名普通患者的身份,在這裏向他們感謝和致敬。
本文標題是邊姬起的,我問她爲什麼如此惡毒,希望每個醫生都得痔瘡嗎?
她說她的本意是,每個醫生都應該做一次患者,體驗一場手術,才能做到換位思考。
之所以選擇痔瘡手術,一是因爲痔瘡發病率高,對健康影響不大,手術風險小;二是因爲手術痛苦大時間長,有助於加深體會。
當醫生成爲患者,纔會理解患者的焦慮和不安,纔會發現自己以前以爲的大驚小怪、少見多怪大多是情理之中,纔會意識到鎮痛、醫生的安慰對緩解患者的身心痛苦有多麼重要。
儘量讓患者明白他的疾病和手術原理、檢查和換藥等操作時儘量輕柔、對可能發生的不適提前預告、多笑多安慰、對患者的問題不要不屑不耐煩,做到這些不會耗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
如果你說:「現在的工作強度和收入,讓我沒有時間和心情做到這些。」那也無可厚非,但至少你應該能理解患者住院就醫的心情,不要輕易把他們當做無聊無知無理取鬧的人。
現在許多醫生都急切地盼望「被理解」,但或許被理解的開端,就是「去理解」。
本文授權轉自公衆號:不神醫堂
徐醫生薦讀:
口味有些重,女士慎入【多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