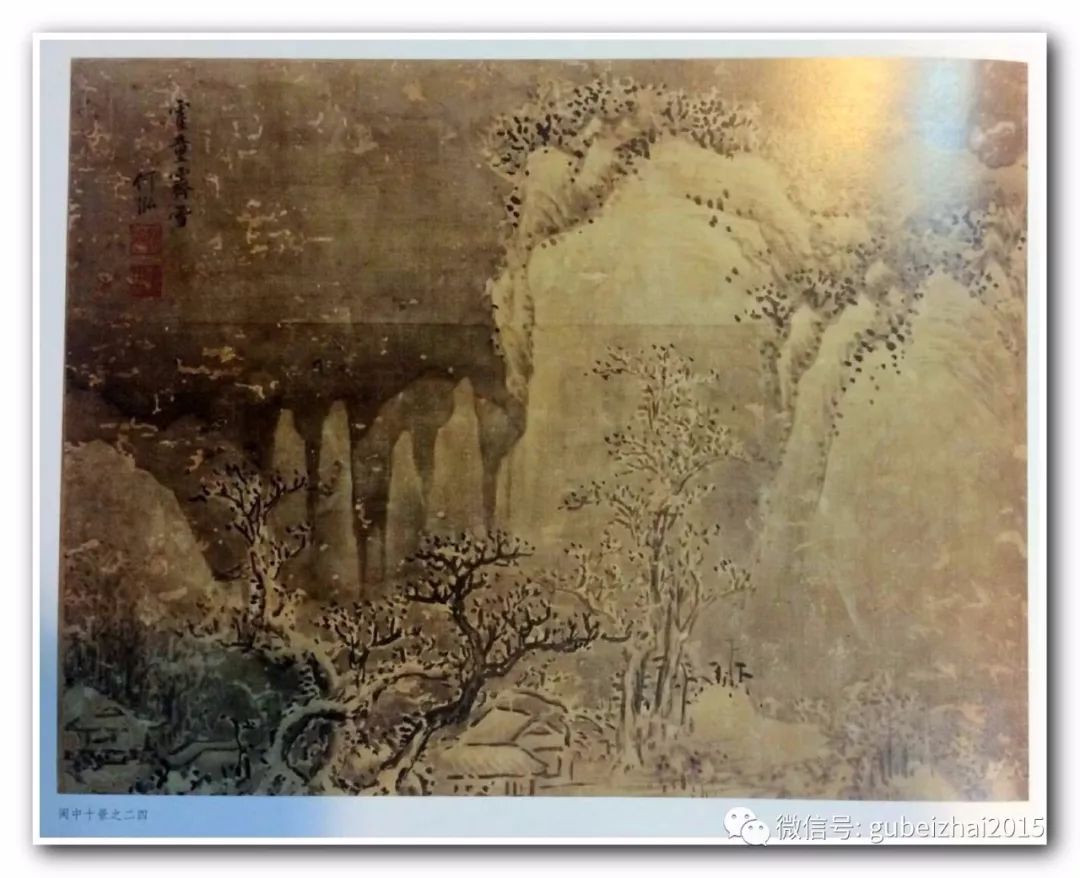陳仕玲 | 鄭宗霖生平及詩作賞析
摘要:曾任寧德知事的東甌名詩人黃式蘇對鄭宗霖的善政大爲稱讚,贈詩“已看流民圖鄭俠,還教諭蜀待相如”,用繪製《流民圖》諷刺時政的北宋名臣鄭俠,草檄喻告蜀民的西漢文學家司馬相如,來形容鄭宗霖關心民瘼的業績,評價是很高的。閩中詩人入社稱弟子者達數十位,鄭宗霖與福安穆洋人陳文翰躋身其間,成爲“說詩社”僅有的兩名閩東籍詩人。
霍童鎮,山清水秀,物產豐富。橫亙於古鎮西北的霍童山,爲道教“三十六洞天”之首。物華天寶,本應該是人傑地靈,但由於諸多歷史原因,霍童鎮自古少有官宦賢達。到了乾隆六十年(1795),出身霍童街黃氏大族的貢生黃鯁史深感地方教育落後,爲了使霍童各姓子弟能夠出人頭地,在風景奇特的大小童峯下修建了一座頗具規模的“雙峯書室”,並重金延請名儒魏敬中擔任西席,造就了一批棟樑之材。尤以進士黃樹榮和本文要提到的舉人鄭宗霖最爲著名。
一
鄭宗霖(1874~1950),字儕驥,又字守堪,號少甘。晚號“蟬窩老人”。同治十三年(1874)生於今蕉城霍童鎮霍童村一戶破落商人家庭。祖父實圃,經商爲業;父良勵,廩膳生。鄭宗霖幼受庭訓,髫齡即過目成誦,九歲能爲文。後家遭變故,父憂傷過度,臥牀不起。家人延醫診治,收效甚微。鄭宗霖夙夜憂嘆,乃仿效古代孝子,具疏禱告蒼穹,願減自身陽壽以補之。時有“孝子”之名。父親病故,家徒四壁,鄭母亦爲名門閨秀,與子相依爲命。鄭宗霖在母親的教誨下,學業進展很快。不久入“雙峯書室”,受教多年,孜孜不倦,遍讀六經諸史及百家之言。二十歲考取秀才。由於鄭宗霖學識淵博,名聲在外,被城關望族蔡家聘爲家庭教師。在蔡家執教期間,培育出了蔡祖熙、蔡祖霖等優秀學生。光緒二十八年(1902),鄭宗霖鄉試得中第二十一名舉人。時年二十九歲。
光緒三十年(1904),鄭宗霖進京參加會試,因試卷出現筆誤而名落孫山。三十一年(1905),科舉制度廢除,遂斷絕應試之心。光緒三十四年(1908),朝廷欽加鄭宗霖四品銜,授江西東鄉知縣。蒞任以後,鄭宗霖以漢代“飲馬投錢”的項仲仙、“蒲鞭示辱”的劉寬爲榜樣,關心政務,體民疾苦。深得東鄉士民擁戴。後丁母憂,辭官歸裏,東鄉父老攀轅臥轍,遮道涕泣。並贈以“萬民傘”,上面題有“民愛鄭侯之政,奈何挽之而不留”、“君去省親民失母,春暉一例共長吟”等讚語。
鄭宗霖丁憂回鄉後數年,清政府土崩瓦解。值此朝代更替之時,再加上軍閥混戰,民不聊生。鄭宗霖在政治和生活上很不如意,遂避居省垣,長達二十餘年。由於鄭宗霖爲官清正,辦事幹練,深得省府諸要員器重。民國二年(1913),閩省民政廳長張元奇聘爲行政公署總務處長,又委以福鼎縣長之職;繼任民政廳長劉次源及福建省長薩鎮冰屢次授以重任,均辭而未就。
鄭宗霖雖退居林下,仍憂心時局,對家鄉事務尤爲關注。民國七年(1918)七月,土匪吳鐵部300多人劫掠莒洲,燒殺姦淫,無惡不作,居民死傷慘重。民國十一年(1922),霍童遭遇百年罕見的大洪災,沿溪廬舍淪爲廢墟,哀鴻遍野;民國十七年(1928),土匪洗劫四都濂坑村,燒燬民房八十餘座,死亡五十餘人;民國十九年(1930),陳良鐵土匪入侵霍童長達四日,燒殺搶掠,焚燒店鋪百餘間,百姓流離失所。還有衆多的天災人禍,先後均仰仗以鄭宗霖爲首的在榕鄉賢奔走呼籲,先後均得到省政府的優恤。曾任寧德知事的東甌名詩人黃式蘇對鄭宗霖的善政大爲稱讚,贈詩“已看流民圖鄭俠,還教諭蜀待相如”,用繪製《流民圖》諷刺時政的北宋名臣鄭俠,草檄喻告蜀民的西漢文學家司馬相如,來形容鄭宗霖關心民瘼的業績,評價是很高的。
民國十二年(1923),由於重修的《寧德縣誌》久未成稿,寧德士紳續聘鄭宗霖爲總纂。鄭宗霖以體質孱弱爲由,婉言推辭,轉託福州舉人林步瀛擔當此任,不久得已告竣。
鄭宗霖作爲民國時期寧德文壇之翹楚,爲家鄉留下了大量墨跡文稿。蕉城城鄉許多匾額、楹聯、壽幛、墓誌都出於其手,至今仍多有保存,是研究民國時期地方文化的寶貴資料。
民國初年,名詩人陳衍由京返里,組織了著名的“說詩社”。閩中詩人入社稱弟子者達數十位,鄭宗霖與福安穆洋人陳文翰躋身其間,成爲“說詩社”僅有的兩名閩東籍詩人。
鄭宗霖晚年落葉歸根,閒居霍童,督課子孫,深居簡出。直至一九五零年去世。他一生娶有四房妻妾,有子四人。其中次子慶岷、三子慶嵋均出於壽寧名士葉昇門下。
二
鄭宗霖出身書香門第,幼年即隨父學習音律,國學基礎牢固。由於他苦心造詣,頗有成就。早年好遊歷,詩風清新俊逸。中年加入“說詩社”,受其師陳衍影響,詩宗兩宋,古樸蒼勁,嚴謹又不失宛轉曲折。成爲“同光體”的推崇和繼承者。陳衍的論詩意旨,痛斥盛唐詩人太白(李白)、岑(參)、高(適)、杜(甫)、孟(浩然)等其他詩派。他在《石遺室詩話》中揭櫫“詩莫盛於三元”:上元“開元”(盛唐)、中元“元和”(中唐)、下元“元祐”(北宋),尤其宗法宋人,學古而不摹古。目前,我們雖然還沒看到鄭宗霖的詩詞言論,但從他的存詩中可以大概領略到,他受陳衍的影響是深遠的。陳衍對鄭宗霖也十分看重,在著作中也多次提到鄭宗霖以及他的詩作。他嘗語人道:“少甘傑作如行雲流水,神態迥出天機,其深得名山大川之助多矣。”《石遺室詩話》曾三次提到鄭宗霖的詩作,並讚語:“守堪好詩甚多,佳句尤夥,幾不勝收。”陳衍於近世詩壇諸老中堪稱圭臬,有“六百年來一人而已”之譽,當時士林耆秀爭相附奉,以得先生一點評語爲榮。鄭宗霖以自己超人的造詣,得到業師的肯定,確屬難能可貴。
鄭宗霖早年壯遊東南名山大川,所作紀遊詩委婉清麗,蘊含山川靈秀之氣。中年幾經社會變革,詩風轉爲清峻奇峭,古樸蒼勁,字裏行間飽含着憂國憂民的情感。與之同時代的長樂人董子良贈以“憂患詩書裏,生存鋒鏑餘”詩句,是十分恰當的點評。
四川江油李青長(1861~1947),爲光緒二十九年(1903)舉人,民國時曾榮聘爲國史館顧問。青長工詩,存世者甚衆。爲近代蜀中著名學者。朱德任護國軍旅長,與青長交往頻繁,多有唱和。民國初年,鄭宗霖避難入蜀依附友人林振翰,與李青長得以結識。惺惺相惜,私交甚深。鄭宗霖曾評價李之作品雲:“電目雷膽,裁判古今,犁然不液絲毫,此殆所謂有天眼人也!”這也是至今僅見的鄭宗霖所作詩詞評論。
鄭宗霖一生著作較多,但歷經變革,今天能夠保存下來的已經不多。散見於《石遺室詩話》、《說詩社社錄》及蕉城民間譜牒、私家筆記、文集、碑刻中,約有詩詞三十餘首,文二十餘篇。他早年的詩詞代表作品有七言古風《黃陵廟》,中年代表作爲七律《追紀天遺老人入祀》,七絕《無題》,晚年則以七絕《蟬》爲代表作。
三
黃陵廟
黃陵廟前雲影孤,黃陵廟後啼鷓鴣。
聲聲勸君行不得,可憐客子已在途。
途中盡日何所有,但見雲影隨俱西。
客行日逐孤雲遠,轉勸鷓鴣休更啼。
這首七律,是民國初年,鄭宗霖應同鄉林振翰之邀,與林幼軒、葉從周相攜入蜀,在途中留下的一首作品。黃陵廟,在湖南省湘陰縣北洞庭湖畔,傳說舜帝南巡,死於蒼梧。二妃從徵,歿於湘江,後人遂立祠湖濱,是爲黃陵廟。由於此地歷史是屈原流放之地,且地處三楚要衝,古今遊客不絕。文人墨客過此最易觸發羈旅愁懷,唐李涉、鄭谷、李羣玉,宋張孝祥、明徐世佐、清將常泰、郭嵩燾均有留詩。但情緒都比較低沉,充滿萬千思鄉愁緒。鄭宗霖這首七言古風,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上沒有多大區別,但是意境優美,表達含蓄,實不失爲佳作。首聯“黃陵廟前雲影孤,黃陵廟後啼鷓鴣。”黃陵廟的鷓鴣,爲歷代遊客題句的重要素材。唐人鄭谷以一首黃陵廟《鷓鴣》而博得“鄭鷓鴣”的雅號。明徐世佐也有“鷓鴣不信蒼梧遠,飛向黃陵廟裏啼”的名句。鄭宗霖在這裏完全模仿李羣玉“黃陵廟前莎草碧,黃陵女兒茜裙新”寫法,開門見山,將黃陵廟周圍的優美環境展現在讀者面前。使讀者閉上雙眼,腦海中就能浮現出一幅迷人的圖畫來。這種句式的設計,對詩人所要抒發的情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讀後令人覺得客觀環境與詩人的心情十分和洽,由鳥聲而產生哀怨、悽切的情韻。第二聯語氣稍挫,詩人認爲思鄉的情緒固然難以避免,但既然“身在江湖”,就只能“身不由己”了。無奈之餘,表達了作者敢於面對事實,嘆惜卻不悲傷的情緒。這也正是詩人青壯年時代風華正茂的寫照。“途中盡日何所有,但見雲影隨俱西。”羈旅生涯旅途生活過於單調,只有默默無語的青山白雲相伴,當客船向東行進時,雲影、黃陵廟也逐漸消失在了詩人的眼簾,原來滿腔懷古的思緒也隨之煙消雲散。尾句“客行日逐孤雲遠,轉勸鷓鴣休更啼。”詩人遠遠地離開了黃陵廟,而悽清、哀怨的鷓鴣聲仍繚繞在耳畔。詩人曠達大度,雖然奔波旅途,胸中的憤懣早已化作了煙塵,但不知他的一番好意,是否能得到“鳥兒們”的共鳴。這一句承接第三聯,詩意卻豁然改變,別有天地。但與上句折而不斷,銜接地十分妥帖自然。與唐代金昌緒《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如出一轍。它表達了詩人複雜的情感世界。腐朽的清政府滅亡以後,進入了提倡民主的民國時代,但由於軍閥割據,戰火綿延,此時的鄭宗霖正是在入蜀依附友人的路上,半生的飄蓬不定,並沒有壓垮這位性格剛毅的年輕人。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鄭宗霖對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向上的,不論仕途是得意或失意,詩人總能勤於政事,與民休養。這種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借鑑的。整首詩以詩人自身、鷓鴣、浮雲爲描寫內容,情景交織,折射出深邃的人生哲理。
三
鄭宗霖自江西解組歸田,避居榕城以後,由於所處環境不同,接觸交流的都是當時省內乃至國內詩壇的頂尖人物,詩詞創作水平亦趨於成熟,詩風更見老練沉着,達到更高一層境界。從以下兩首詩足識端倪:
追紀天遺老人入祀
晚於湖上日相親,香火分明認夙因。
蕭瑟平生雙老淚,蒼茫天地一吟身。
高風汐社同埋恨,片月西江未洗貧。
百本梅花千歲鶴,閩山亦有姓林人。
福州西湖宛在堂原址爲明代高士傅汝舟築堂之所。清康熙年間(1663~1722)建有湖心亭。至乾隆時期(1735~1796),詩人黃任倡議將湖心亭建爲小樓,並取傅汝舟 “孤山宛在水中央” 詩意,名爲“宛在堂”,設以詩龕,祀福州“晉安派”著名詩人十位。歷代不斷增祀,至民國時期(1912~1949)竟達270位。由於福州託社社長林蒼於宛在堂詩龕吟事最爲出力,因此在民國十四年(1925)逝世後,經詩社同仁研究決定,榮幸入祀宛在堂詩龕。當時很多詩友都以詩文祭奠之,鄭宗霖這首七律也是作於這一時期。全詩盛讚了林蒼的身世人品,感情真摯,對仗貼切,耐人回味。陳石遺在《石遺室詩話》中曾對這首詩做過註釋。首句表現了詩人與林蒼結社西湖,志趣相投,觴詠終日,樂趣融融。詩人佩服林蒼的聲名,認爲林蒼的入祀宛在堂是理所應當,無絲毫自矜及妒忌之氣,誼摯情深,溢於言表。正如陶淵明《雜詩》中所說的:“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接着,詩人又抒發了對林蒼的哀悼之情。林蒼籍貫閩縣,是光緒三十年(1904)進士,曾任江西石城知縣。爲官清廉,去任時宦囊蕭然,與之同省爲官的鄭宗霖對此是十分了解的,林蒼一生淒涼貧苦,自己也久寓榕城,處境艱難,因此產生了同病相憐的想法。作者更是愁腸百轉,老淚縱橫。陳石遺認爲頷聯爲“一窮老詩人之寫照,其一生別無他好,只嗜吟詩,而所吟之詩,無非一雙老淚者。”實“字字貼切”。筆者則認爲頷聯一語雙關,既是在解說林蒼,更是詩人在排遣內心的憂憤。鄭宗霖與林蒼進入民國以後,面對軍閥混戰的局面,清高自奉,不再入仕。二人情深意篤,肝膽相照。而今林蒼撒手塵寰,詩人又失去一位知己,不免產生“蒼茫天地一吟身”的感慨。頸聯借用了南宋謝翱“汐社”的典故,進一步表明詩人的心跡。元朝初年,詩人謝翱對宋室一本初衷,保持民族氣節,積極聯絡遺民方鳳、吳思齊、吳謙、鄧牧等成立“汐社”,以詩文作爲抗爭工具,進行愛國宣傳活動。鄭宗霖自清朝滅亡以後,鬻文自給,屢次拒絕民國地方政府授予的高官厚祿,表現出始終如一的品質。這與其師陳石遺自詡的“吾入民國後,決不爲官,經口不談政治”的作法如出一轍。這種保守的遺民心態雖不可取,但鄭宗霖憂國憂民、關心時事、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舉動,比起同年鄭孝胥、梁鴻志等附逆文人卻不知強了多少倍。下句描寫林蒼任職江西清廉自守,一個“貧”字成爲林蒼生平的真實寫照。末尾兩句則是對林蒼的人品、詩壇地位的蓋棺定論。詩人在這裏把林蒼比作南宋著名詩人林和靖,高等的評價,洋溢着詩人對林蒼崇敬與仰慕的心情。林蒼自號“耕梅”,詩友陳篤初也曾贈之“止水枝清猶或滓,老梅氣鬱總能香。”縱觀鄭詩情真意切,用詞深沉,堪稱佳作。
我們再看這一首七絕:
無題
雁鳴能引人呼嘯,蛩語如吟世亂離。
閱盡滄桑還不死,太平何日見希夷。
全詩語調低沉,悲涼蒼勁,發自肺腑,直抨時政,頗有南宋陸游、陳與義的悲壯風格。故與“秦皇焚書恨未盡”在《石遺室詩話》中同被列爲“警句”。開頭兩句採用比興的修辭手法,引物自喻,以“萬物肅殺”的秋季爲背景,反映出民國末期江河日下,民無寧日的真實狀況。雁鳴蛩語襯托出詩人內心的苦悶,他對現實倒行逆施,產生悲觀絕望。詩人身經朝代更替,慨於時事不堪過問,報國無門,平生抱負皆付諸東流,而今苟延殘喘,感慨萬千,纔有了語重心長的末句,這句“太平何日見希夷”取自北宋邵雍《邵氏見聞錄》:
“陳摶(字希夷)常乘白騾,以惡少年數百,欲入汴京,中途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
可謂擲地金石,錚錚有聲。民國時期,烽火遍地,四分五裂,百姓顛沛流離,飽受戰爭之苦。局勢與五代十國時期頗爲相似。詩人爲之痛心疾首,他能突破一己之得失,將國家命運、蒼生疾苦牢掛心上,北宋文學家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憂國憂民的思想素爲古代讀書人所看重,鄭宗霖言行一致,爲官則清正廉潔,居鄉則關心地方公益,爲後人留下了良好的形象,同時也爲後人樹立了榜樣。
四
民國三十年(1941),日寇魔爪伸向東南沿海,福州慘遭淪陷。鄭宗霖不甘受辱,從榕城返回霍童老家。過着“課諸孫,以田園自足,且恆年深居簡出”的恬淡生活。年過古稀,壯志豪情已大有減退,詩風則更見古樸。爲了明志,鄭宗霖晚號“蟬窩老人”,並留有一首七絕《蟬》:
何不高飛與世爭,一生誤汝是廉名。
葉間是否無多露,死抱殘枝盡力鳴。
蟬作爲清高孤潔的象徵,被歷代詩人廣泛引用。尤以唐代虞世南、駱賓王、李商隱三首詠蟬詩最爲膾炙人口。宋人計有功《唐詩別裁》中曾評價李商隱的一首詠蟬五律:“詠蟬者每詠其聲,此獨尊其品格。”雖然各人的經歷不同,處境不同,寄託的情感自然也不同,但是蟬的形象在三位詩人心目中的地位是一致的。鄭宗霖這首七絕不泥古法,認爲蟬的優點其實正是它的弱點。蟬因爲“廉名”束縛,高立枝頭,吸風飲露,自命清高。待等秋去冬來,即化作烏有,無處尋覓。這種與世無爭,安於現狀的生活方式在詩人看法中是不可取的。一方面蟬體弱小,不可能與鷹隼比翼飛翔,這正是七旬老者的真實寫照。詩人空有一腔熱忱,卻只留下了無盡的遺憾,生活環境的惡劣,也使他心灰意冷。從這首詩總體來看,鄭宗霖對人生的態度還是比較積極的,我們仍能感受出他不甘衰老的奮發氣概。全詩無文字矯飾,樸實傳神,說眼前景,道心中事,不借助典故,信手拈來,卻別有韻味,這正是鄭宗霖晚年詩作的一大特色。
鄭宗霖的作品給我們留下了歷史的鴻爪,時代的印記,其雋永的詩作將流傳不殆,百誦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