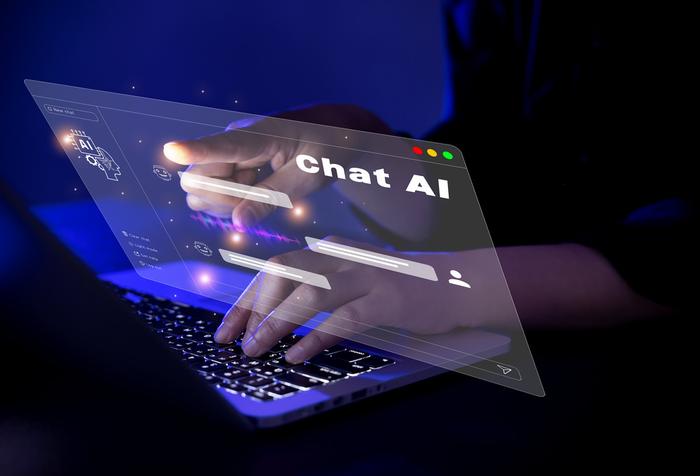師大教授:價值觀危機是中國教育的根本危機
(原標題:價值觀危機是中國教育的根本危機)
77歲的葉瀾自1962年從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畢業留校工作,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持續從事基礎教育改革的實踐和研究。在此期間,她首創並主持了“新基礎教育”研究與“生命·實踐”教育學派的建設。
教育改革與教育學理論建設是中國問題,也是世界問題。三十多年來,葉瀾和她的團隊紮根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教育變革實踐,以中國話語、中國思維方式,形成了當代中國教育學的整體原創型態,被認爲是對這一世界問題的中國回答。
日前,葉瀾教授的集成之作《迴歸突破:“生命·實踐”教育學論綱》被譯成英語,向世界發行。這本專著以獨特的視角解讀了西方的教育思想,而且有所突破,它表達了對西方教育思想的尊重和理解,同時明確了中國教育思想必須保持獨立,體現中國文化的獨特。
一些西方學者認爲,《迴歸突破》顛覆了西方對中國教育的刻板印象。中國地方學校在主動創造方面積累了值得西方學習的獨特經驗;與這樣的學校實踐相關的教育思想,同樣顛覆了西方對中國教育研究的刻板印象。
近日,《中國新聞週刊》就中國基礎教育的現狀、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及中國教育學派的構建對葉瀾教授進行了專訪。
“以‘成事’替代‘成人’
是當前教育最大的問題”
中國新聞週刊:基礎教育是全社會都很關注的話題。在這方面,大家的議論和不滿也很多。你認爲,當前中國基礎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葉瀾: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複雜的思維方式,不能平面地看教育。在我看來,認識基礎教育至少有三個層面。首先是宏觀層面,教育政策、要求和目標的制定;其次是學校,我們稱之爲中觀層面,作爲教育最基本的“細胞”,在這裏發生着教師和學生之間真實的教育行爲;再次是微觀層面,各種教育行爲怎樣轉化爲學生的發展。社會上議論較多、家長感受較深的主要是第二個層面的問題。但實際上,宏觀層面的問題也不少。
我一直有這樣一個看法,宏觀的教育決策,應該解決宏觀層面的問題,而不是直接去要求其他層面的事情。但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的宏觀決策對學校教育實際存在的需要和發展遇到的困難並不是很清楚,往往是把政治、經濟方面的要求簡單地移植過來,規定學校做這樣做那樣,但好心未必辦好事。
比如,爲了解決教育公平的問題,現在很多地方要求學校每年有一定比例的教師要流動,有的地方還要求校長也要流動。這個想法是好的,期望通過師資的流動,達到教育均衡的目的。但問題是,每個學校內部都有自己的文化,想通過換校長的辦法,短期內改變一個學校非常困難,往往是新校長還沒完全熟悉情況,又被調走了。最後,結果是不僅差的學校沒有得到改變,而且原來好的學校反而因爲師資力量的流失,教學水平下降了。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所以我認爲中國的基礎教育,如果宏觀決策不反思,是很難做好的。
中國新聞週刊:你剛纔談到的是宏觀決策的問題,對於學校層面你有什麼看法?
葉瀾:作爲教育的主體,學校在整個基礎教育過程中起着非常關鍵的作用,因爲對學生的發展最直接、最真實的教育行爲主要發生在學校。就像前面提到的,現在學校教育面臨很多問題,經常受到家長的詬病。我認爲,學校教育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以“成事”替代了“成人”。
在學校裏隨處可見教師爲事務而操勞,關注學生考分、評比、獲獎等顯性成果,忽視、淡漠的恰恰是學生和教師在學校中的生存狀態與生命質量的提升。即使在改革開放已40年的今天,依然存在着教育者心目中有教書無育人、有知識無生命,不真正把學生作爲一個個鮮活的生命個體來看待的問題。
這種對個體特殊性以及個體生存方式的忽視,造成了課堂的根本缺陷:把豐富複雜、變動不居的教學過程簡化爲知識傳遞的活動,把它從整體的生命活動中抽象、隔離出來,導致課堂教學缺乏生氣與樂趣,變得機械、沉悶和程式化,失去對智慧的挑戰和好奇心的刺激,師生的生命力在課堂中得不到充分發揮,精神生活趨於“沙漠化”。
中國從來不缺聰明、有潛質、可成爲尖端人才之人,缺的是把潛質變成現實的發展。教育在實際上常常只是訓練的過程,老師講、學生被動聽和記,缺乏思維的活躍和課堂生活的積極體驗。日積月累,往往使本來具有生命能動性的人異化爲被動機械的“物”。學生如此,教師同樣如此,生命異化爲滿足教育之外目的的工具,教育也異化爲沒有生命關懷、沒有創造活力、缺乏精神追求的事務。
“不能把教育改革的希望
全都寄託在高考改革上”
中國新聞週刊:這些問題談論了很多年,現在很多地方也在提倡素質教育。但有種觀點認爲,只要現行的高考制度不改革,基礎教育就無法擺脫當前的怪圈。你同意這種看法嗎?
葉瀾:我覺得,不能把基礎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寄託到高考改革上。我對長期以來批評“高考指揮棒”也有自己的看法,好像把基礎教育的一切問題,一股腦兒歸結爲由“高考指揮棒”造成,就能解釋一切或很快改變。這種判斷的實質是想用管住“出口”的方式,來改變整個教育教學的“過程”。“出口”的控制和“過程”的開展是兩件事,不能相互替代。
高考的改革,不管是選拔式的還是鑑定式的,總歸要通過測試。你不能把教師應承擔的教育改革的責任,都交到改革高考方式、方法上。承擔高考改革與承擔中小學教育改革是兩個不同的主體羣,儘管這兩件事相關,但它們各自承擔的責任不能替代。
影響教育全過程的因素很多很多,絕對不只是高考出什麼試題的問題。所以我說,我們可能抓錯了源頭。孩子從小到大要長十幾年,孩子進小學的時候離高考還遙遠。如果我們強調高考改革了才能改革基礎教育,這種說法會帶來什麼呢?中小學教師、校長可以說:你高考還沒改好,我改革了會對不上你的高考,所以我沒辦法改革!其後果是中小學教育責任的承擔者,可以對一個漫長的教育積累變化過程不着力去研究和承擔責任,把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也爲不改革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我不是說高考不要改。要改!但是不能把基礎教育改革的希望全都寄託到高考改革上。這也許是素質教育提出二十多年卻進展不大的原因之一。
中國新聞週刊:那你認爲,基礎教育改革該從何入手呢?
葉瀾:中國教育改革的起點在哪裏?已有的改革方案,或編制新課程新教材,或改變教學策略與方法,或提升學生成績,或培訓新教師新校長等等,以此作爲教育改革的出發點,各種教育改革流派隨之而生。但我認爲,價值觀是一切教育教學改革的起點,價值觀危機,是中國教育根本的危機,教育轉型應從價值觀轉型開始。
三十多年來,我和我的團隊一直在致力於“新基礎教育”研究,這是一項以學校整體轉型爲指向的教育改革。它的“新”,首先新在“價值觀”。我們提出以促進學生的生命發展爲最根本的教育價值觀。
促進生命發展的價值是教育的基礎性價值,教育具有提升人的生命質量和豐富人的精神生命的意義,具有開發生命潛能和提升發展需要的價值。教育的過程是把人類生命的精神能量,通過教與學的活動,在師生之間、學生之間實現轉換和新的精神能量的生成過程。
師生主動、積極投入學校各種實踐,是學校能否實現上述價值的前提性保證。“新基礎教育”就是要把課堂還給學生,讓課堂煥發出生命活力;把班級還給學生,讓班級充滿成長氣息;把創造還給老師,讓教育充滿智慧挑戰;把精神發展的主動權還給學生,讓學校充滿勃勃生機。
“當下中國教育學建設
需要改變‘依附’心理”
中國新聞週刊:從這些年的實踐看,“新基礎教育”改革的成效如何?你覺得,它能夠改變中國的基礎教育嗎?
葉瀾:“新基礎教育”是通過深度改革,提高教育質量和師生的生命質量。這種變革要求我們一個學校接一個學校地去做工作,去改變校長、教師的觀念,變人、變學校、變文化,把舊我變成新我,把近代型學校變成現代型學校。
這項工作需要時間,需要腳踏實地一點一滴的努力。一旦一個學校的教育質量得到提高,我們就通過聯合研討的方式,而不是簡單的教師調動,讓他帶動其他學校的發展。因爲,我們相信一個學校的發展必須依靠它內在力量的成長。所以,我在合作研究伊始,對參與“新基礎教育”的學校所屬地區有關領導,有一個要求:五年內不換校長,以保證整個改革的持續進行。
當然,我和我的團隊畢竟力量有限。我們從不指望自下而上、具有典型草根性質的“新基礎教育”能夠改變全國的基礎教育。我的心願無非是改變一個個教師、改變一所所學校、改變一個個區域,這樣,“火種”總存在着變爲“火炬”的可能。
我們從事“新基礎教育”就是想告訴大家,有一羣執著教育的人走了一條不同的路,而且這條路走得通。同時,爲了讓更多的人瞭解“新基礎教育”,這些年我們在實踐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全新的教育學派——“生命·實踐”教育學派。
中國新聞週刊:學派建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你看來,與其他教育學派相比,“生命·實踐”學派有什麼獨特之處?
葉瀾:教育學是近代中國自西方引進的衆多學科之一。事實上,直到今天,教育學在中國還是一門很少人真懂,許多人輕蔑、嘲笑的學科,認爲教育學沒有也不需要理論,這造成了我們現有的教育學理論大多來自西方,缺乏中國自己的教育學家和教育學理論。
當下的中國教育學建設需要改變“依附”心理,太需要有一批具有獨立人格、矢志不移,而且具有大愛心、大智慧和大境界的人,一起努力,改變這種狀況。由這樣的人組成的隊伍,不能指望只在書齋中產生,更多的要在教育變革實踐中經歷理論與實踐的雙向互動,才能形成。
教育學是研究造就人生命自覺的教育實踐的學問。在我的教育學研究生涯中,最能打動我的兩個字是“生命”,最讓我感到力量的詞是“實踐”。
“生命·實踐”教育學派是直面當代中國教育學面臨的挑戰,對教育學的整體形態和形成過程進行了當代反思與重建,是基於中國問題、立足中國實踐、運用中國資源、通過中國學者,以中國方式表達的中國原創的教育學派。
教育改革與教育學理論建設是中國問題,也是世界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生命·實踐”教育學派正是對這一世界問題的中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