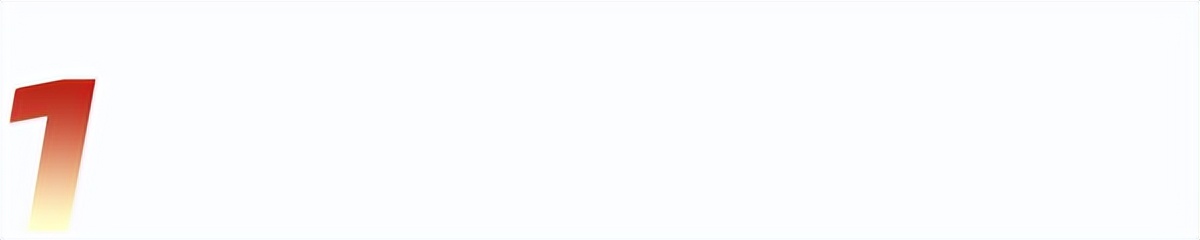故鄉蕎麥花似雪,常入夢中勾情懷
故鄉蕎麥花似雪,常入夢中勾情懷
作者:若耶非耶
行行數里猶回首,秋雪滿山蕎麥花
(明)吳兆《別九華山二絕》

20世紀90年代以前,漫山如雪的蕎麥花,是北川最美的秋天景象。後來,因退耕還林耕地面積大幅減少,尤其是效益更高的謀生門路多了之後,蕎麥種植便基本上退出了人們的生活。看着蕎麥花發呆的種種情結,成爲一代代北川人記憶中那一縷縷抹不掉的鄉愁。
一
英雄轉眼逐東流,百戰工夫土一抔。
蕎麥茫茫花似雪,牧童吹笛上高丘。
三十多年前,當我讀到范成大這首《長沙王墓》時,覺得他是站在北川明代永平堡或伏羌堡的城牆上所寫。逶迤的羣山腳下,河流如一根繡花的細線,明亮而悠長;山坡上一片片正在開花的蕎麥如同村姑繡出的掛毯,美得粗獷、神祕而又令人神往。城牆外的蕎麥花隨風拂動,飄來一陣陣淡淡的馨香,你便不由自主地長長深吸幾口,然後咂吧着口水美美地想那誘人的蕎花蜜。人間如此美好,卻又有着殘酷無情的戰爭。那些戍邊將士離鄉別家奔赴撕殺的疆場,與素不相識、無怨無仇的敵人相互殘殺,你死我活。正如北川老人所言:關塞處處留白骨,馬革裹屍幾人回。歲月如水一般地流淌,戰死的英雄也早就只剩一抔泥土。溫暖無比的愛情、親情,一同埋進了親人的無盡痛苦和歷史的縫隙之中。在歷史的長河中,腥風血雨過後,曾經的戰場,蕎麥花依舊盛開似雪,牧童在高高的山丘上悠閒地吹着羌笛,憧憬着未來。
 圖爲永平堡明代松潘總兵巡行駐地遺址。
圖爲永平堡明代松潘總兵巡行駐地遺址。當我第一次到永平堡時,就被城牆那高峻、壯偉的氣勢和宏大的規模所震撼。古人云:兵者,兇器也。作爲兵之“重器”的城堡,我們既不知道有多少生命之花凋謝在了修築它的過程之中,也不知道有多少衝鋒的羌人死在了它的城牆之下。
今天的北川羌人在面對這處“兇之重器”時,頌揚或詛咒,都無法表達矛盾而複雜的心情:
永平堡前何蕭森,鄉關舊夢總斷魂。
滿山蕎花開似雪,荒城落日染血痕。
何卿生祠的建築早已蕩然無存,只有被歲月剝蝕得難以卒讀的《何公生祠碑》依然佇立,但又有幾人知道,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戰將卻在今上海一帶的戰鬥中屢戰屢敗,不得不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歷史,總是弔詭得找不到理由。也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波浪似地相互裹脅着前進就是它不容置疑的邏輯。

二
成書於西周至春秋時期的《詩經》中已有蕎麥的記載,距今2000多年,但它的種植歷史肯定更爲久遠。
北川什麼時候開始種植蕎麥,則因資料缺乏無從考證。清乾隆《石泉縣誌·食貨志》物產載:“邑種蕎。有春蕎、秋蕎。有甜、有苦,民資爲生。” 清《四川通志·物產》龍安府下記載說:“蕎麥,有苦、甜二種,民資以爲食。”《石泉縣誌》不僅記載了有甜、苦兩個品種,而且還記載了兩個可以播種的季節:春、秋。宋大觀元年(1107),李新(1062-?)赴茂州通判任途經北川,他在《蕎麥》一詩中說:“神農播百穀,賜羌蕎麥種。下子分苦甘,甘賤苦蒙寵。” 由於甜蕎主要是靠昆蟲和風力傳播花粉,而苦蕎則屬自花傳粉,產量比甜蕎要高,且種子不易退化,所以“甘賤苦蒙寵”,人們更喜歡種植苦蕎。
雖然無法斷定北川從什麼時候開始種植蕎麥,但我們知道,在玉米、洋芋(土豆)傳入北川之前,蕎麥是最爲主要的農作物之一。在其它農作物遇到自然災害被毀時,蕎麥往往成爲“替補”作物種植,以彌補損失。
蕎麥麪可以做成麪條、涼粉等食品,尤其是涼粉,更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經典美味。蕎麥麪饃饃是祭祀神靈的必備供品,蕎麥殼還是枕頭芯的最佳材料。
豌豆開花角對角,男人走了睡不着。
抱到枕頭打個啵,杵了一嘴蕎殼殼。
(北川土語音:角對角,各對各;睡不着,睡不戳;啵,be兒,意爲親嘴;殼殼,渴渴。)
這首極富生活情趣的北川民歌,就是蕎麥物盡其用的生動寫照。
 蕎麪涼粉
蕎麪涼粉三
1987年7月,我第一次去小壩鄉(已改爲鎮)做文物調查,因事先有幾位老先生的指點,所以目標也非常明確:小壩街橋頭的元代摩崖石刻、街後半山上的走馬嶺,內外溝的二郎廟和天主教堂。
走馬嶺,是因爲那裏曾有“走馬廟”而成爲調查對象。從小壩街到走馬嶺,有一條坡度超過60度的山路。當我氣喘吁吁地走到嶺上那塊大平地時,哪見廟宇的影子!只有用破木板、竹子擋風的三間小瓦房孤零零地佇立在那裏,倒是有口水井消除了一些荒涼的感覺。
我正四處張望時,從房子旁邊走出一個頭高高的小夥子,他問我是哪個單位的?來這幹啥?我說,我是縣文化館派來普查文物的。他說:廟子早就毀了,東西全都打爛了,聽說是縣上的紅衛兵來打的。我邊和他閒聊,邊四處搜尋了一番,除了一些殘碑之外,並沒有其它有價值的東西。我向他借來一隻水桶,想用井水把一些殘碑清洗乾淨,再把文字抄錄下來。
抄到快1點左右,我看時間不早了,就打算把帶來的饅頭喫掉後,趕緊去下兩個調查點。這時,他走到我旁邊說:老師,我飯煮好了,飯喫了再來抄嘛。我說,我帶的有饅頭。他說,饅頭你下午餓了好喫,我飯都煮好了。我再次禮貌性推辭,他說,是不是嫌我髒嘛。我說,不是不是。推辭不了他質樸的熱情,我走進了他那隻能遮雨,卻不能擋風的房子。
堂屋的桌上擺着一大碗臘肉、一大碗蕎涼粉,其它還有什麼菜,如今倒是想不起來了,但臘肉和涼粉給我的記憶可謂刻骨銘心。因爲後來在與鄉幹部的聊天中,我得知那小夥子30多歲了,還單身一人。知道這些,我的心裏反而湧出一種莫名的酸楚。一個家徒四壁的陌生大哥,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拿出了他自己都捨不得喫的美食,還一個勁地叫我:老師,你多喫點。也許當時我自己也是嘴上無毛的年紀,沒有進一步向鄉幹部再多問一問他家裏的情況。他爲什麼孑然一人住在那裏?他的父母呢?甚至連他的姓名都沒問過。後來,每每想起這事,很是內疚。

喫好飯後,我拿出2塊錢欲付他伙食費。他笑着說:老師,你見外了,你到這裏來,就是我的客人,我咋會要你的錢嘛?你要不是來抄這些碑,我請還不一定能把你請來呢!
拗不過他的真誠,我一再道謝並與他告辭,奔向下一個調查點。
民國《北川縣誌·廟壇祠觀表》載:“寶華寺,走馬嶺,七楹四合,正殿供佛祖像及文殊普賢像,明萬曆年造。”因其地名,才被人們俗稱爲走馬廟。
明嘉靖、萬曆年間,是白草羌反抗朝廷最爲激烈的時代。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白草羌酋長自稱皇帝,並封李保將軍、黑煞總兵等職。嘉靖二十四年(1545),趁官軍防禦鬆懈之機,白草羌數千人突然襲擊了大魚口的平番堡,數百名官軍成爲俘虜,並直接威脅到石泉縣城(今禹裏鎮)和隴東路(石泉縣城到松潘、茂州的交通線)軍需運輸的安全。四川巡撫張時徹、松潘總兵何卿經過一番周密謀劃後,於嘉靖二十五年(1546)臘月底,指揮三萬多官軍,分三路對北川地區的羌寨發起了釜底抽薪式攻擊,於次年正月在走馬嶺大敗羌人,徹底控制了白草河上游地區。明萬曆七年(1579)三月,元氣盡喪的白草河流域羌人不得不向朝廷投降。曾經是撕殺戰場的走馬嶺,大概就是在萬曆七年(1579)之後,修建了寶華寺。
明萬曆年間,瞿九思在所著《萬曆武功錄》中第一次爲北川羌人立傳,曰《白草風村野豬窩諸羌列傳》。小壩走馬嶺一帶羌人,野豬窩等寨是其代表。風村,即今青片河一帶。
離開走馬嶺時,雖然我沒有看到蕎麥。但我知道,每當蕎麥花盛開的時候,站在走馬嶺上,看到的一定是白居易《村夜》所寫的景色:獨出前門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雪。
 ▲小壩場北面的走馬嶺
▲小壩場北面的走馬嶺
四
離開走馬嶺,我快步向內外溝二郎廟、天主教堂而去。
民國《北川縣誌·廟壇祠觀表》載:“二郎廟,內外溝,四楹四合,內供關聖、川主、真武各神像。”可見,這是一處道教活動場所。位於通往內外溝大路旁的山坡上,掩隱在一片樹林之中,距大路約300米左右。我到二郎廟時,天色已經開始變暗了。我快速地找好位置拍了幾張照片(120膠片相機)後,立即進廟對其樑架構造等作了觀察,找到樑上立廟的時間,畫出示意圖,並估測了幾個主要數據。
二郎廟那棵高大的柏樹,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
由於時間已經太晚,我不敢在此久留,便匆匆趕往內外溝的天主教堂。民國《北川縣誌·廟壇祠觀表》載:“志道堂,內外溝,六楹四合。”天主教大約在清同治元年(1862)傳入北川,光緒三十年(1904)左右,傳入片口和小壩內外溝。民國前,其教務一直是一位法國神甫在負責管理。
志道堂處在一片民居之中,旁邊還有一所小學。我到這裏時,學校已經放學,天色已經很暗了。院裏的人突然看到闖進一個陌生人,都很詫異,有個女青年問我,你是哪裏的?天都黑了來這裏幹啥?我簡單地作了介紹,周邊的人告訴我,她是學校的老師。在這位老師的引領下,我走進教堂看了看,覺得這裏沒有我需要進一步瞭解的東西,加上天色已黑,還要返回鄉政府,就對女老師告辭說,這裏沒有需要詳細瞭解的東西,我回鄉政府了。她說,都這麼晚了,回鄉政府還很遠呢,今晚就住在這裏,明天再回去吧。女老師的年齡和我差不多,我覺得住下來會給她添不少的麻煩。我說,我跑得快一點就是了。她說:這路上有點怕哦。我說:我不怕,謝謝你!我邊說邊快步踏上返程。這時,天色已經渾渾沌沌。
 網絡配圖
網絡配圖這一路到鄉政府要走一個多小時,沿途基本上沒有人家。有一段路的邊坡上,還有一片墳地。我一陣小跑、一陣快步,交替着調整體力和速度。原野裏只有我一人在行走,寂靜的夜空裏還時不時傳來一聲聲怪異的鳥叫。前段時間的文物調查中,我也常常一個人在幾十裏沒有人煙的樹林中穿越,也敢在偏僻的墓地憑藉手電筒鑽進那些被破壞了的“蠻墳”中,說來膽子也夠大的。但這一路,卻讓我越走越後背發涼,頭皮發麻,頭髮更是如鐵絲一般直立。夜裏走路,你會覺得那些越是黑得可怕的東西,越是在主動向你靠近。快步、小跑,堅持了半小時左右,就再也跑不起來,再也快不起來了,只能慢慢走。在這之前,曾聽一個內外溝的人說,有一天晚上他在這段路上碰到過“走陰兵”:陰曹地府的軍隊人喊馬叫,浩浩蕩蕩地呼嘯而去,場面恐怖,令人魂飛魄散。而我遇到更恐懼的,則是快到鄉政府約三里的地方,那段路從數百米高的懸崖上攔腰穿過,是硬生生在崖壁上鑿出來的。
我的一位表兄,因他老婆的孃家是內外溝的,因此對這段路況有點熟悉,他曾告訴我,就是在這段路上,有兩個迎親抬衣櫃的人,只因衣櫃在崖上碰了一下,結果雙雙跌入萬丈深淵。走在這段路上,我就越是想起他說的這起事故,雙腿發軟,只得弓腰順着最裏邊的排水溝走。抬頭,望見的僅僅是對面山頂上空的星星點點,往懸崖邊看,彷彿伸手就能觸摸到對面的崖壁。嘩嘩的流水聲則似從腳下一個很深很遠的地方傳來,那聲響裏帶着咄咄逼人的寒氣,使人腳板底發癢,我是連走帶爬走過了這段路的。
其實,半路上我就已經後悔沒聽那女老師的勸。當我回到鄉政府打開客房房門時,一下就癱軟在那裏。
五
宋李新在《答李丞用其韻》詩中說:“頑雲垂翼山碉暗,蕎麥饒花雪嶺開。”過去,北川最佳的蕎麥花欣賞地,還有壩底河兩岸,“蕎麥花開似雪鋪”的宏大景像(宋姚勉《道中即事其五》),只有套用清初汪琬的詩句“彌望蕎麥花,沿流獨如雪”(《泛溪》)才十分妥帖。北川的秋天,溼度大、晝夜溫差大,很容易起霧。一片片蕎麥花、碉樓、吊腳樓在霧中朦朧、縹緲,如人間仙境。在我看來,霧裏的蕎麥花是最美的,猶如披着蓋頭的新娘,妖嬈而又模糊。只是,北川這樣的美景,已經很少能夠看到了。

時光荏苒,參與文物普查雖然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仍有不少的經歷銘刻在記憶的深處,耿耿於懷。我常常想起那些幫助過我的人,尤其是2008年5·12地震災難之後,滄海桑田、物是人非,走馬嶺上的那位大哥、內外溝那位鄉村女老師,你們還好嗎?
(2021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