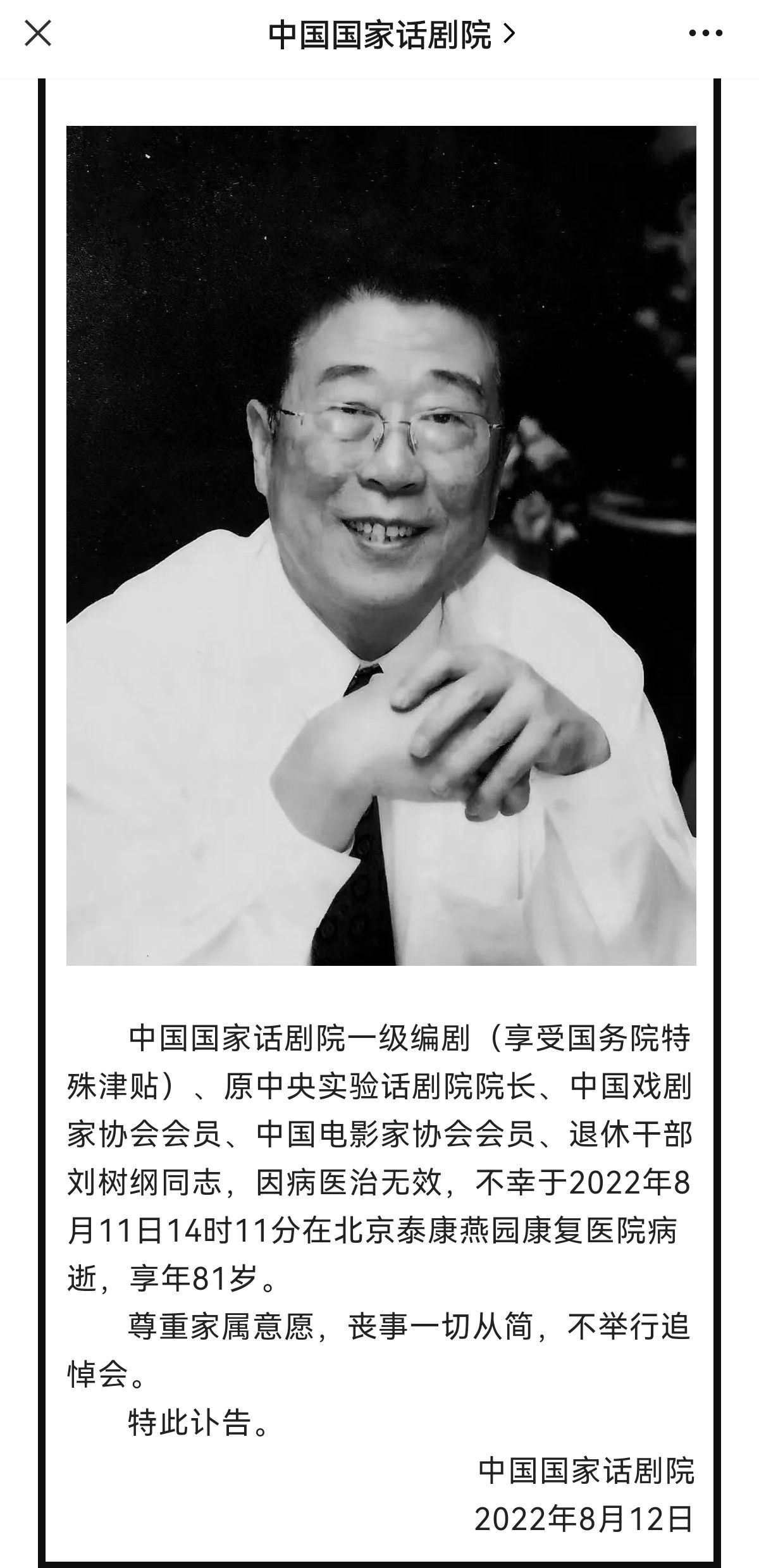廢物研究所:撿得開心,廢得豐富
來源: 三聯生活週刊
“我看到一個東西,覺得能變,就發揮一下,讓它有新的生命。”
記者 | 安妮
2021年底,第28屆開羅國際實驗戲劇節,生於1992年的中國設計師於雷爲實驗劇《廢話製作工廠》設計的舞美入選當屆非常規先鋒戲劇設計展,與國際著名舞美設計師們的作品一道在埃及歌劇院Hanager藝術中心展出。

於雷在海拉爾
通常情況下,舞美設計師的工作從手稿開始,再用電腦製圖,最後製作成戲劇舞臺上的佈景和道具。與大多數設計師相比,於雷的設計過程顯得“草率”得多。他沒有電腦,從不畫圖,創作一概從廢舊材料出發,與其說是設計,不如將他的創作描述爲改造。“我看到一個東西,覺得能變,就發揮一下,讓它有新的生命。”
《廢話製作工廠》假設了一個極端又荒誕的情境:除了溝通交流之外,語言也許還有別的作用。未來的某一天,人類發現語言可以產生能量,並且與風和水一樣,是可以循環再利用的資源。這座語言再生工廠由工廠裝置、機械木偶、燈光裝置組合而成,工廠裝置是舞臺核心,連接着一個可以自主發聲的音樂車,車內有10件自制樂器。在於雷的構想中,“廢話製作工廠”像一架巨型機器,有大量精密機關,互動設計讓虛構的工廠滲透進觀衆的生活空間,演出過程中,它和演員的表演一起爲觀衆提供觸手可及、感同身受的未來體驗。

《廢話製作工廠》劇照(圖 | 於雷微博@廢物研究所-寶勒爾)
如今的世界戲劇舞臺充滿紛繁的前沿技術,似乎只要資金充足,一切新材料、新科技都可以出現在劇場裏。藝術家們不斷探索創作邊界,以極快的速度一次次地刷新觀衆對舞臺藝術的認知。於雷的選擇讓人感到驚訝。他將目光對準廢舊品,作品討論的卻往往是當下乃至未來的話題。在上海戲劇學院學習舞臺美術專業四年,於雷覺得,戲劇舞臺上的佈景、道具每次都要用大量新材料製作,既佔據空間,又浪費資源。“其實把用過的東西加工一下,就是一套新的舞美。”
從上戲畢業後的幾年裏,於雷開過實體模型材料店,與好友創辦工作室“廢物研究所”,他們以“有啥用啥,說做就做”爲口號,用廢舊材料製作裝置及戲劇作品。於雷認爲,人們通常強調商品的功能性,對其內在物質性並不瞭解,當商品不再具有功能的時候,它就回到了單純的物質本身。“太好玩了,希望我們撿得開心,廢得豐富。”

於雷爲工作室設計的復古招貼畫
從模型店到“廢物研究所”
文化商廈是昔日上海藝術生的樂園。以前每逢開學季或寒暑假,這座上世紀90年代開張的商廈總是熱鬧非凡,尤其是畫材、模型、裝裱耗材類門面,往往人滿爲患。不過,和各地紅極一時、主營文化用品的專門型商場類似,近幾年,上海文化商廈日益蕭條,往遠看是因爲網絡電商的興起,從近處說,疫情對實體店的打擊還在最後支撐的店面中蔓延。
於雷模型店曾位於文化商廈二樓。2019年,他常光顧的模型材料店老闆聯繫他,問他有沒有興趣把店盤下來自己開。當時於雷剛畢業不久,帶着“凡事要好玩”的心態,他熱情地擁抱了這座已顯頹勢的商廈,將模型店視作自己在上海的陣地。門店主營舞臺設計、模型製作、復古玩具,店內空間很小,看上去像個雜貨鋪。朝向走廊的透明玻璃映出花花綠綠的貨品,玻璃上貼着卡通體大字,算是宣傳語,“真愛無坦途”,來自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

模型店一隅(圖 | 於雷微博@廢物研究所-寶勒爾)
細想起來,於雷覺得自己大概是爲玩而生的。他是內蒙古人,蒙古族,家鄉在呼倫貝爾海拉爾。在他的記憶裏,父親以前總帶着他做“亂七八糟的小手工”,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小時候喫完牛羊肉,他們總把骨頭洗乾淨攢起來,做成樂器或玩具,其樂無窮。“那會兒玩得特別瘋,都在野外,家門口全是草原。遊藝項目就是在草地上挖個坑,到坑裏做個小房子,再用土做幾把小椅子,採些野花裝飾一下。”離他家不遠的地方有一所鄂溫克民族中學,學校裏有一大片草原,原上的一條河邊有很多野果樹。“我們經常在河邊家庭聚會,夏夜裏去野餐,採野果子喫。”
童年時期,於雷幾乎沒玩過商店裏賣的商品玩具,他感覺那些東西過於精緻漂亮,不夠自由、開放,用他的話說,“不夠亂套”。帶着這樣的審美觀念,於雷模型店的商品幾乎都是淘換來或者撿來的,網購的中古玩具、街頭商鋪廢棄的舊材料、朋友從海外帶回的小衆手辦……沒什麼特別的選擇標準,“但我喜歡長得比較醜的東西”。
模型店開張後吸引了一批覆古愛好者,站三五個人就滿滿當當的店面很快就成了一個同好交流的小社區。“我在那裏認識了很多人,都聊得來,這是開店最酷的一件事。”

(圖 | 於雷微博@廢物研究所-寶勒爾)
2021年10月,於雷模型店租約到期,於雷和在模型店結識的朋友于唯一、沃德勒將共同成立於2020年的工作室“廢物研究所”正式落在一座創業園區,開始專心搞創作。儘管在此之前,他們創作的裝置及木偶已經因潮酷的視覺風格受邀參加了多個展覽,幾位成員還是決定將創作重心放在劇場,專攻木偶劇。“戲劇讓想象不受限制,木偶能把做手工和戲劇結合起來,我自己還能上臺演。”在於雷看來,舞美設計有廣闊的空間,創作者能把自己的想象呈現在觀衆面前,讓創造的樂趣被更多人分享。“真的,你要說舞臺是外太空都沒問題,你想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
作爲本能的想象力
2021年12月,廢物研究所推出的裝置偶劇《不可思議的十八相騎士》(下簡稱《十八相騎士》)在上海界界樂文化藝術中心首演。這是一部做給孩子看的木偶劇,根據我以往的兒童劇觀劇經驗,它似乎過於複雜了。
一般來說,兒童劇臺詞較少,多采用肢體語言和音樂,讓劇情便於理解。在傳達上,創作者大多會用盡可能清晰的方式表達一個明確的主題,同時爲孩子構建安全無害的觀劇環境。當然,兒童劇絕不意味着選題上的淺易或是形式上的低幼化,優秀的兒童/青少年劇場作品常能抵達成人世界難以直面的深邃議題。譬如法國阿維尼翁戲劇節前藝術總監奧利維耶·庇(Olivier Py)就常從童話故事取材,探討道德問題甚至反戰話題。

《不可思議的十八相騎士》劇照(圖 | 上海界界樂文化藝術中心)
《十八相騎士》講述的是一個懸疑推理故事。小女孩蘭妮剛剛度過她的10歲生日,因爲崇拜福爾摩斯,她的夢想是成爲一名偵探。去朋友家做客的時候,朋友的父親準備到國外參加展覽的漆畫被盜,蘭妮遇到了真正的案件,她開始調查。隨着調查的深入,她發現案件與都市傳奇“十八相騎士”有關,通過蘭妮和貓咪肥飛仔的共同努力,疑案成功破解。
作品臺詞密集,兒童觀衆必須跟上主角蘭妮的探案腳步。舞臺上遍佈大量塗鴉風格的佈景和道具,木偶角色和人物角色同臺演出,客觀上增加了理解難度。更加違反常理的是,《十八相騎士》把諸多主題或重或輕地拋擲在舞臺上。比如,美的價值是否可以用數字衡量?歷史與當下存在怎樣的聯繫?爲別人製造快樂會不會給自己帶來傷疤?友誼意味着什麼?劇中真正的竊賊十八相騎士以擅長僞裝著稱於世,但沒有人知道他本人的樣子,究竟什麼才代表一個人?自我認同和他人評價,哪一個更重要?
於雷認爲,精力旺盛的孩子眼中總有一個活潑而奇異的世界。他不相信“靈感”,在他看來,想象力是一種從孩童時代保留下來的本能。“我們的作品可能就是孩子眼中的世界,你感覺複雜因爲你是大人。孩子的眼光簡單而直接,但他們也會思考成年人視角下深刻的問題。”

於雷(左)進行操偶表演(圖 | 上海界界樂文化藝術中心)
實際上,《十八相騎士》的創作起點是一把手風琴。於雷告訴我,當工作室裏那把破舊手風琴出現在視野裏的時候,他突然有個念頭:它是不是能變形?變成一隻貓,一隻能上天入地會說話的貓。“我每天就像浸泡在材料裏,它們包圍着我,會帶我去往一個方向。”
於是,材料被於雷加工成素材,經過整理又成爲作品。這種隨性且佛系的創作方式讓他們產出效率極低,大概一年只能完成一部偶劇,因爲廢舊材料較爲脆弱,不易運輸,在戲劇商品化的時代,作品也很難高頻演出或是異地巡演。對於我的擔心,於雷像玩贏了遊戲一樣哈哈大笑。“你沒有過童年嗎?小時候沒那麼計較得失,喜歡的玩具壞了可以修補,修不了還能跟別的組合一下,變成新玩具呀!一樣的。”

(圖 | 於雷微博@廢物研究所-寶勒爾)
於雷把現在獲得的成績和機遇視作自己長不大的福利。逐漸獲得關注後,他們總能接到一些設計、展覽和製作業務,維持工作室的正常運轉。至於戲劇創作,於雷說,他們還是會繼續很用心地慢下去。“木偶承載被外化的視覺符號,是我們都經歷過的、對世界有着模糊認識時,小朋友眼中的奇幻景象。我們還是不可避免地長大了,但成長到現在,也無非是成爲一顆柔軟又剔透的果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