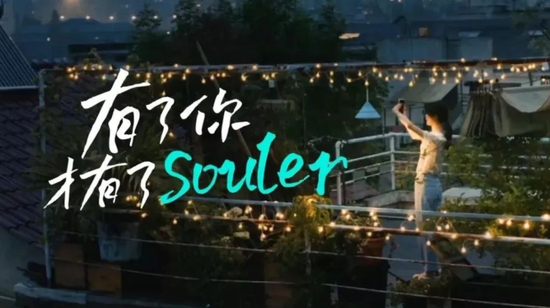Soul,趁虛而入

來源:南風窗
作者/滄南
陳曉鳴跟一個“假人”談了一場戀愛。
24歲的她,其實不太相信網戀了,但去年8月23日,她還是跟Soul App認識的一個男生定下了CP關係。
Soul,顧名思義,是一款用“靈魂”交友的軟件。畢竟,美顏氾濫的年代,再好看的臉,也有翻車的風險。
相比顏值,對內在要求高的陳曉鳴認識了一個男生,他27歲,建築學碩士畢業。他們兩人有很多共同點:對TVB新老劇如數家珍,熱愛臺灣文學、日本電影,還都渴望一種淡泊的生活。
談了一個月,男生原形畢露——動不動開黃腔,想看私處,想“嗑泡泡”。
隨後,因一起“借錢”事件,陳曉鳴的Soulmate幻想瞬間破滅了——她打電話報了警,哪有什麼建築學碩士,他的照片、名字都是假,只有一個輟學在家的“家裏蹲”,所謂借錢也不過是一場蓄謀已久的詐騙。
陳曉鳴哭笑不得,作爲一名5年的資深Souler,“以前逛Soul,可以感受靈魂的多樣性,現在,只能見識物種的多樣性”。
在她看來,Soul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
Soul上線至今6年,日活用戶近千萬。近兩年的瘋狂燒錢營銷,幫助它吸納了多樣化的用戶。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Soul平臺用戶增長水平及參與度的統計數據
隨之而來的,除了有Souler在上面找到了精神共鳴、戀愛結婚的對象,該款App仍沒能躲過“變味”的命運。
知乎問答“你爲什麼卸載了 Soul”,9000多條回答裏,有遇到騙子的,有遇到騷擾狂的,有遇到渣男的,但更多的,可以籠統概括爲“物種的多樣性”,千奇百怪。
某種程度上,這是一款社交軟件的宿命。所不同的是,Soul打着靈魂社交的旗號,把年輕人的孤獨當作生意,弱化真實信息的陌生人深度社交,魚龍混雜,各類灰色事物,趁虛而入。
靈魂的底色仍是荷爾蒙?
5年前,在浙江某高校就讀英文系的陳曉鳴,從一位豆瓣友鄰那裏聽說了Soul。
她至今記得初識這個軟件所帶給她的“喜悅”——界面是一片星空,無數光點,既像浩瀚的宇宙,又似一顆顆孤獨的靈魂,彼此連接。
這樣的意境與格調,瞬間拿捏住了陳曉鳴。

Soul App的界面
陳曉鳴設置了很多興趣標籤,點擊靈魂匹配,大數據開始爲她尋找志同道合的Souler。
而現實生活中,陳曉鳴內向,跟同學有些格格不入。沒有社團活動,她大部分時間在圖書館,讀書、看電影。因此,“Soul,其實很能抓住我們這樣的人的痛點”。
早期的Souler,以文藝青年居多,基於興趣和愛好的高質量精神交流,是他們最主要的交友需求。
Soul在2016年上線,創始人張璐曾公開表示,人們在社交平臺有除了有看臉的需求外,還有精神交流的需求。她希望“不以臉爲必要條件,而用‘圖片音樂’進行心靈匹配,給人們更多想象空間和感知能力”。
跟隨靈魂找到你——彼時的Slogan,吸引了很多陳曉鳴這樣的用戶。

Soul最初的slogan是“跟隨靈魂找到你”
沒多久,得益於Soul的靈魂匹配,陳曉鳴結識了一個她人生中很特殊的朋友——一個在廣東讀書的文學系男生,熱愛重金屬搖滾和藝術電影。她喜歡跟他交流,他的觀點、談吐,總是一次次拓寬她的認知和眼界。
陳曉鳴對鹽財經說,那時候的Soul,交友沒有那麼強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不是上來就“聊騷”,也不是“約炮”或者“搞CP”,“是純粹的靈魂交流,我們都沒想過發展男女朋友關係”。
一年後,因爲偶然因素,陳曉鳴跟這個男生都去了上海。兩人在咖啡館見了一面,聊了一下午。男生似乎對她動了心,幾天後表白,但陳曉鳴拒絕了,她更珍惜這樣一個朋友。
早期的交友軟件,是陌陌、探探們的天下。在大衆認知中,這些平臺的交友,是目的很直接的婚戀或者“約炮”。
Soul則靠着口口相傳的口碑,打開了一方小天地。
王園是2018年通過微博廣告點進Soul的。
彼時,他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在深圳一家營銷公司上班,工作很累,獨居在出租屋裏,經常夜裏感到很寂寞。所以他目的也很明確,希望交一個志同道合的女友。

那時的Soul,卻不是他想象的那樣。
Soul有一個“字母點亮功能”:隨着聊天次數增加,會積累一顆顆愛心,每3顆可點亮一個字母。王園記得,他花了5個月時間,跟一個女生點亮“Soulmate”。
“儘管戀愛沒談成,但這個過程還是很別緻。”
但是,隨着時間推移,Soul的使用體驗變得越來越複雜。
王園的使用感受並非孤例。事實上,2018年,Soul拿到了B輪融資,開始在各大平臺投放廣告,比如豆瓣、微博等。這給Soul帶來了第一輪用戶的大幅增長。

Soul融資歷史(來源:Soul港股招股書)
用戶基數增長,帶來了更復雜的社區氛圍。
王園記得,從2019年開始,Soul開始流行“磕泡泡”了,即一種語音形式的幻想性愛,在“00後”羣體中頗爲流行。
不少人的主頁裏,慢慢出現了這種色情需求的隱晦表達。這正得益於Soul上線的語音匹配功能。“磕泡泡”的隱祕現象早已有之,但語音匹配功能的出現,讓這種需求迸發出來。
王園感到失望,一個主打靈魂交友的軟件,竟然跟色情與軟色情掛上了鉤。

Soul App的語音匹配功能
2019年,有媒體報道,Soul軟件的“匿名小助手”功能裏,有着相當一些帶有軟色情的狀態、評論與私密照。因涉及色情內容、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Soul曾多次被網信辦點名批評。
2019年6月,國家網信辦發佈《國家網信辦集中開展網絡音頻專項整治》通知,要求對包括Soul在內的App下架整治。其中,Soul被牽扯上的不僅是“直白荷爾蒙社交”,更被認爲是“殺豬盤”的工具。
當私密電話成了一場直播
“00後”女孩“鯨魚”是南風窗在2021年曾報道過的案例。
那年4月,她跟另一名Souler“嗑泡泡”。
認識1個月裏,他們嗑了5、6次,通常是對方發起,語言挑逗上,對方更主動,尺度更大。慢慢地,鯨魚也被帶入其中,“解放了天性”。
但她當時並不知道,這其實是一個巨大的圈套。
鯨魚來自成都,正在讀大學。經一位朋友的介紹,她在2020年註冊了Soul。對她來說,這個軟件的吸引力,早已不是什麼靈魂社交,她是奔着語音交友而來,需求很簡單:爲了磕泡泡。

陌生人社交在中國已經走過了十幾年的歷程
茜茜是她在Soul認識的第一個人,也是唯一一個。“對方很會聊天,尤其是節奏掌握得好。”不過平臺加大了審查力度,一兩次後,她們便轉移到了QQ。
鯨魚和對方“奔現”(奔赴現實,指線下見面),對方趕到成都去找她,兩人在酒店住了一宿。聽口音,像是重慶人,也在讀大一。不過對方對自己的身份很警惕,鯨魚表示能理解。
一個月後,2021年5月份,圈子裏一位好友告訴她,在某平臺上,有人的聲音跟你很像。鯨魚認爲也許是巧合,朋友堅持讓她確認一下,給了她一個鏈接。
下載後,她發現是一個色情平臺,按朋友指示,登進去一搜。
鯨魚瞬間崩潰了。
真的是她。
此刻,她正在直播——她當着直播間數百人的面,一邊進行語音匹配,一邊介紹直播間“福利”,送足一定金額的禮物,可以獲得進羣資格,羣裏有所有“磕泡泡”的直播錄音、線下開房錄像。
很快,匹配成功,直播裏的“她”跟對方開始“聊騷”,又一個獵物上鉤了。
手機界面一晃而過,但鯨魚認得,就是Soul。
也就是說,鯨魚跟對方所有的私密通話,都是當着幾百號人的面進行。
鯨魚頓時覺得毛骨悚然,不知如何是好,憤然刪了軟件。只能安慰自己,“反正也沒人認識你”。
她並不敢找對方對質。她對鹽財經記者說,“畢竟她拿着你最羞恥的隱私,也知道你的學校”。
越想越氣不過,鯨魚重新下載了軟件,花錢混進了那個羣,反手給了一個舉報。

作爲一個老Souler,陳曉鳴也沒想到,自己居然也被騙了。
原本,工作那幾年,她已經很少登錄Soul,換了手機就沒下載回來。不過2021年6月,突發奇想,她登上了這個軟件。
爆炸的私信裏,她看到有人在她年前的一條動態裏留言,就這樣,她認識了報道開頭的男生。
但在一起才發現,男生並沒有想象中那麼美好。“他的藝術見解和觀念,談來談去,就那麼回事,你甚至覺得,他可能是對着豆瓣短評跟你聊天。”
不過當時她沒有在意。
直到2021年10月初,男生開始鋪墊了母親得乳腺癌的事情,逐漸頻繁跟她吐露自己的壓力和煩惱。到了11月,男生說自己走投無路了,10萬手術費湊不到。
言語之間,不外乎希望陳曉鳴借錢給他。
第一次,陳曉鳴主動轉了1000元過去,說是給阿姨買點營養品。不過男生胃口不在這裏,主動提出借2萬。那時候,陳曉鳴正在報考教師事業編,花了2萬多元報了個保過班;剩下的錢,都在股票裏。
2021年11月12日,她又轉了3000元過去。男生提出,能不能幫他借個貸款。陳曉鳴開始警惕起來。對方心虛了,後來就不再回消息。
陳曉鳴越想越不對。她看到對方給的病歷上,病人年齡才42歲,明顯有問題。
她報了警,警方反饋沒有這個人,名字、家庭,學歷,通通不對。網絡信息鎖定的人結果是一個大專輟學的男生,整天蹲在家裏上網,20歲出頭。

男方見驚動了警方,慌忙退了她4000元。那時陳曉鳴忙於考試,便沒有追究法律責任,“算是給自己上了一課”。
陳曉鳴這樣的,不是個案。在裁判文書網搜索“Soul”,共有90多篇判決文書,其中大部分涉及詐騙。
比如,甘肅省東鄉族自治縣人民法院一份判決顯示,2020年開始,一位姓楊的“00後”男子,就僞裝成女性,在Soul認識人發展戀愛關係,以生病住院爲由,騙了16萬,然後揮霍殆盡。
當然,Soul上面部分詐騙,並非全是個人作案,還有一些是組織化、產業化的,大多涉及殺豬盤、理財投資詐騙、刷單、裸聊等。
判決書中還展示了Soul的人間百態。
比如,有的人“奔現”,但被非法囚禁或者強姦、毆打,在男方的脅迫下拍小視頻;太原迎澤法院一份判決書中,就有一個女孩“奔現”後,被“男友”偷了手機,從支付寶、京東等平臺借貸4萬,轉走了。
單身社交的悖論
Soul,何以走到了今天這個局面?
從小而美的特色賽道起家,但它沒能逃脫野蠻生長。
2018年開始,Soul的廣告投放,越來越頻繁。在抖音、小紅書、微博,我們也時常可見Soul的宣傳語。
根據今年6月底Soul提交的港股招股書,2020年,它的廣告支出費用是6.02億元。2021年第一季度,已經達到4.59億元。2022年第一季度,Soul已經贊助了3、4檔熱門綜藝,廣告支出有增無減。

截至2021年底,Soul的銷售及營銷開支(數據來源:Soul港股招股書)
鋪天蓋地的廣告,讓Soul走出了一方小天地。2020年,月活用戶增速達到80.9%,2021年初更來到109.0%。凌晨時分,Soul的同時在線人數經常超過1000萬。#Soul崩了#這一話題甚至還衝上熱搜,大家調侃,新來的人,實在太多了。
從《演員請就位》到《追光吧哥哥》,再到《明星大偵探7》,它目標用戶越來越大衆化,自然,依靠這種方式吸納的用戶,結構上肯定更加多元、複雜。
但遺憾的是,在陳曉鳴這樣的早期用戶眼裏,就是所謂的魚龍混雜。
早先,Soul吸引的是那些孤獨的,關注自我精神世界的用戶。用陳曉鳴的話說,曾經這裏是咖啡館一樣的存在,現在卻成了喧鬧熙攘的公共廣場。
變化是明顯的。早些年,這裏不看臉,很少人發個人生活照,現在隨便匹配一個,全是A4腰、網紅臉,以至於陳曉鳴感到有些自卑。
Soul的社區氛圍,也更鼓勵一種速食社交。比如,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匹配界面添加了一個加速匹配的按鈕。這是一個付費功能。匹配有了次數限制,語音匹配每天只有三次是免費的,普通的靈魂匹配,免費額度30次。超額匹配,指定性別、指定城市的匹配,都需要額外付費。
匹配中的附加服務,還有“幫你找一個寶藏女孩”,需要支付8個Soul幣。
從商業的邏輯來講,這一點無可厚非。但這種付費邏輯,破壞了原有的社區文化,“它讓交友變成了一件非常功利的事情,交友有了成本的計算,就變味了”。
在很多早期用戶眼中,這使得Soul跟探探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而且別人還是免費的”。

事實上,所有陌生人社交的底色,都是基於慾望。這一點,無論早期的Soul,還是如今的Soul,都無出其右。
Soul創始之初,打着降低用戶孤獨感的旗號,希望走一條獨特的道路,不強制用戶展示位置,不允許用戶上傳真實頭像,只能用虛擬頭像。突出的是,不看臉,只看靈魂。
這種策略下,早期吸引的用戶,大多是文藝青年,他們的慾望,更多集中在精神與心靈層面。他們渴望聯結,可以得到他人的理解,渴望志同道合的交流。
顯然,早期的Soul,並不歡迎那些荷爾蒙的奴隸。
但是,越是深層的慾望,越難以轉化爲變現動力。同樣是文藝青年聚集的豆瓣,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
而慾望越接近生理層面,就越是暴利——色情交易是暴利,賭博是暴利,毒品也是暴利。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道理。
於是Soul似乎開始了新的轉型,淡化了靈魂社交的社區屬性,以適應新用戶的偏好——或者說慾望,引入了社交元宇宙的概念。

這本質上還是噱頭,無非是增加一些互動玩法,比如狼人殺小遊戲、類似直播間的“派對”等,藉助這些“破冰”遊戲,引導一種不那麼注重靈魂的社交氛圍。

Soul App上提供的多種遊戲化和沉浸式功能
基於此,可以說,Soul最終褪去“靈魂”的光環,變爲一個直白的相親平臺。而用戶基數的規模性、複雜性,將這一點放大了。
不看臉的文化,本質上,是真實信息的隱匿。在前面判決書中,我們已經見識過,人美聲甜的小姐姐,其實是女裝大佬;你以爲的Soulmate,也許是步步爲營的陷阱。
鹽財經記者的前同事中有一位資深的Souler,過去5年,他與Soul上面的女孩們奔現超過10次,“但次次都翻了車”。他沒有遭遇過詐騙或者女裝大佬,但在真實的顏值面前,他還是暴露了“虛僞的本性”。
但下一次,他還是樂此不疲地投入了Soul的星球。
(文中陳曉鳴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