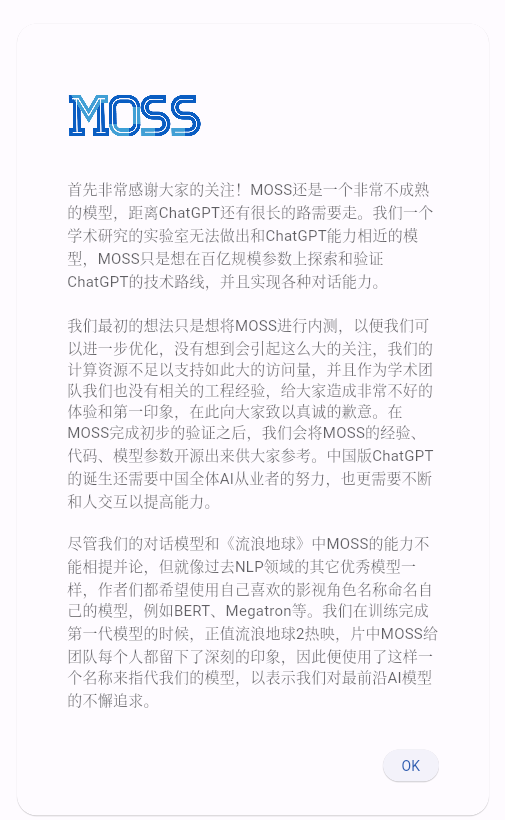愛國的全球主義,保守的未來想象:《流浪地球2》進步了嗎?
撰文 | 徐魯青
編輯 | 黃月
《流浪地球2》春節期間上映,距離《流浪地球》開創的“中國科幻電影元年”已過去四年。第一部講述了“流浪地球”計劃實施過程中途經木星遇到的危機,第二部更像是第一部的前傳,聚焦“流浪地球”計劃的緣起——太陽老化膨脹,即將吞沒太陽系,人類爲了生存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實施“數字生命”計劃,把人類意識上傳到數字世界,這一計劃後來被聯合政府禁止;另一種便是“流浪地球”計劃,即不改變人類的存在形態,讓地球逃脫太陽系。
上映超過一週,《流浪地球2》不僅在春節檔中票房佔據前列,在豆瓣上也收穫了8.2的較高分數。許多評論認爲,電影在技術、視效、科幻思考等方面遠超第一部的水準,除了宏闊的世界建構與精尖的特效水準,還加入了深層的科技哲思。

2019年2月20日,上海,南京西路大光明電影院外《流浪地球》的大幅海報。
四年前《流浪地球》上映時,除了對中國科幻電影的開拓意義,圍繞電影的主要討論還包括電影流露的“戰狼”式民族主義、人定勝天式自然觀以及人類集體至上等觀念。《流浪地球2》的價值取向並未改變,電影呈現的未來世界隨處可見高精尖的技術,但內裏的價值觀仍然傳統甚至陳舊;另一方面,在深知它們可能激起許多觀衆反感的前提下——至少在面對全球市場時——電影做出了軟化與修飾的處理,最終形成了一個遍佈罅隙與裂痕的文本。
愛國式普世主義:
電影中的國際合作想象
《流浪地球2》包含三條故事線:一條是作爲普通航天員的劉培強,先後爲了家人與人類選擇自我犧牲,完成佈設核彈的太空任務,後又被同伴拯救,返回地球;另一條線是劉德華飾演的科學家圖鴻宇,在喪女後,將女兒和自己的意識上傳至量子計算550w,在虛擬世界與女兒團聚;第三條重要故事線則展現了面對地球危機全球合作與政界決策的樣態,由李雪健飾演的“周老師”作爲中國政府的代表,在聯合國負責談判協商,最終引導“流浪地球”計劃取得成功。
與第一部相似,《流浪地球2》試圖在民族主義與人類共同體式的平等團結之間尋求平衡,對全球合作的價值理念強調得也更多,主要呈現在第三條線中周老師的臺詞表達裏,比如在月球核彈因爲各國密碼不同、無法共同引爆時,他憤怒感嘆:“人類把最精密的保密系統,都用在了自我毀滅上。”電影中出現的宇航員們膚色不同,航空服上國旗各異,在同聲翻譯技術的幫助下,他們自然地說着各國語言,但也有多個場景呈現了技術退場後各國宇航員難以理解彼此的狀況。
電影前段劉培強對劉朵朵的追求與表白,除了爲故事劇情需要而設,也作爲表現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段而存在——不同國家的宇航員文化不同,但都明白紅玫瑰作爲禮物的意義,他們一起對劉培強打趣鼓勵,暗示着語言和國族的障礙在“愛”的面前都可以消解。此外,最引觀衆落淚的場景之一要數各國均堅定派出50歲以上的宇航員出列,完成一趟有去無回的、拯救人類的任務,不同國家用各自的語言報出國名,抒情的出征配樂迴盪在俯拍全景的英雄式畫面裏。

加蓬基地劇照(圖片來源:豆瓣)
在人類共同體式的話語縫隙之處,影片處處埋藏着對國族榮耀的展示和民族主義的碎片:影片多處出現了對外國宇航員的喜劇化嘲弄,無論是白人宇航員在工作場合對劉朵朵的性騷擾調侃,還是在後來工作中的大出洋相;在太空電梯危機中,吳京與反派打鬥時飛出了一個飛船零件,上面刻着“Made in China”,零件特寫鏡頭定格在畫面正中。危機化險爲夷後,“Made in China”零件作爲戒指,和幾分鐘前還充當世界主義象徵的紅玫瑰,一同作爲表白禮物送給了劉朵朵;在地球逃脫任務的最後關頭,周老師堅持點火,激動地喊出:“我們的人一定能完成任務。”人類共同體在這一刻重新劃分了“你們”與“我們”,對於“我們的人”的絕對相信,成爲電影中人類取得勝利的最關鍵理由。
在《末日時代的新天下秩序:<流浪地球>與新大國敘事》一文中,廣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蓋琪指出,90年代以後,文化產品中的民族主義敘事主要呈現爲“受辱-雪恥型”話語面貌,然而這類敘事越來越容易引發觀點撕裂。以2017年春節檔熱門影片《戰狼2》爲例,雖然票房可觀,但其內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面對非洲人的居高臨下以及強烈的敵我意識,都在公共輿論引發了強烈反感。
蓋琪發現,近幾年,一種更注重兼容性的“新大國敘事”範式出現,注重平衡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她從《流浪地球》中指認出了這類“新天下”話語傾向的價值表達——“天下”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近十餘年來被諸多學者頻頻回望並延展出新的價值內涵,其中頗有影響力的是中國社科院哲學教授趙汀陽提出的 “新天下體系”。

擦肩而過的劉培強與圖鴻宇(圖片來源:豆瓣)
在趙汀陽的設想裏,“新天下體系”基於全世界的共享利益,涉及人類集體命運的事務歸世界主權的管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係教授柯嵐安認爲, “新天下體系”將看似矛盾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話語結合了起來。《流浪地球》恰是這類相異理念的揉雜產物——在大框架上,這是一個面對外部威脅,倡導各國放下芥蒂、共同合作的故事,流露出世界主義色彩;另一方面,電影文本的細節裂縫中又隨處可見民族主義的碎片。至於如何防止“世界主權”的異化、如何設計權力制約機制,“新天下體系”的設想懸置了這些問題。
有意思的是,“世界主權的異化”在劉慈欣《流浪地球》原著中得到了更詳盡的描繪。爲了長達兩千五百年、跨越一百代人的“流浪地球”計劃得以順利實施,“聯合政府”成立,擁有高度集中與深入的權力,不僅可以執行進入地下城的抽籤,劃分35億存活者與35億被犧牲者,還可以通過《流浪地球法》徵召所有人類爲全球公共服務勞動。小說中的反烏托邦構想與反思並未在電影改編中出現,“聯合政府”統領的世界具體如何運行?普通人的生活是什麼樣的?在兩部電影中,這些思考僅作爲粗略的背景被一筆帶過。
繁衍執念與“人定勝天”:
延續人類中心主義自戀
根據《流浪地球》的設定,爲了躲避一百年後太陽的氦閃,“聯合政府”實施了跨時2500年的“流浪地球”計劃,啓動地球推進器的代價是一半人口的死亡。這一背景以冷靜的畫外音呈現,電影沒有在可能引發的倫理兩難問題上做出任何停留,縱使距離太陽氦閃還有一百年的時間。如果將所有資源投入地下城的建設,不是實施流浪地球計劃,作爲代價的三十五億人口大多都不用死去,而計劃指向的2500年後的人類安危,也大大超過了普通人的共情範圍。
《流浪地球2》中人類的最大分歧,是“數字生命派”與“流浪地球派”之爭。前者提倡將人的意識上傳至數字世界,後者則要求保全“地球家園”,二者最根本的分歧不只是放棄還是保衛地球,更在於對生命本身的理解——正如科學家圖鴻宇同馬老師數次爭吵的核心:只有數字化意識,沒有實體的女兒丫丫,到底是不是活着?
這不僅僅是圖鴻宇的故事線,也是諸多經典科幻電影嘗試探索的問題:沒有實體形態卻擁有自主意識的存在是生命嗎?身體是生的必要條件嗎?在結尾彩蛋處,主機MOSS對稱自己已死的圖鴻宇說:“對於‘已經’和‘死’的定義,有一點點和你不同的看法。”
然而,這些更具突破性的哲思嘗試被電影中文明傳承的使命感蓋了過去,無論是劉培強見到劉朵朵第一眼馬上幻想婚後手裏抱的孩子,還是馬老師的臺詞:“沒有人的文明,毫無意義”(在第一部中,吳京也說過這句話),以及周老師在動員演講時,號召大家相信選擇“流浪地球”計劃,堅定說出“我信,我的孩子會信,孩子的孩子會信”,這句話也對應了劉培強的臺詞:“沒事,我們還有孩子,孩子的孩子還有孩子。”縱使計劃橫跨了2500年,孩子的孩子已經展望到100代之後。在這些箴言式臺詞與抒情演講裏,電影探討的焦點從後人類的思索維度——何以爲人?何以爲死?——再次退回了人類傳承,抑或“人類文明的延續”的執念裏。

2020年1月7日,四川成都。《流浪地球》電影主題展在四川科技館展出,展覽展出劉啓地表防護服、張小強軍用防護服、李一一地表防護服等
人們的行動目的不是自身,是後代與人類;不爲此刻,爲未來與千年。自願犧牲的年輕人被要求退後,軍隊命令五十歲以上的老人出列,承擔有去無回的引爆任務。在視聽語言製造的抒情氛圍中,一個電車難題被化解爲一場感天動地、理所應當的犧牲,生命的功利主義計算成爲了無需懷疑的倫理準則。即使之前電影着重刻畫了劉培強爲家人進入地下城、應聘宇航員的場景:負責考覈他的550W通過計算,測出了他的最優選擇是放棄妻子的生命,人工智能的建議激起了劉培強的情緒失控。這段場景意圖以人類真情反襯人工智能的冰冷,而實際上,諸多人類行動沿用的也是同一個功利準則。
另一處顯見的觀念裂痕體現在,電影一方面強調對地球的家園情懷,另一方面人定勝天的思維又貫穿全片。周老師在面對美國對“流浪地球”計劃的質疑時,翻出了宇航員曾經拍下的衛星圖片,看着小小的地球,動情地說“這是我們的家園”。在他表達的未來願景裏,多次出現的臺詞是“看到藍天,鮮花掛滿枝頭”的生態性想象。與之矛盾的是,電影中流露的自然觀是人定勝天式的,很難讓人感受到對待地球家園有何溫情。“流浪地球”計劃的原名“移山計劃”,對應着愚公移山這個承載着“人定勝天”理念的中國古代傳說;故事設定從用核彈炸燬月亮,到通過發動機駕駛地球,都顯露出了對於控制自然的樂觀且強硬的態度;當人類用數億顆核彈炸燬月亮時,電影響起了恢宏低沉的配樂,流露的不是破壞宇宙秩序時的敬畏,也並非對人類犧牲者的致敬,而更多沉浸於人類偉大精神的感動裏,慶祝又一次對自然的勝利。

電影中頻頻出現的聯合國總部大廈(圖片來源:豆瓣)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師林品在《太空幕布上的家國天下》中對《流浪地球1》做出的評價,四年後用在第二部中也頗爲適當。他提到,劉慈欣曾說科幻文學最重要的意義是讓人類認清自身的渺小——“不是征服者,甚至不是手下敗將,而是‘宇宙角落中一粒沙子上的微不足道的細菌’。然而,電影《流浪地球》卻重複着人類的自戀——父子情深、保家衛國、人定勝天等。”在林品看來,電影呈現出的是一個保守陳舊的科幻故事,在這一前提下,“人類可以選擇的道路就很少了:或將崇拜技術,或將崇拜人類,或將崇拜作爲整體的人類與技術的結合體——龐大的、渾身機甲的利維坦。”
儘管《流浪地球2》出現了許多對上一部理念的修飾嘗試,但文本的縫隙之間仍泄露了其內核不變的保守陳舊。好的科幻作品或許不是勸服我們相信什麼——不管是人定勝天的必勝決心,還是對人類文明、國族信仰的堅定熱枕——而更可能是動搖我們固守的價值信念,超越久未反思的視角邊界,讓我們看到宇宙如茫茫沙漠,人類如一粒塵煙。
參考資料:
蓋琪. “末日時代的新天下秩序:《流浪地球》與新大國敘事.” 探索與爭鳴 3(2019):10.
http://rdbk1.ynlib.cn:6251/Qk/Paper/696646#anchorList
太空幕布上的家國天下——《流浪地球》與民族主義話語的對接.“ 文化研究 3(2019):13.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19440g80wq2b0jk07b570rt0fe439745&site=xueshu_se
《流浪地球》的政治想象:以“人類”名義要求“人”的犧牲 澎湃思想市場
https://mp.weixin.qq.com/s/jUj66LKYNNoXfEwDkEqs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