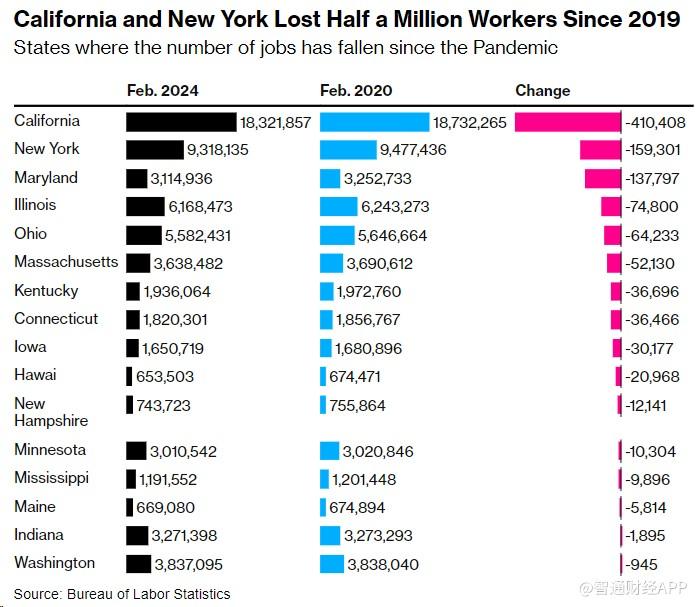專訪劉俏:當前財政政策空間仍較大,可在統籌考慮前提下用國債置換地方債

提振需求、擴大消費已成爲當前經濟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近期多部委聯合出臺多項宏觀政策,加力促消費、擴內需、暢通經濟循環。
總需求不足的核心原因是什麼?如何暢通生產到消費的經濟循環?宏觀政策又要如何加力?
8月2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圍繞上述話題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
劉俏表示,當前經濟恢復短期需要依靠財政政策通過轉移支付直達需求端,而宏觀政策也要考慮跨週期調節的遠期目標。要加大向關鍵節點領域進行超前的部署、大規模的投融資,要向基礎科研領域加大投資力度,從而維持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增長。
劉俏認爲,我國當前還擁有較大的財政政策空間,可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提高債務水平。可發行30年期甚至50年期的超長期國債、可通過轉移支付機制爲社會最低收入人羣直接進行收入補貼。此外還要推動戶籍制度、社保制度、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改革,讓常住人口、農業轉移人口成爲城市戶籍人口,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
對於化解地方債問題,劉俏贊同在統籌考慮的前提下用中央政府債務置換地方債,他表示:“此時要考慮的第一性問題不是道德風險,而是‘激活經濟運行,修復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逐漸恢復地方政府償債能力’。”
新舊動能轉換正在加快推進
澎湃新聞:需求收縮、消費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總需求不足的核心原因是什麼?
劉俏:經濟總需求不足至少有以下幾個因素:
首先是疫情帶來的疤痕效應還未完全消退。當前疫情防控工作已經平穩轉段,但疫情對企業和家庭帶來的衝擊還需要一些時間恢復。
其次是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質量下降。在中國居民的財富構成中,住房資產佔據了約60%的份額,疫情期間全國二手房價格平均下降了近20%,這也就意味着居民家庭財富遭遇了減值,特別是很多三四線城市的房價降幅並不低。居民財富有所減損就一定會降低消費能力,同樣也會對消費意願、消費信心帶來很大影響。
再者,市場對未來預期不穩、信心不足也影響了內需擴大。疫情三年來我國GDP平均增速只有4.5%,低於預期的潛在增長率,這對企業資產負債表帶來了不利影響。1.6億個市場主體很大一部分是中小微經營者,他們這幾年的生存情況並不理想。近期,光華管理學院張曉波老師正進行一項樣本量超過5萬家中小微企業的抽樣調查研究,目前完成調查的中小微企業經營者對下半年的預期不太樂觀。
此外,近年來我國的外部環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外部需求有所下降。西方國家實行的“去風險化”戰略也導致了我國出口再次面臨很大壓力,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也正在出現一些結構性變化。這些都對我國的進出口貿易帶來了一定影響,特別是今年上半年,我國的出口增速表現並不盡如人意。
澎湃新聞:從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看,當前我國物價持續走低,但總體失業率維持相對穩定,進出口、社零、規上工業增加值等都在同比恢復增長,但需求端爲何沒能實現持續性的、更大力度的反彈?當前面臨的需求問題,主要是週期性使然還是特殊因素導致的?
劉俏:當前總需求不足呈現結構性分化的特點,在有些領域尤其脆弱,供給與需求之間錯配還在加劇。我們通過調查瞭解到,當前微觀基礎層面的情況與宏觀趨勢層面之間產生了一定的脫節和背離。
衡量需求主要看有效需求,是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受多重因素影響,很多人這幾年沒有能夠實現預期收入增長,對未來經濟預期相對負面,自然消費能力與消費意願都會受到影響,這在供給端就體現爲“生產過剩”。
通常大家習慣於用“三駕馬車”去衡量經濟增長,但從學理上看,消費、投資、外貿等指標都屬於內生變量,會受其他經濟變量的影響,用這些指標分析經濟問題往往不能剖析到最本質的原因。
剛剛談到了疫情的疤痕效應、居民與企業資產負債表受損、外需減弱等等因素,而在這些連鎖衝擊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中國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舊動能轉換正在加快推進。
根據索羅模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是推進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當一個國家完成了工業化進程,就很難繼續保持很高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要保持中國經濟健康穩定發展,要實現中長期經濟發展目標,應對TFP增速下降,就必須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在要素投入領域,勞動力要從提高數量轉變爲提高質量,而資本投入則需要找到新的節點行業作爲增長點。
當前傳統動能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正在減弱,而尋找並推動新動能崛起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經濟增長壓力越大,就越需要把過去發展過程中識別出來的一系列階段性問題解決掉,把宏觀政策發力點所錨定的變量,從短期的簡單增長目標轉換成中長期國家經濟核心增長力領域,這樣才能實現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
“再工業化”、 “新基建”、“碳中和”等基礎核心行業領域,都可能成爲新動能的節點行業和上游領域,成爲TFP增速的來源。然而,這些行業的發展不僅需要時間,同樣也需要巨量投資推動,保持投資強度非常重要。然而,當前整個市場的信心不足,對這些關鍵領域的超前投資也缺乏動力和意願。
刺激一定要直達需求端
澎湃新聞:您怎麼評價過去幾年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加大投資的政策顯效週期有多長?通過投資能解決當前經濟面臨的困境麼?
劉俏:當前經濟依然面臨三重壓力,特別是需求收縮超出此前預期,這與投資不足是有關係的。比如房地產投資下滑,其所延伸的上下游產業也會產生連鎖反應,投資不足就會導致需求不足,進而導致資產負債表趨於惡化,最終加劇了對未來的負面預期。
談及投資,我們總將目光侷限在幾個特定領域裏,主要是固定資產投資。但在我的理解中,投資是個相對廣義的概念,比如對人力資本、對科研、對公共服務體系等等的支持都可以視爲投資,而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工程基建。投資的產業鏈領域越長,對經濟所能起到的帶動作用就越大。
面向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要求,當前我們需要投資一些新動能的產業,來填補包括房地產在內的傳統動能的下滑。因此,我一直建議要加大向關鍵節點領域進行超前的部署、大規模的投融資,要向基礎科研領域加大投資力度,投資強度至少要達到能抵消傳統動能退坡的量級。
如果單從商業價值看,可能一些人會認爲投資回報太低了,可能民營資本對這些領域沒有信心、暫時沒有商業回報模式,這就要求政府主導的公共資本去推動,同時也要給民營企業留出公平進入這些領域的機會。要建立一個公平的評估體系,除了考慮商業價值,也要考慮社會價值。這也對地方政府官員的考覈機制提出了改革目標,一方面要建立長週期、跨週期的考覈,另一方面要針對不同情況建立相應的約束和激勵機制。
對於新能源、人工智能(AI)、大數據、大國工業等等可能成爲節點的行業加大投資,再改善營商環境,提升民營企業信心,讓那些具有企業家精神、企業家才幹的人在這些行業創新發展。
但從短期內拉動經濟回升的角度看,這些投資的邊際作用可能會比較弱,可以說指望這些投資拉動經濟的效果不會特別顯著,所以短期還是需要依靠財政政策。刺激一定要直達需求端。
可以適當擴大政府債務率
澎湃新聞:在宏觀政策層面,您怎麼看當前提振需求、刺激消費的各項政策措施?除了現行的政策外,您還有什麼建議?
劉俏:對於當前的政策措施我可能會有三點擔心:第一,是否已經很充分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第二,面對新動能,政策路徑是否還會侷限在以前的思維框架模式裏?第三,面對當前問題,政策實施是否還會猶豫不決?
我認爲現在決策部門一定要轉換政策思維方式,現在已經到了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節點,需要儘快推進一系列滯後已久的結構性改革。而對於短期的宏觀政策,關鍵在於讓經濟能夠重新恢復到正常的循環中,其中有很多可以產生很好效果的政策工具。
比如,可以適當擴大政府債務率,可以更大力度增加長期國債或者特別國債發行。適當擴大國債規模,推行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非常大,可以考慮發行30年、40年甚至50年的超長期國債、特別國債等。當前我國居民流動性財富總量約爲200萬億元,其中在資本市場的約80萬億元,其餘120萬億元都以不同形式的儲蓄存在。如果能將其中一部分財富用長期國債等方式置換出來,給一個相對合理的利率,以中國的政府信用水平,是可以獲得很巨量的財政政策空間的。
今年初美國聯邦政府就已經觸及了31.4萬億美元的法定舉債上限。2022財年末,美國國債上限規模佔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百分比已飆升至125%。而相比之下,我國的債務率並不高。財政部數據顯示,2022年末我國中央財政國債餘額與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共計60.93萬億元,假設再加上30萬億可能的城投債、隱性債,相比於2022年121萬億元的GDP總量來說,債務率也不足75%,還有充足的發債空間。
可以適當增加財政赤字率。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赤字率擬按3%安排,如果擴大一些赤字空間,增加GDP的5%的財政投入,總計6萬億元左右,就能解決好多問題,比如在統籌考慮的前提下可以用中央政府債務置換地方債。
澎湃新聞:關於化解地方債問題,中央政府是否要下場的爭論非常激烈,一邊可能產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另一邊可能產生的道德風險。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劉俏:現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比較嚴峻,此時要考慮的第一性問題不是道德風險,而是激活經濟運行,修復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逐漸恢復地方政府償債能力。
中央債務置換地方債要有所區別,地方債中有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拖欠企業的經營性賬款。如果讓企業持續負債經營,會降低企業的投資信心。像這種經營性的地方債務就應該大膽置換。讓很多企業活下去,激活經濟運行的循環。
如何提振消費
澎湃新聞: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快速推進城市化帶來了農村轉移勞動力和新市民消費羣體,也成爲推動內需擴大的重要力量。然而當前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65%,已經進入城鎮化全面減速階段。中國的城鎮化還有多大空間?您怎麼看城鎮化紅利減退對內需的影響?
劉俏:城鎮化進入減速階段或許是個僞命題,因爲當前我國的城鎮化率超過65%是按照常住人口來計算的,而如果以戶籍人口來計算,這部分的比例就還只有47%,二者之間有18個百分點的差距。未來中國推進城鎮化,必須要解決兩種城鎮化率指標統計口徑的差異,這涉及近2.5億人在城市的生存和發展問題。
有研究顯示,不擁有戶籍的居民,其自身的身份認知是非常敏感的。在對身份敏感的過程中,他的經濟決策會趨於保守,對消費的影響是巨大的,對於沒有戶籍的居民而言,往往不能平等地得到公共服務,這種情況下消費意願往往較低,消費能力也無法得到充分釋放。
我國的農業從業人口數量佔總人口數量約24%,但只貢獻了不到8%的GDP,到2035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之後,基本上農業在GDP佔比會降到3%-4%,而農業從業人口則可能只有總就業人口的5%-6%,這就意味着未來15年,將會有近1.5億人發生跨地區、跨行業的重新配置。
讓在城市常住但無戶籍的2.5億人與未來從農業轉移的1.5億人在城市待下來,那麼他們將帶來可觀的消費,也會由於人的聚集而產生很多需求。當前中國需要真正在制度層面改革,從而消除對這4億人的軟硬性約束——比如戶籍制度改革,比如社保和公積金制度改革,比如保障性租賃住房政策等等。
澎湃新聞:從域外經驗看,伴隨着經濟社會結構轉型、人口老齡化加劇,一些國家和地區進入了“低慾望社會”模式,需求明顯下滑。與此同時,隨着國民收入提高,邊際消費傾向也在遞減。我國是否也面臨這種因素的影響?擴大消費的空間還有多大?
劉俏:兩年前,光華研究團隊曾經做過經濟學模型測算,到2035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規模可能要在總人口中的比重達到23%,幾乎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老人。而2035年我們預期的人均購買力水平大約是日本2004年的水平,那時日本的老齡化率是14%。這兩年隨着生育等數據更新,似乎老齡化的速度還有加快的趨勢,這是個蠻嚴重的問題。
但我並不認爲我國會進入“低慾望社會”,因爲目前收入水平還是太低了,還有很多人沒有被基本的公共服務覆蓋,他們被壓抑的需求其實有很多。比如,14億中國人中,有多少沒有護照,有多少沒坐過高鐵、飛機,有多少一輩子沒出過自己的城市,這些不是“低慾望”造成的,相反我更擔心無法滿足人們需求而帶來的社會問題。
澎湃新聞:疫情期間,您曾多次呼籲政府要發消費券、甚至可以考慮發錢。當前有效需求不足延續,您是否還建議財政通過“發錢”來提振消費?
劉俏:長期以來,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只佔GDP的43%,居民消費佔GDP比重約38%,而美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能達到65%以上。居民消費佔GDP比重更是高達70%。
要支持需求改善,長期來看要改變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而要短期見效則必須採用轉移支付直達需求端的方式,發消費券、發現金都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有約2.8億人年收入不足8400元。如果採用財政直達機制,給2.8億人每人每年補貼1萬元,將年收入從8400元提升至18400元,相當於月收入從700元提升至1500元。我相信大部分人會把這些錢用於消費,可以預見,很多此前長期沒能滿足的剛性需求可以在財政轉移支付之後得到釋放。比如,從每月喫一次肉變成每週喫一次肉。
可能會有人擔心給貧困人口發錢會面臨交易費用陷阱、面臨基層治理能力水平的問題。其實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觸達機制,疫情期間的健康碼都能推廣,現在或許可以集成數字人民幣功能,讓健康碼發揮餘熱。
2.8億低收入羣體每人補貼一萬元就是2.8萬億元,如果這些資金全部用於消費,相當於增加了7%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而消費又佔中國GDP的60%,也就是能實現4.2個百分點的GDP增長。2.8萬億可以從財政赤字來,通過發行發放國債、特別國債獲得資金等等。
此外,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佔比只佔到GDP的4%,遠低於美國16%的水平,提高資本市場、銀行理財等金融服務水平也是改善居民收入的一個重要渠道。
還需要再次強調,我們宏觀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制定的思維方式需要轉變。
一方面要充分認識財政政策的空間。應將宏觀政策錨定爲我國的整體價值而非GDP,這將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積極實施提供更爲開闊的空間。
另一方面,我們的宏觀政策目標除了要解決短期問題,還要服務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跨週期長遠目標,這就要求推動節點領域投資,加速新舊動能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