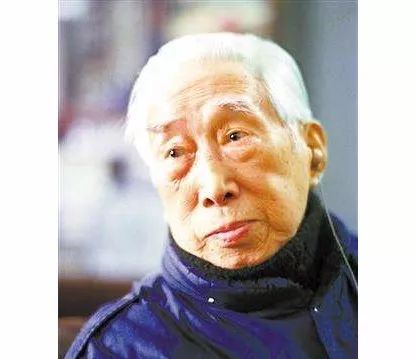那些年,我们做过的家务劳动
摘要:爹爹有辰光讲闲话下巴没有脱牢(意思“胡说八道”),他打量着我帮他擦得敞敞亮的皮鞋,会讲,“阿拉大伟本事大了,将来不怕没有饭吃了,寻勿着生活,擦擦皮鞋总可以的。我们小辰光作业只有一点点,一做就做完了,姆妈看我们小囡闲着,就叫我们帮她做家务,什么家务都让我们兄妹俩学着做,只有两桩事体不许,一桩是爬高揩玻璃窗,一桩是动刀切小菜。
原标题:那些年,我们做过的家务劳动
记得老底子唱过一首儿歌,“我有一双勤劳的手,样样事情都会做”。我们小辰光作业只有一点点,一做就做完了,姆妈看我们小囡闲着,就叫我们帮她做家务,什么家务都让我们兄妹俩学着做,只有两桩事体不许,一桩是爬高揩玻璃窗,一桩是动刀切小菜。
现在回想起小辰光我们做过的家务劳动,仍旧觉得就在眼面前。
【生煤球炉子】
要是问我,侬小辰光最讨厌的家务劳动是啥?我想也覅想就告诉侬:生煤球炉子。在没有使用煤气之前,对阿拉小鬼头来讲,生煤球炉真是件叫人头疼的家务劳动。姆妈下班晚,生炉子通常是我们兄妹俩的事。要晓得用点燃了的申报纸把柴爿点着,柴爿再把煤球点着,实在有难度。特别是到了黄梅天,柴爿潮湿,要烧脱好几张申报纸才能点着柴爿。有辰光看上去明明点着了,煤球压上去,一歇歇功夫,火又喑脱(熄灭)了。唔没办法,只好重新来过,用火钳把一只只煤球搛出来,重新点着申报纸,点着柴爿,加煤球。一把破蒲扇,“哗啦哗啦”拼老命扇,厨房间里的烟,弄得眼泪水嗒嗒滴,面孔龌龊得像只野狐脸。
劈柴爿是件力气活,爹爹包揽的。他用一把卷了口的旧切菜刀,在水门汀上哼吱哼吱的劈,劈得汗嗒嗒滴,交关吃力。把劈好的柴爿放在煤球箱旁,堆得整整齐齐,好像大饼配油条。我至今还勿晓得,爹爹是从啥地方弄来的旧木头?煤球店里有卖煤球煤饼,可从来没有看到过卖柴爿。爹爹看我们兄妹俩生煤球炉子困难,便请隔壁的铜匠师傅用洋铁皮敲了只小烟囱。小烟囱下大上小,往点着的煤球炉子上一放,刚才还死样怪气的火星,一歇歇功夫就呼呼燃烧起来。后来才晓得这是力学里的“拔风”原理。自从有了小烟囱之后,生煤球炉子的家务活就不再使我们烦难了。
买煤球也是件吃人的家务劳动,当然依然是爹爹负责。开始时爹爹借了小推车到煤球店去拉煤球,后来听说出点钞票可以叫煤球店里的工人送,爹爹就不再自己推了。送煤球的工人面孔墨墨黑,挂在头颈里的一条毛巾也墨墨黑。我们班级有个同学的爸爸是煤球店送煤球的工人,他说他爸吐出来的痰也是黑的。那辰光上海人都交关节约,煤球箱角落头碎落的煤屑,没有烧透的煤球,敲掉外面枯黄色的灰,里面黑色的煤核,敲敲碎,拌上水,可以搓成一只只煤球。侬经常可以看到地面上晒着的一只只自制的煤球。还有,拿烧过的煤球灰擦钢精锅子(铝锅),也是件蛮吃力的生活。我们力气小,钢精锅子擦不干净,姆妈就自己来擦。
记得后来爹爹把煤球炉换成了煤饼炉。用煤饼炉的好处是,晚上侬只需把炉子的风门关小一点,留一条缝,第二天早晨再打开风门,炉子里的煤饼就会“死灰复燃”。用了煤饼炉子以后,就不再做煤球了。
据史料记载,上海最早引进煤气是为了照明,150多年前6个英国商人向租借工部局写信,要求把英国的煤气引进上海,得到允许。他们用招股的方法募集到10万两白银,在今天的苏州河南岸、西藏中路以西的位置建成了上海最早的煤气厂。不过煤气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是解放以后的事了。1960年代初,上海的工人新村开始大面积安装煤气。我家就是那个辰光装的煤气。记得开始一二个月还没有装煤气表的辰光,按每家人家的人头算,一个人一个月0.80元,装了煤气表后是每个字0.07元。资料显示,到1966年上海100户人家中,能用上煤气的人家还不到6家。
【淘米烧夜饭】
“淘米烧夜饭,侬吃几碗饭?两碗饭。侬吃几碗饭?三碗饭……”
生好煤球炉子,淘米烧夜饭也是我们兄妹俩的事体。淘米这生活简单,你淘得清爽不清爽也吃不出来。可烧饭就不简单了。首先加多少水就得凭经验了,而这经验的取得,是以N次夹生饭、烂饭为代价的。同样是米,籼米涨性足,大米涨性差。如果米和水的比例掌握不好,烧出来的饭不是夹生饭,就是烂饭(只好再放些开水烧成泡饭或是粥了)。另外不同品种的大米和籼米,涨性也都是不一样的。记得那些年买大米、籼米和面粉都是有一定的比例。大米配给得少,每次烧饭都是籼米里掺点大米,这就更加增加了加水的难度。饭烧好后还要用小火焖饭(用一块中间带孔的盖板盖在炉口以阻隔火力)。如果这辰光火候控制有误,也会出现夹生饭或把饭烧焦的窘相。
那辰光由于人们吃的油水少,饭量吓得煞人,我见过好几个一顿吃一斤米的人,勿晓得他们哪来这么多的粮票?记得我的同事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评论,批评“饭吃三碗,闲事不管”现象。可见“饭吃三碗”是当年的常态。那些年很少有人吃完一碗饭不再添饭的,个别“大小姐”只吃一碗饭,背后还要被人议论,“细气点啥呀?”
现在家家户户都用电饭煲,淘米烧夜饭都不算啥事;不过要是加水比例不对,照样会烧出夹生饭或烂饭来。
【拣菜剥蚕豆揉面粉】
现在菜场里卖出来的蔬菜都是净菜,是经过菜农整理过一遍,把老黄叶子等统统去掉,有的还洗得清清爽爽。而我们小辰光,姆妈下班晚,常常从小菜场里买回来的落脚货,乱糟糟、脏兮兮的菜,非得拣一遍不可。据说有个统计,当时每10车蔬菜从郊区拉进城,就有2车菜皮再运回郊区喂猪或做肥料,一来一去要浪费多少运输成本啊。现在超市里一只辣椒、两根茄子装一只盒子,似乎有点过分细巧了。
当年一般家里有小囡的,拣菜的生活好多都有小囡来承担。我向来动作快,一歇歇功夫就把菜拣了一遍,将泥块、野草、老菜皮、黄叶子拣清爽,颇有一种成就感。拣黄豆、绿豆、芝麻,也是一件有趣的生活,我眼睛尖。还有剥毛豆、剥蚕豆,也蛮有趣。在剥好的蚕豆中部拉一条线,剥去下半部的豆皮,眼前便出现了一个戴钢盔的美国兵的脑袋,没去皮的部分是钢盔,露出的豆芽是美国兵的鹰钩鼻子,哈哈!我们一家门都喜欢吃蚕豆,蚕豆上市的日脚,天天吃葱油蚕豆,一人一小碗一小碗的吃。姆妈讲,蚕豆上市的日脚短,要吃就抓紧吃,她买小菜几乎天天要买蚕豆,所以我们家里剥蚕豆的生活,必须人人动手。剥蚕豆比剥毛豆便当,蚕豆大呀,缺点就是会把手弄得墨墨黑。
我常常与妹妹比谁剥得好、剥得快。为了剥豆方便,我右手的大拇指指甲总是留得长长的,所以遭到校门口检查卫生的值日生的指责(值日生在校门口检查每一个学生是不是带手帕、是不是剪指甲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有一趟我被一名“严格执法”的值日生拖到老师那里,我申辩,帮大人剥蚕豆,错在哪里?老师来了个折中判决,“你热爱家务劳动是好的,但以后指甲不要留得过长”。蚕豆吃着吃着就老了,姆妈就叫我们去皮剥成豆瓣,烧成咸菜豆瓣酥也蛮好吃的。
那些年买米除了要购粮证和粮票之外,每家人家的米和面都有计划的,按一定比例购买,至于糯米只有春节期间才计划供应。还有,考究的人家,买来的米都要拣一遍,把混在里面的泥粒、小石子拣出来。我喜欢拣米(还有赤豆、绿豆),就像有种人喜欢给人家掏耳屎一样。当然我特别喜欢揉面粉,虽然我们南方人不喜欢面食,也翻不出各种花式,吃来吃去是蒸馒头、烧面疙瘩。
我虽然不喜欢吃馒头、吃面疙瘩,不过揉面粉常常自告奋勇。把面粉倒进面盆里,加上水,然后开始揉,慢慢的,揉成胖乎乎的一团。侬可以像打拳击一样,面对一个胖子,任意挥拳,砰砰砰,扎劲。有辰光我会把多下来的面团做只小兔子,用两粒赤豆嵌在兔子脑袋的两侧当眼睛,一起放进蒸笼里蒸,邪气有趣。揉完面粉,鼻头上沾上面粉,镜子里的我,像京戏里的曹操,坏人,奸臣,交关有趣。
其实剁肉糜更扎劲,可是我小辰光姆妈一直不准我动切菜刀,我只能在一旁看爹爹“噔噔噔”地斩砧墩板上的肉,看着怎么从肉粒剁成肉糜,一歇歇“米”字形,一歇歇“井”字形。有辰光姆妈从小菜场买来螺蛳,用尖头钳轧螺蛳屁股的活,姆妈倒是同意的。姆妈不让我动切菜刀而允许我用尖头钳轧螺蛳屁股,这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拎清。
我经常发现,只要把家务劳动跟游戏结合在一起,自己就不会觉得厌气,就会觉得好玩、有趣,辰光也过得快。
【汏碗轮值制】
家里的菜都是姆妈烧的。我跟妹妹负责汏碗,一三五,我汏;二四六,妹妹汏;留个礼拜天,让爹爹汏。兄妹俩“两人转”,有辰光会羡慕子女多的人家,阿大阿二阿三阿四……有阿七头的人家,一个礼拜才轮到一次。
汏碗,姿势要准确,否则肚皮上、袖子管里,水溅得嗒嗒滴。姆妈教阿拉汏碗的标准姿势,“肚皮不要挺起来,要收缩。看,这个样子。”我说,那不是《三毛学生意》里的三毛学剃头,师傅教三毛要“挺胸吸肚子”。姆妈讲,“一眼(一点)勿错!”一家门哈哈大笑起来。
那辰光洗油腻的碗筷,先是用淘米水浸一歇,这样就好洗一些了。热天洗碗还方便,到了冷天,不当心手里一滑,常会敲坏碗盏、调羹。不过后来有了洗洁精,有了热水器,洗碗不算件事。至今家里餐后洗碗,我总揽在手里,从不推诿。
【拷酱油】
“打酱油”如今成为流行词,也远离本意。不过想当年,哪一家小囡唔没去帮家长拷过酱油?拎着空瓶拷酱油,酱油分红酱油、鲜酱油(辣酱油不能零拷,只能买整瓶装的)。红酱油2角4分1斤,维持了几乎我的整个学生时代。酱园店里除了卖酱油、生油、豆油,还卖酱菜(各式各样的品种好多),还可以拷花生酱、豆瓣酱。有辰光姆妈会特别关照,在豆瓣酱里再加1分钱辣火酱,回来烧八宝辣酱。一砂锅八宝辣酱,可以吃一个礼拜。
我出门去拷酱油,如果姆妈等着烧菜要用,一般都来不及。为啥?拷酱油的来回路上,我都会乘机在外面兜一兜,看看弄堂口人家下象棋(往往看大不懂)、下军棋(可以帮助指点)、下五子棋(这是我的强项)。有辰光看人家吵相骂也会看上半天。至于拷酱油勿当心敲碎玻璃瓶或是丢了钞票的事,也屡有发生。记忆中出过这样一个洋相:有一趟家里有人客(客人)要来,姆妈烧菜前发现油瓶里的油不多了,就叫我拿只空瓶去拷斤生油(花生油),并且勒令不许在外面兜圈子。我急匆匆拿了只空油瓶,快去快来,一歇歇就完成了交办任务。
这天姆妈烧了好几只好小菜,一桌人坐下来,吃吃这只菜,说是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吃吃另一只菜,也说有种怪味道。寻了半天原因,姆妈突然发现是油的问题。原来我拿的是一只拷过火油的油瓶(烧暖锅用的是火油)。火油哪能吃到肚皮里去?不过此刻桌上的菜肴已消灭大半。待大家知道怪味道的原因,一个个都拔直喉咙,想吐哪里吐得出来?
【从汏绢头开始】
我汏衣裳是从汏绢头开始的。
四五岁的辰光,姆妈就开始教阿拉汏绢头,如何擦肥皂,如何搓,洗,过水……再后来就洗自己的袜子、短裤。记得汏好的绢头贴在卫生间的瓷砖上,干了以后绢头煞煞平。其实阿拉男小囡是不大用绢头的,汏好手甩甩干,用袖子管揩鼻涕的也时有发生。不过到了学堂门口,值日生就要检查你有没有带绢头和有没有剪指甲。
那辰光还没有洗衣机,每家人家汏衣服都要用汏衣裳搓板。姆妈喜欢清爽,喜欢汏衣裳,喜欢用板刷刷龌鹾的地方。外婆常对我抱怨,家里的衣裳不是穿坏的,是被你妈汏坏脱的。如果汏起床单、被单来,姆妈还要大进贡(动静大),要等天气好的日脚,一早,先将床单、被单放进大木盆里用水里浸透。
我家有一块1米乘2米的汏衣裳板用来汏被头的(不汏被头的辰光,姆妈常常在上面裁衣裳,包馄炖皮子,我们小朋友开学习小组辰光,就在上面头挨着头的做作业,我还把它竖起来当黑板呢)。汏床单、被单,阿拉插不上手。姆妈把床单、被单铺在汏衣裳板上,涂上肥皂,然后用板刷“唰唰”地刷,特别是被横头地方,比较脏,必须狠狠地刷。
姆妈常叮嘱我们,“第一趟没有洗干净的地方,以后就再也洗勿干净了。”“一个人穿旧衣裳没有啥好难为情咯,衣裳穿龌龊了也不汏,邋里邋遢的,才坍台!”平时不大出场的爹爹,这个辰光腰里也扎起了饭单,等姆妈把床单、被单汏清爽,过了水,便跟姆妈一起到空地上绞床单,绞被单。然后一起捧着,小心翼翼地挂到绳子上,唯恐不当心拖到地上,还要重汏。
后来市场上一有洗衣机,爹爹就抢先尝鲜,买了台“水仙牌”。试运行那天,一大堆脏衣裳扔进洗衣机里,定时,选择洗衣模式,按钮一揿。笃定泰山休息,辰光一到,洗衣机“嘀嘀”一叫,衣服洗得喷喷香,姆妈开心得眼泪水都要流出来了。
【太阳出来晒被头】
每天早上起来摊床(整理床铺)也是件烦难的事。被头要折得四四方方,叠得整整齐齐,下面是厚被头,上面依次是薄被头、羊毛毯,把被单摊平拉挺,不留一条折痕,把枕头拍松软,端端正正放在床头……有这个必要吗?晚上还要摊开来睡的。特别当家里要有人客来时,姆妈对摊床更是一丝不苟。
那辰光屋里厢房间小,人客来的多了,椅子上坐不下,就要坐到床沿上了。因此床沿上必须铺上床搭(大毛巾或是其他布头)。那些年一家人家床上的被头,也是展示这家人家经济实力的一项指标。不是吗?新结婚人家床铺上叠起的被头,多的嚇煞人。女家陪嫁以6床被头、8床被头来显摆,互相攀比。我一直讨厌摊床,后来有了床罩以后,只需把被头拉拉挺,勿管床上乱七八糟,弄也覅弄,“呼啦”一下,床罩朝上面一遮,如同“古彩戏法”一般。勿晓得啥人发明了床罩,太美妙了,省去不少劳动力啊。
如果礼拜天碰到出太阳的日脚,就不用摊床了,姆妈会催促我,“快点去拉绳子,把被头拿出去晒晒!”那神情生怕浪费了太阳光,就像浪费屋里厢的水电煤一样。碰到出太阳的礼拜天,双职工人家都要出来晒被头,那辰光新村里的空地上,电线木头之间,树与树之间,只要是晒得到太阳的地方,各家各户都抢着拉绳子、晒被头,动作稍微慢一点都不行。弄得我碰到天气好的礼拜天,常常不能睏懒觉。那辰光出太阳日脚,人们晒出的各色各样的被头、羊毛毯、棉花胎,琳琅满目,也是上海滩的一大风景。
看一家人家经济条件怎么样,只要看他家晒出来的被头、羊毛毯、棉花胎就可以晓得了。穷人家晒出来的棉花胎,筋筋拉拉的。不过冷天里晒过的被头,夜里盖在身上暖烘烘的,倒是实在适宜。不过要是碰到天变的日脚,突然之间下起了阵头雨,那各家人家抢收被头、衣裳的慌乱场面,就像打仗一样。有辰光绳子断脱,更是洋相出足。
上海最难熬的是黄梅天,到处都潮兮兮、黏嗒嗒的,弄得人心情也勿爽快。过脱黄梅天,就是大太阳当头的大夏天(大暑)。那辰光,家家户户都抢着在太阳底下晒东西。我就帮着姆妈翻箱倒柜,从大橱里、樟木箱里翻出棉袄、大衣、绒线衫来,放在太阳底下晒,窗台上、地板上铺得都是,像在摆旧货摊。
阿拉弄堂里有两家人家晒出来的东西有点两样:弄堂口的那家人家晒的是中草药,申报纸四只角上压着石块,申报纸上铺着各式各样的中草药,大风一来,骨头轻的草药就飘飘然起来,急得主人家不停地往上压石块。弄堂底的那户人家晒的是线装书,一旁一个戴墨镜的老头打着瞌睡。一旦你走近了,想去翻翻那些书店里看大不到的线装书,老头就会“去”的一声,不让你靠近这些书。
阳光免费利用足。那些年,好多人家都喜欢自制咸菜、萝卜干。太阳底下晒大头菜、萝卜、雪里蕻菜、腊肉,酱油肉的,比比皆是。我们家有辰光也晒点雪里蕻菜、萝卜干。姆妈讲,自家做的咸菜,味道鲜,小菜场里卖出来的咸菜,都是用化学药水腌的,死咸,一点点鲜味也没有的,不好吃。道理讲了一大套,晒咸菜、萝卜干的生活都是我的。
冷天晒被头,到了热天揩席子,也是阿拉小八腊子的生活。下半天睏好午觉,大人就会叫小囡揩席子。考究的人家,先要用温水揩,然后再用干布揩干。那些年,虽然钞票不多,有辰光日脚倒是过得蛮讲究。
【扫地揩房间】
爹爹爱干净,阿拉小囡一回家,第一句话就是,“先去汏手,要拓(擦)肥皂咯。”一趟也不会放过侬。姆妈更是个洁癖(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不管大人小囡回到家,一律先要把外套脱掉。后来时行穿睏衣睏裤了,更是规定回到家,一律换上睏衣睏裤。
姆妈布置我们兄妹俩每天都要扫地揩房间(当然也是轮值制),她下班回家,角角落落都要摸一遍。家里的扫帚有好几把,姆妈规定,扫房间的用芦花扫帚(比较软),扫厨房间(3家合用)的用高粱扫帚(硬一点),而扫公共空间,则必须用竹扫帚(最硬)。侬讲复杂不复杂?一把扫帚扫到“脱顶”了,还在用。记得那辰光每个礼拜四是里弄里大扫除的日脚,每户人家派一个人出来扫小马路(大马路归环卫局的清洁工打扫),扫小弄堂。
我总是我家的代表,每趟听到居委会阿姨的摇铃声,我立刻拿着竹扫帚出门,从不拖泥带水。难般(偶尔)一趟勿去,隔壁邻舍就会问我姆妈,“今朝哪能唔没看到大伟?生毛病啦?”触我霉头嘛。那些年,小马路、小弄堂里总是脏兮兮的,侬想一个礼拜只打扫一趟(而且还有混在里面出工不出力的),哪能弄得清爽?
拖地板是爹爹的事体,我有辰光也会帮着做做。有一趟我拖地板,拖把没有绞干,水嗒嗒滴的,洇到了楼下,楼下的邻舍跑上来骂山门。我和姆妈下楼一看,不得了,人家天花板上一滩滩水迹,像画了张世界地图。姆妈连忙“对不起”,我也哭出乌拉地朝人家鞠躬道歉,事体就算结束了。换了现在,嘎便当?赔偿经济损失是必须的。
桌子、椅子因为天天揩,揩起来就比较省力。有些老式家具有不少凹槽,揩起来就麻烦。大面积的揩灰,我们常用鸡毛掸子,鸡毛拉过,灰就唔没了。有一趟我用鸡毛掸子掸灰,把爹爹放在五斗橱上的一只瓷瓶打碎了。之后爹爹就勿要我揩五斗橱上了,因为五斗橱上摆放着一些他从旧货摊上淘来的宝贝瓷器。
揩玻璃窗也是件家务活,特别是春节前的大扫除。揩玻璃有个窍门,先要用申报纸擦一遍,申报纸上的油容易把灰去掉,再用湿揩布揩两趟,玻璃就贼刮厉亮了。不过姆妈只让我们揩下面的几块窗玻璃,上面的几块特别是气窗玻璃,绝对不让我们爬高了揩。虽然住在二楼,一失脚摔下去,也非同小可。揩天花板上的灰尘有点麻烦,我学邻舍隔壁的办法,在竹竿头上扎一个布团,这样就可以把鸡毛掸子够不到的天花板上的灰尘、蜘蛛网一一揩掉。
【拆绒线挷绒线】
那些年,上海滩的阿姨妈妈们只要手头一有空,就喜欢结绒线。姆妈也是结绒线大军中的一员。阿拉一家门的绒线衫统统都是阿拉姆妈结的。一件明明看上去还蛮好的绒线衫,她非要拆掉,洗干净,再重结。
拆绒线快,汏绒线也勿是我的事体。不过汏好绒线晾干了,在拆洗结的过程中,还有个绕绒线的环节,需要一个人挷绒线,一个人绕绒线团。侬看过《水浒》里林冲充军的连环图吗?林冲在被衙役押解过程中,双手必须举着,带着木枷锁。我帮姆妈挷绒线的辰光,总是觉得自己跟林冲戴木枷锁充军一样,老举着双手,让姆妈一圈一圈的从我双手间绕走绒线。绕完一个绒线团,又是一个绒线团。两只手举着,一个姿势,多少不自由啊。
唉——挷绒线这种生活,邪气(非常)厌气。姆妈为了不浪费时间,常常在绕绒线团时,要我背乘法口诀,背唐诗宋词,或者给她讲我们学堂里各种各样的事体,烦也烦死了。
【帮爹爹擦皮鞋】
这是件颇有技术含量的生活,我很乐意去做,只是为大人夸奖的话。爹爹有辰光讲闲话下巴没有脱牢(意思“胡说八道”),他打量着我帮他擦得敞敞亮的皮鞋,会讲,“阿拉大伟本事大了,将来不怕没有饭吃了,寻勿着生活,擦擦皮鞋总可以的。”姆妈立刻竖起眉毛,“瞎七搭八些啥呀?讨骂!”
爹爹是化工原料公司的采购员,经常在外面跑业务,早上头穿出去的一双干净的皮鞋,下班回到家早已灰蒙蒙的一层。爹爹每天上班临出门前,总会用鞋刷在皮鞋表面来回擦几下。等到礼拜天,他会给皮鞋上鞋油。咖啡色的皮鞋用棕色的鞋油,黑颜色的皮鞋用黑色鞋油,两只鞋刷分别刷两种不同颜色的皮鞋。爹爹生活粗糙,常常用刷咖啡色皮鞋的刷子去刷黑颜色皮鞋,结果等到再刷咖啡色皮鞋时,刷出来的皮鞋变成了黑咖啡皮鞋,侬讲好白相伐?
我开始帮爹爹擦皮鞋,是从认得小江北开始的。勿晓得从啥辰光开始,有个擦皮鞋的男小囡,出现在离我家不远的商场门口。男小囡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一口苏北话。“皮鞋擦伐?啊有皮鞋擦伐?”叫起来刮辣松脆。看来生意不错,慢慢的小江北在商场门口似乎有了个固定摊位。放学以后,我好几趟立在他旁边看他擦皮鞋。他的木箱子里有各种颜色的皮鞋油,当顾客一坐下,将脚踏在木箱的踏脚上,他动作利索地把硬纸板插片插在鞋帮里,防止皮鞋油弄脏顾客的袜子和裤脚管。先是用揩布把鞋面上的灰尘擦去,用刷子把皮鞋缝隙里的尘土刷干净,然后薄薄地涂上一层鞋油,稍等,待鞋油干了些,便开始擦皮鞋。“唰唰——唰唰——”来回擦的动作越快,鞋油就能被皮层充分吸收,擦出来的皮鞋表层就越亮,敞敞亮!
没有生意的辰光,他就拔直了喉咙吆喝,“皮鞋擦伐?啊有皮鞋擦伐?”我跟他搭讪,聊天,他也很乐意。闲着也是闲着,讲讲擦皮鞋的一些小技巧(比如用废弃的女人丝袜来擦鞋、抛光,效果很好等),他又不怕我会去抢他生意。不过他跟我聊天的辰光,一双眼睛还是总盯着来来往往行人的脚上,一看到穿皮鞋的,就停下话题,使劲吆喝起来,“皮鞋擦伐?啊有皮鞋擦伐?”唯恐流失了自己的生意。
依葫芦画瓢,我照搬小江北擦皮鞋的一套程序,擦出来的皮鞋当然比爹爹自己擦的要挺括。每个礼拜帮爹爹擦一趟皮鞋,一擦擦了好多年,一直擦到成家。
【倒马桶那些事】
最后来讲一讲倒马桶那些事。不过要说明一点,倒马桶历来不是阿拉上海小囡做的家务劳动,在我的记忆库里也印象不深。
我家是1958年从地处市中心的复兴中路复兴坊,搬到市郊结合部的广灵二路(属虹口区,隔一条马路就是宝山县)商业二村的。据说爹爹、姆妈肯放弃热闹地段,搬到冷角落垛的地方(当初新村周边全是农田,还能看到一些战争时期留下的碉堡),看中的就是新村里有抽水马桶。那辰光在市区有抽水马桶的房子叫洋房,一般性的楼房、平房、石库门房子……用的都是马桶。
印象中,每天一清老早,马桶车就“轰隆轰隆”的推进了弄堂,“马桶拎出来”的吆喝声,打破清晨的宁静。人们(主要是女人,记忆中好像很少有男人倒马桶的)纷纷打开房门,睡眼惺忪地拎着马桶走向马桶车,将装满粪便的马桶,递给倒马桶的清洁工。紧接着人们就开始刷自家的马桶,一片“沙沙”的声音。上海滩在倒马桶声中苏醒过来,人们忙完这一切,才开始各奔东西,有去小菜场买小菜的,有去点心摊买早点的……而在墙根处,留下一排斜搁着的掀掉马桶盖的马桶,在阳光下“消毒”。倒马桶,曾经是上海滩居民区黎明生活的一道风景线。
那些年倒马桶的场景早已模糊淡忘,而大人“现在勿好好念书,大起来只配去倒马桶”的教训,却还依稀记得,
那些年,我们做过的家务劳动实在多,多得数不过来。现在家务劳动社会化(比如社区食堂)、家务劳动电子化(比如扫地机器人)、家务劳动网络化(比如网上手指头一点)……好多曾经的家务劳动,也都成为过眼云烟,只是留下了一些回忆的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