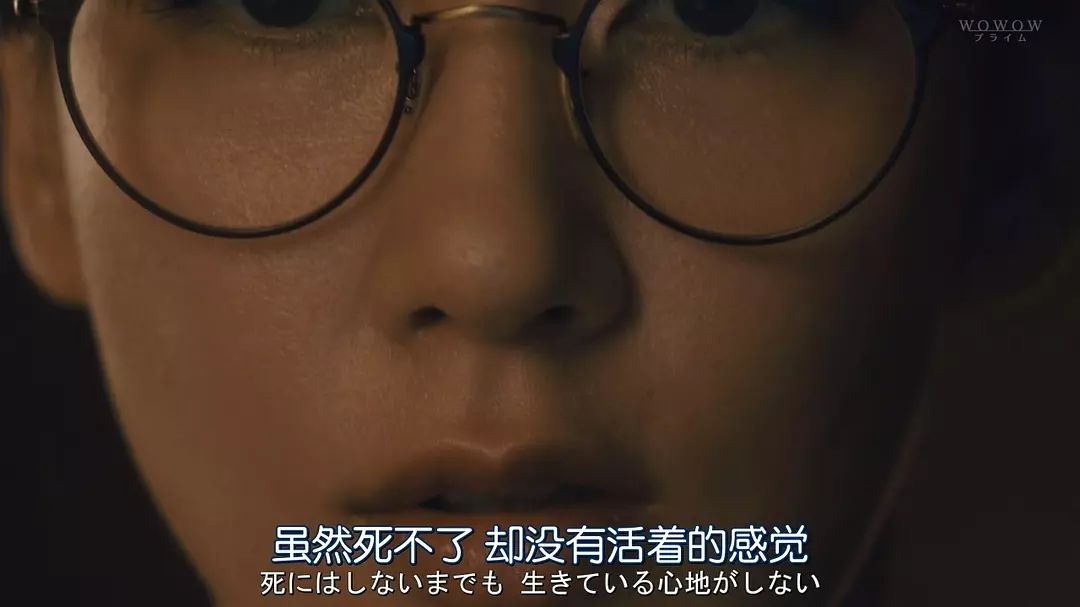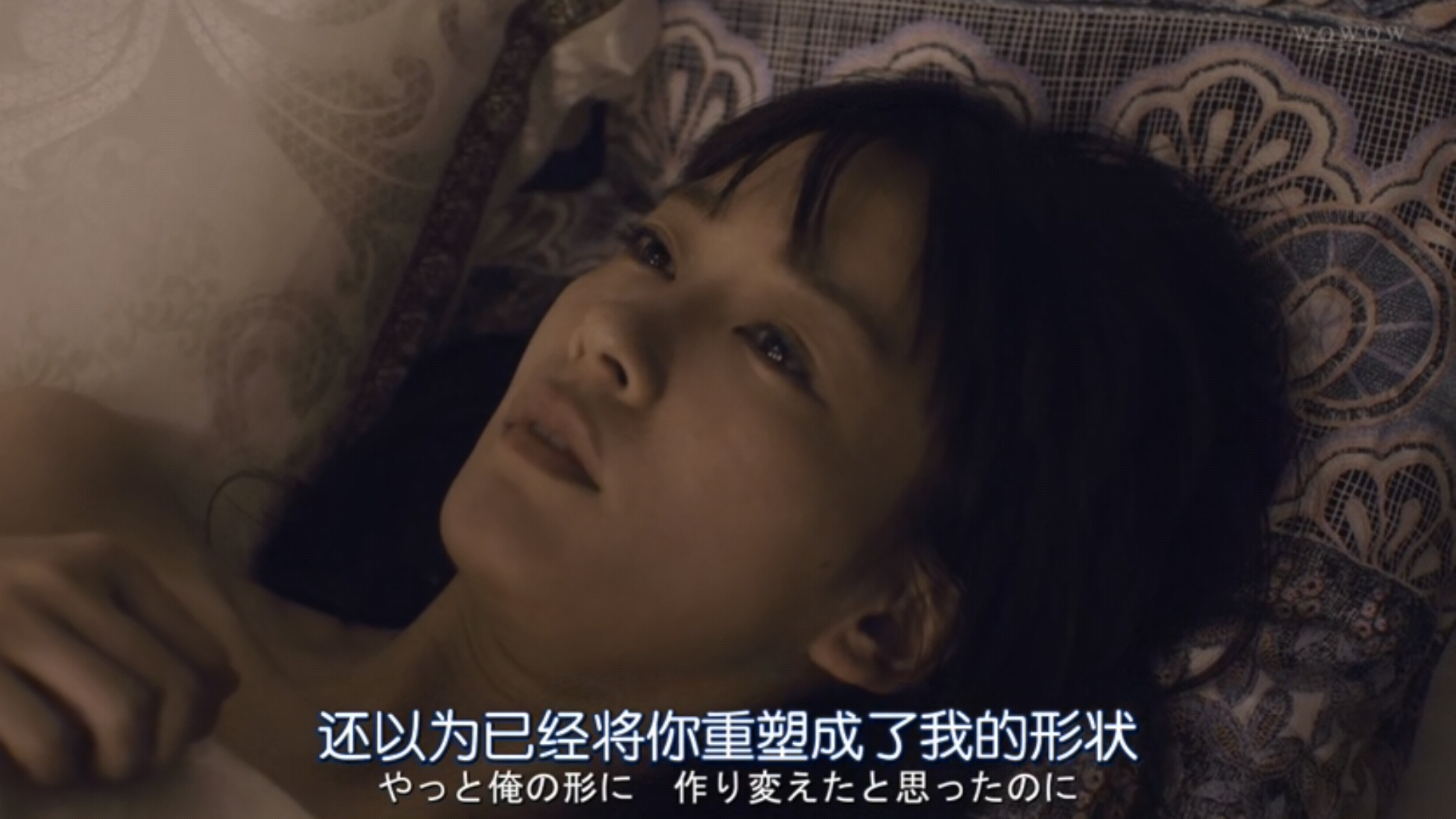觀劇《雙重幻想》| 你不知道的慾望人妻
“不要說愛我,我只是發情了而已……”這樣的露骨臺詞乃是出自於穩重的人氣美女編劇高遠奈津之手。
儘管從事着名利雙收的工作,還有一個照顧生活的居家丈夫,奈津的內心卻感到極度的虛無,漸漸上演起了現實版的官能小說。和牛郎翻雲覆雨,不專業的男人投入得一本正經,在奈津看來卻由於自以爲是而顯得拙劣無比,提不起半分情趣。
奈津讀大學時想當演員,因爲“在這個定好結局的虛構人生中,我不需要在意任何人的眼光。”
一旦真實的自我無法表達,人就會變得分裂。
越是壓抑的情感,越是蠢蠢欲動尋找突破口。
劇作家的職業,恰好賦予了奈津自由創造一個幻想國度的機會,得以用一種迂迴又坦白的方式言說自身。
曾經,初入職場的奈津也把大自己三歲的丈夫省吾理想化過,認爲他看起來非常成熟。但結婚六年,早早退休在家的丈夫原來只是一個婆婆媽媽格局頗小的男人。關鍵在於,省吾並不關心奈津的心理世界。
用奈津的話說:“他彷彿變成了我母親一樣。”當一個丈夫在妻子眼中變成媽媽,恐怕也象徵着精神上被去勢。奈津需要一個更陽剛的男人,一個無論外在內在都足夠強大的對象,可以引領自己,延續夢想。

享有國際聲譽的舞臺導演志澤狼太是站在雲端上的男人。不僅年紀上作爲奈津的長輩,專業上也是望塵莫及的老師。狼太的挑逗就像是樟腦液,從日復一日的死氣沉沉中激活了奈津的心跳。
爲了以最好的狀態迎接和大人物的約會,奈津像所有愛美的女人一樣下足了功夫。拼命取悅那個需要仰視的男人,奈津是看輕自己的。沐浴後的她躺在牀上靜靜等待着狼太的傳召,活像一個祭品。這場男歡女愛在不對等的條件下拉開了序幕。奈津在狼太面前瞬間退行回一個手足無措的小女孩。得到這樣一個高高在上衆人仰慕的男人垂青,哪怕是狼太在交歡時施虐性的小小暴力,也能被奈津昇華視爲獨特的寵愛。
依依不捨地道別後,奈津失魂落魄地離開了酒店房間,突然嚎啕大哭起來,那顯然不是打破世俗規則的喜極而泣。在狼太眼裏,奈津的赴約或許是成爲優秀劇作家所需要的徹底突破。但奈津心中充斥的,敏感到用手按一下就會溢出淚水來的龐大悲痛和哀傷卻從來沒有被任何人注意到,憐惜過。奈津買了一隻尾戒送給自己,被賦予濃烈情感的小小項圈是代表狼太的過渡性客體,也象徵着奈津的心靈被如何牢牢囚禁。
傳統且控制的母親,對奈津的人生干涉到了極致。
不請自來跑到小兩口家中,各種數落女兒不賢惠,還催着生孩子。似乎患有不孕症的女兒是自己沒有捏好的泥巴小人,是做母親的恥辱。奈津問及父親,母親淡淡地回答說去文化教室了,奈津笑着感嘆父親真是悠然自得。這個自始至終沒有出場的閒置男人,雖生猶死。
奈津不僅無法從母親身上獲得良好的情感體驗,想要撲進父親懷裏尋求支持的願望還沒來得及喊出口便也落了空。
最可怕的是,丈夫和母親一樣擁有幾近變態的控制慾,總是強加想法到奈津身上。興致一來就要不分時候馬上親熱,對妻子辛苦撰寫的作品習慣性地指手畫腳,甚至在奈津提出想獨立決定獨立創作時露出不屑一顧的輕蔑笑容,自大到將奈津的想法曲解爲擔心依附丈夫被人知曉的羞恥。當發現奈津開始不受管控,立馬變了臉,留下憤然離去的背影,還幼稚得把情緒發泄到了鄰居身上。在狼太的調教下,奈津忍無可忍,捨棄丈夫和婚姻的勇氣遠遠超出了省吾的想象。
奈津原本以爲狼太可以填補人生所有的遺憾。“眼前這個男人,纔是我的雄性。”奈津對狼太的癡迷,是對理想化父親的渴望。儘管無法從母親那裏獲得鏡映,但當狼太在身體和心理上一步步地開發着自己時,奈津好像通過和狼太的結合讓自己感受到了踏實的存在。就像吸食罌粟一般,奈津沉溺於這種肌膚之親帶來的溫暖。
可當奈津將殷切的期待和依賴一股腦地拋向狼太時,這個遊戲早已偏離了狼太的設定。那個叱吒風雲的男人內心還保留着原始的全能感,認爲他的女人就是應該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他從沒想過爲誰停留。一旦對方想在情感上靠近,對他而言只會是令人厭惡的糾纏。狼太的短信冰冷決絕,和教訓一個他認爲不聽話的孩子沒什麼區別。理想化的神像重重倒了下來,碎裂的大片玻璃砸得奈津血肉模糊。
心灰意冷之際,大學時代的前男友巖井良介的出現如同夏日清風,讓奈津有了呼吸新鮮空氣的機會。失戀時,新歡的效果常常好過時間,因爲漂泊無依的感情總是想要抓住一個可以轉移的對象。老情人的再會默契十足,良介的溫柔細膩和狼太的專橫粗暴形成了鮮明對比。而對良介來說,更像是被自己能夠征服奈津吸引。奈津享受的興奮模樣,妻子身上難以得見,這有損於他的男性尊嚴。
“他讓我說我愛他,明明是強迫我說的。他明明說了我也是,真的那麼說了。難道那些都是假的嗎?只是什麼都認真對待的我太傻嗎?”在良介懷裏可以暢所欲言,放聲大哭,奈津無處安放的滿腔悲憤終於暫時尋找到了一方棲身之所。這份打着友誼旗號的性關係再次被塞滿奈津源自兒時的心理需求,沉重得開始搖搖欲墜。良介像心理諮詢師一般認真分析着奈津的強迫性重複:“你一直都在扮演你母親的女兒。
童年時期留在心底的恐懼,就好像宗教裏不能觸碰的禁忌。
就因爲這樣,一直以來,你總是習慣讓自己做個乖乖聽話的好孩子。不是嗎?所以,無論是誰,只要兇你,只要態度強硬地逼迫你就範,你就會忍不住退讓,去服從對方。不是嗎?”良介似乎真的懂奈津,可同時又開始不動聲色地疏遠着她,就像生怕被奈津一塊兒拽進海里。
奈津越來越喜歡良介,直到在良介公司樓下看到對方一家三口其樂融融的畫面,提醒她不要忘記現實。奈津的身體裏又傳出了清脆的聲響,她自嘲是對自己太軟弱太寂寞的懲罰。沒有資格對良介發火,那就對自己生氣好了。隱忍的失望和憤怒誘使奈津在行爲上越來越開放,花和尚的邀請也照單全收。比起身體的慾望,更像是以性來發表宣言和示威。良介對家人撒了謊來找奈津,儘管意識到這個男人其實自私又狡猾,奈津卻沒有點破。
一段畸形的關係也好過沒有關係,她不想連這份僅有的慰藉也失去。
和良介親熱時不巧被母親撞破,奈津就像無助的小女孩一樣蜷縮在牆角,忍受着母親近乎歇斯底里的羞辱和打罵。這輩子的委屈湧上心頭,超出了奈津身體的承載能力。暈厥醒來,母親干涉自己婚姻的執念依然不可撼動,這愈發加深了奈津想要通過開放的性行爲忤逆母親的意願。
當話語權被剝奪,付諸行動似乎成了唯一的法子,聰明的奈津可以選擇性忽視它的代價。
和充滿野心的新人演員大林一也發展到牀上似乎是相對容易的。沒有感情的糾葛羈絆,奈津和一也的關係顯得更加純粹簡單。可是身體裏的繩結解開了,心裏的卻沒有。奈津在短暫的歡愉過後,陷入冗長的空虛。年輕的一也熱情衝動,不按規矩出牌反而打動了同樣向規則挑戰的奈津。一也告訴奈津,狼太提醒自己“可別被她大口吞了,那個女人看起來那樣,其實內心是個男人。”奈津愣住了,喃喃自語了一遍這話,繼而流淚大笑不止。
以一也的心智,根本搞不懂發生了什麼。狼太這番以已度人的投射顯然深深刺傷了奈津。他自戀地否認了奈津的女性心理身份, 否認了奈津內心翻江倒海的萬千柔情。
良介發覺一也成爲情敵後,開始瘋狂地聯繫奈津,兩個人狀態顛倒了過來。良介無比害怕失去奈津,就像小男孩捨不得心愛的玩具。
某日,一也在歡愛中途莫名其妙地停了下來,嚴肅逼問奈津沒跟自己見面的期間是否跟良介做了。“還以爲已經將你重塑成了我的形狀。”奈津愕然,說不出地痛苦,不管是哪種類型,男人們全把自己當成物品,性關係變成了一種權力關係。
奈津穿上舊浴衣和母親儀式性地告了別。路上接到警局電話,替惹了事的良介善後。在不知不覺中,奈津從需要他人的人,成爲了被他人需要的人。離開了母親,人生似乎變得有太多可能性。奈津在狼太面前瀟灑自若,還等來了良介的一句“我愛你”。唯有穿越孤獨那麼難。
煙花大會上,奈津凝視着絢爛的焰火出了神。
它們騰空而起,轉瞬間又四散下落,像是寄託在男人們身上的夢。
她比煙花寂寞。
身旁的一也像是關心奈津,發出詢問,卻冷冷的面無表情。奈津抹了抹淚,她不指望一也能明白,況且她看得出他不想明白。事實上,和一也牽着的手在熙攘人羣中也確實那麼輕易地就被衝散了。回過神來,一也已經消失在夜色之中,就像從未來過。
奈津不斷更換着性伴侶,既是渴求親密情感而不得的心靈空虛轉化成肉體安慰,也是她逐漸實現和母親的分離,放飛自我的大膽嘗試。在“我是被睡了呢,還是我把男人們睡了呢?”的自問中,奈津開始慢慢找回自己的主體性,真正享有了對身體的主宰權。
“我活在天堂與地獄間的縫隙裏,再也不會回頭。” 失足摔落山坡的奈津索性脫下木屐,眼神堅定地一步步向上攀爬,如戰士般悲壯。天堂之下,地獄之上,不正是我們身處的平凡人間嗎?無法回頭的是過去,是我們切實經歷過的人生,受過的創傷和永遠都不可能完全撫平的傷疤。
用社會常識來評判,奈津誠然不是良家婦女,可她也只是保留着一個小女孩的單純願望而已:渴求愛和親密,盼望長大和獨立。然而這些願望卻過早地遭受了太多挫折。
帶着未完成的夙願,她跌跌撞撞地孤身上路,飲鴆止渴。奈津的男人們並不瞭解她,事實上,她又幾乎從來沒有了解過自己,這也註定了她在黑夜險途上的踽踽而行。就像驚慌的跛足小鹿,在迷霧下,從一片荒原倉皇逃往另一片荒原。
性於奈津,太過複雜深刻。“女人光靠愛是活不下去的。”奈津的劇作推介詞一如她披着情慾的外衣發出無聲的悲情吶喊。希望有多強烈,破滅就有多受傷。其實,她是憧憬靠愛點燃生命,活下去的。
波伏娃在《第二性》裏寫道:“人不是生爲女人,而是成爲女人。” 那是一個小女孩慢慢坎坷成長,從幻想過渡到現實的過程。
女兒、妻子、母親,沒有一個標籤可以定義女人。
沒人能讓誰完整,這種事情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