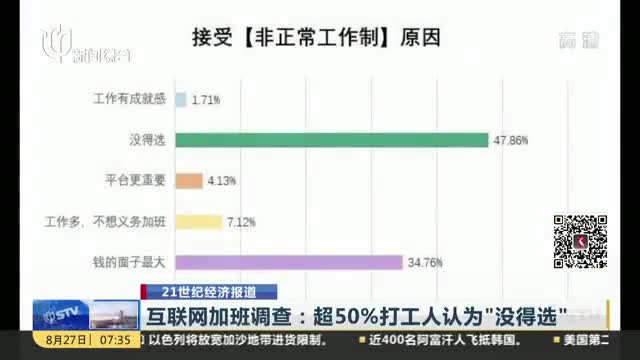互聯網“病人”:不加班,就很慌
作者/陳曉妍
編輯/張子睿
25歲的林肖屬於主動加班到最晚的那一批員工。
他對公司的夜晚尤爲熟悉:公司的空調會在晚上8點準時斷電,聲音突然停止,整個辦公室陷入凝固般的寂靜。很快,角落裏會繼續傳來噼裏啪啦的打字聲,電腦散熱器發出間歇性散熱的呼聲。起身打一杯水,他看見加班的同事們臉上掛着眼袋。
不久前,“字節跳動將推行1075工作制”登上了微博熱搜。但對林肖絲毫沒有觸動,他所在公司明文規定的朝九晚五,到了林肖這裏,變成了自願的“996”。
“不知道怎麼活成了一天不工作就很恐慌的人”、“不加班沒錢賺,感覺就要死於安樂”。
這是林肖在朋友圈裏看到的關於加班的討論。這羣年輕人有着相同的煩惱,被工作的快節奏和kpi(績效考覈)練就出強大的自驅力。一旦休息,就會感到恐慌不安。
近一年來,隨着“996”、“大小周”等話題的廣受熱議,大廠的加班文化也慢慢在退熱。字節跳動、快手、Boss直聘等多家互聯網公司都已宣佈取消“大小周”。近日,連格力這樣傳統企業也宣佈實行雙休制。
問題也隨之而來,工作制度的調整,能放緩快車道上的工作與生活嗎?
“工賊”?
林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互聯網運營負責人。來上海半年,他每晚都在10點後才離開公司。最近一個月,辦公軟件顯示,林肖每天的工作時長平均爲12.6個小時。
加班不是公司的強制要求。公司明文規定的朝九晚五,到林肖這裏,變成了自願的“996”。即使有雙休,林肖也會抽出一天到咖啡廳,抽出電腦繼續工作。
林肖所在的團隊也成了公司的“內捲髮起人”。他發現隔壁部門晚上的燈熄得越來越晚,也聽到過同事抱怨加班的風氣,“把整個公司的人都‘卷’了起來。”
1930年,經濟學家凱恩斯樂觀地預估100年後的生活:每週只需工作15個小時。人類最緊要的問題,是如何利用自由、消磨光陰?
如今,距離這個暢想的時間不到9年,每天三小時的工作制卻遙遠得宛如天方夜譚。許多像林肖一樣的年輕人上“時間焦慮症”,一休息起來就沒有安全感。
從第一份工作開始,在北京工作的王敏就習慣了下班後主動加班。她通常會在7點下班,經1小時的通勤回到家裏。喫飯洗漱之後,又在晚上10點開始工作,直到12點才休息。
到另一家互聯網內容公司應聘時,上司明確告訴她,公司沒有加班風氣。她先是感到詫異,入職後偷偷觀察身邊的同事:他們的確會按時下班,但大多帶着電腦回家,繼續白天沒寫完的稿子。“其實就是隱形加班。”她說。
在互聯網公司,很多工作無需固定場合,一臺隨身攜帶的電腦,就是所有人的移動工位。

對王敏而言,不管公司上下班制度如何變更,對工作時長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月度kpi。爲了完成績效。她常常同時操作多個項目,難以完成的工作量,只能靠自願延長工作時長來填補。
有一次,她在上海出差採訪,在酒店看完資料,已是深夜。她想起手頭另一個漫畫的項目,只能熬夜到凌晨三點,寫完文案,倒頭睡去。第二天9點,又得開始採訪。
那段時間,王敏形容自己是一根“緊繃的弦”。有好幾次,她覺得自己處在崩裂的邊緣。但王敏始終默認,這纔是“正常”的工作節奏。
在社交網絡上,主動加班、內卷的人,通常會嘲諷爲“奮鬥X”、“工賊”。有人在網上發佈吐槽同事加班的帖子,標題上寫着:工賊何必爲難社畜?底部有人跟着評論:“哪天公司不行了,你這種人是不是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因爲自己上班偷懶了?”
主動加班背後是更爲複雜的過勞問題。中國適度勞動研究會會長楊河清教授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主動過勞背後也是壓力。員工被要求不斷爲企業犧牲,纔可能會被領導青睞。
消失的閒暇
在現代一線城市,似乎不存在時間上的富裕者。
即使提前完成了工作,林肖也會在休息時感到不安。2021年9月,他剛結束一個視頻項目的策劃。下班時,在電梯裏,他聽見隔壁市場部的同事竟討論起了下一年的戰略規劃。那是一種課還沒上完,學霸卻開始預習起明年課本的感覺。
工作沒有盡頭。有時到了週末,林肖想停下來休息,但內心總是空蕩蕩的,沒法放空自己,覺得需要做點什麼來填滿自己。有相似焦慮的不止他一人,林肖看到有人發朋友圈討論加班:“不知道怎麼活成了一天不工作就很恐慌的人”、“不加班沒錢賺,感覺就要死於安樂”。
林肖的第一份工作,是北京望京的一家創業公司。公司業務發展並不順利。員工每週只需要坐兩三天班,上司也很少找到下屬交接工作。
在互聯網公司遍佈的望京,其他公司所在寫字樓,總是很晚纔會熄燈。這也提醒着林肖,他是這座加速運轉的城市裏的異類。
那時,剛好林肖認識的一位行業前輩,因爲中年失業,加上投資不善,被迫變賣房產。身在互聯網行業,林肖也做好了35歲失業的心理準備。而青春,就是奮鬥最大的資本。他突然理解了,爲什麼很多人崇尚成功學,那是焦慮的產物。他果斷辭職,像是從一條正在沉沒的船上抽身。
林肖得出結論,選擇一家處於上升期、有前途的公司,加班在所難免。
焦慮感同時也是安在王敏身上的發條,她剛入行一年多,急着得到業內和公司的認可。在快節奏的生活中,她一直秉承着效率至上。王敏自稱“小鎮做題家”出身,最懂埋頭苦幹。學生時代,每到飯點,從教室衝到食堂,再到喫完飯返回,她最多隻留給自己15分鐘的時間。
這股勁兒至今沒從王敏身上消失。kpi是老闆考覈員工能力的最直觀數據。有的同事會在完成一個工作項目稍微休息,但王敏總希望有另一個項目可以無縫銜接,甚至同時操作多個項目。一旦手裏沒活,就感到惶恐。
後來,王敏在網上看過過一個觀點:多線工作的能力其實是反人性的。所謂的multitasking(一心多用),是爲了服務效率社會,才強行培養出來的能力。
“都市人是停不下來的,我們不做無聊的事情,甚至失去了發呆的能力。”王敏在她自己身上發現了某種功能的退化。她會用碎片化的事物填滿偶爾得來的閒暇,有時是一些瑣碎的工作,有時是社交軟件上的視頻,扎進永不停歇的信息流。
來自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的諮詢師“心理芝士(下稱芝士)”,在這羣“時間貧困者”身上發現了異常。她告訴《豹變》,996、加班,這類過勞行爲,會影響人的自我調適能力。工作強度正常的人,能更好應對生活裏突發事件和壓力,而過勞人羣,在這方面的功能會出現退化。
芝士曾遇到在一家日企公司上班的來訪者。他連續加了三個多月的班,後來想要離職,公司卻不同意,以各種理由延後離職日期。他想申請勞動仲裁,卻忌憚公司在行業裏的影響力。
這樣的僱傭矛盾並不少見。但這位來訪者被長期的過勞工作透支,心理狀況變得脆弱,因此患上了中重度的抑鬱症。
芝士在來訪的職場人士身上發現一個共同點,他們往往在面對人際關係時敵意更強,敏感易怒。
金融從業人員、程序員等,是來訪者中工作時長最長的一羣人。芝士將加班、996形容爲觸發某些心理問題機制的“扳機”。
扳機扣動之後,緊接而來的是切膚的“疼痛”——有人來醫院時,說自己喘不上氣,冒冷汗、心跳加快;有人一天拉十幾次肚子,有人甚至泌尿系統出了問題,感受不到自己的尿液;更嚴重些,有人胃痛到無法正常工作,到醫院檢查,卻查不出毛病。以上種種,都是伴隨着抑鬱症出現的軀體化症狀。
困在系統的打工人
主動加班,很多時候看起來是個體的自發選擇,但純粹“自發的”過度勞動,似乎並不足以成爲動因。
“北漂”“深漂”“滬漂”等詞,讓一線城市似乎天然帶有一種奮鬥敘事。還在北京工作時,林肖聽一位朋友說,連公司挑選的掛曆,都寫着“成事之心”四個大字。老闆在開會時情緒激動:“真想選擇安逸,你來北京做什麼?”
後來,工作地換成了上海。有一次週末,林肖走進一附近的大型咖啡廳。窗外正下着雨,店裏的位置都被佔滿,每張桌子幾乎都擱着一臺筆記本電腦。有正在跟客戶談業務的上班族,有考研黨,甚至還有人輔導孩子的功課。林肖感到驚訝,這是一羣生活在同樣的城市節奏之中的人。

林肖所在的團隊,是公司里加班最厲害的。而組建起這個“內卷小組”的領導,平日裏給人的印象,是在工作裏永不疲憊的女強人。後來,林肖無意間得知女領導的另一面,那位女領導有一個微博小號,幾乎每一天,她都在上面發“不想工作”的動態。
國慶假期之前,女領導與團隊的同事聊天。她突然提到,希望放假期間,可以和同事當彼此“七天的陌生人”,不要被工作的事打擾。但因爲一位同事發宣傳時,錯放了帶有競品信息的海報,女領導又不得不加班,幫助下屬處理這場事故。
林肖這才發現,不管是基層員工,還是管理層,每個困在這套體系之中的人,都有身不由己的一面。
“你畢竟還要跟別人合作。”王敏也有同樣的感受,個體是鑲嵌在鏈條中的一環,只能跟着轉動。這既是工作倫理所教導的,也是嚴厲的工作機制所強加的。
而另一方面,技術的進步,也進一步完善了這個工作的系統。目前來看,技術非但沒有將人從勞作中解放出來,反而爲隨時隨地加班提供了更大便利。
在貴陽從事軟件銷售的小莫也有類似感受。最近一個週末,她剛爲年末的活動加了一天班。這是她的第三份工作,進入公司也有三四年之久。但緊張的感覺從未改變。“一直想辦法往前趕。”小莫說。
疫情是小莫所在公司加班文化興起的節點。在此之前,同事們尚且不習慣遠程工作的方式,有什麼事都要到公司當面溝通。疫情期間,公司自己研發的辦公軟件帶有會議功能。自從遠程辦公變得更加便利,老闆隨心所欲,大大小小無聊的會議比以前多得多,員工無法請假,處於全天候待命、隨時工作的超額勞動狀態。
有時候正值飯點,老闆突然有事,召齊人開會,小莫剛拿起飯碗,又得放下,一個小時後,家人都已經喫完了飯。工作時間被會議擠佔,爲了完成項目,她只好主動加班。
“扭曲的”工作觀?
幫來訪者處理工作壓力的同時,芝士自己也面臨着工作時長過長的問題。有時候,她一天接待六七個諮詢,有六七個小時的時間,都處於大腦高速運轉的狀態,還要承接來訪者的負面情緒。
一天下來,當她回到家時,也會發現,自己對待家人、孩子的態度更不耐煩。但是,心理諮詢師們常常比普通人更能敏感意識到心理狀態的變化。在她看來,人對自己情感體驗越精細,就越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內在生活,就更能及時且正確地排解情緒。
最近一段日子,王敏正在學着如何放鬆。她申請在家辦公,給自己留出半天的休息時間,刷完短視頻,給自己煮點東西喫,又睡了一覺。幾天下來,她沒有感到輕鬆,反而多出焦慮感和內疚感。
上司詢問王敏的工作進度,言語間透露出對她這幾日工作效率的不滿。這又讓王敏陷入苦悶,她一直重視別人對她的評價和看法。
這種情況,被諮詢師芝士認爲是工作的錯誤思維之一。在她接待的來訪者中,很多人在職場中受挫,過度自驅,都是因爲在工作關係中加入了不合理的期待。
她曾接待過一位銷售行業的來訪者。爲對方做了分析之後,芝士才發現,這位銷售員並不是自己所說,只是需要一份工作掙錢養家,而是希望在工作中能交到知心朋友。
一旦將過多的情感需求放到工作中,就會讓工作變得更復雜。太過期待上級的認可的心態也很常見,很多人主動過勞、焦慮不安,也正因爲如此。
在她看來,當人的成就感,是來自於自己設定的目標和標準,而不依賴外在的評價的,並不容易出現心理失衡的情況。但來訪者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對自身情況和心理需求知之甚少,只能依賴外界的回饋。
林肖認爲,自己的邏輯體系已經足夠堅定。成爲別人眼中的“奮鬥X”,他也並不介意。
他身邊也有一些既不滿現狀,又無力改變的朋友。朋友告訴他,工作日午間休息,總有種“放牢飯”的感覺。晚上下班,熬到坐電梯下樓那一刻,就算是“出獄了”。林肖並不想成爲這種人。即使是現在“躺平”一詞頻繁出現,甚至成爲身邊人的觀念熱潮,他也爲所動。
“能真正躺平是一種能力。”林肖坦言,很多人根本不捨得離開大城市,也不願意放棄體面的收入。他更認同,既然做出了選擇,就忠於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
在上海加班的無數個夜裏,起身打水,看到辦公室裏凌亂的桌面和同事疲憊的眼神,他也會偶爾感慨:“我們公司真是個血汗工廠。”
有時候,無視這種異常,像是一種自我欺騙和矇蔽。但林肖總能順利說服自己,想想擴張的平臺,和正在處於上升期的自己。“挺自洽的,把自己活成體系的一部分。”(來源:豹變)